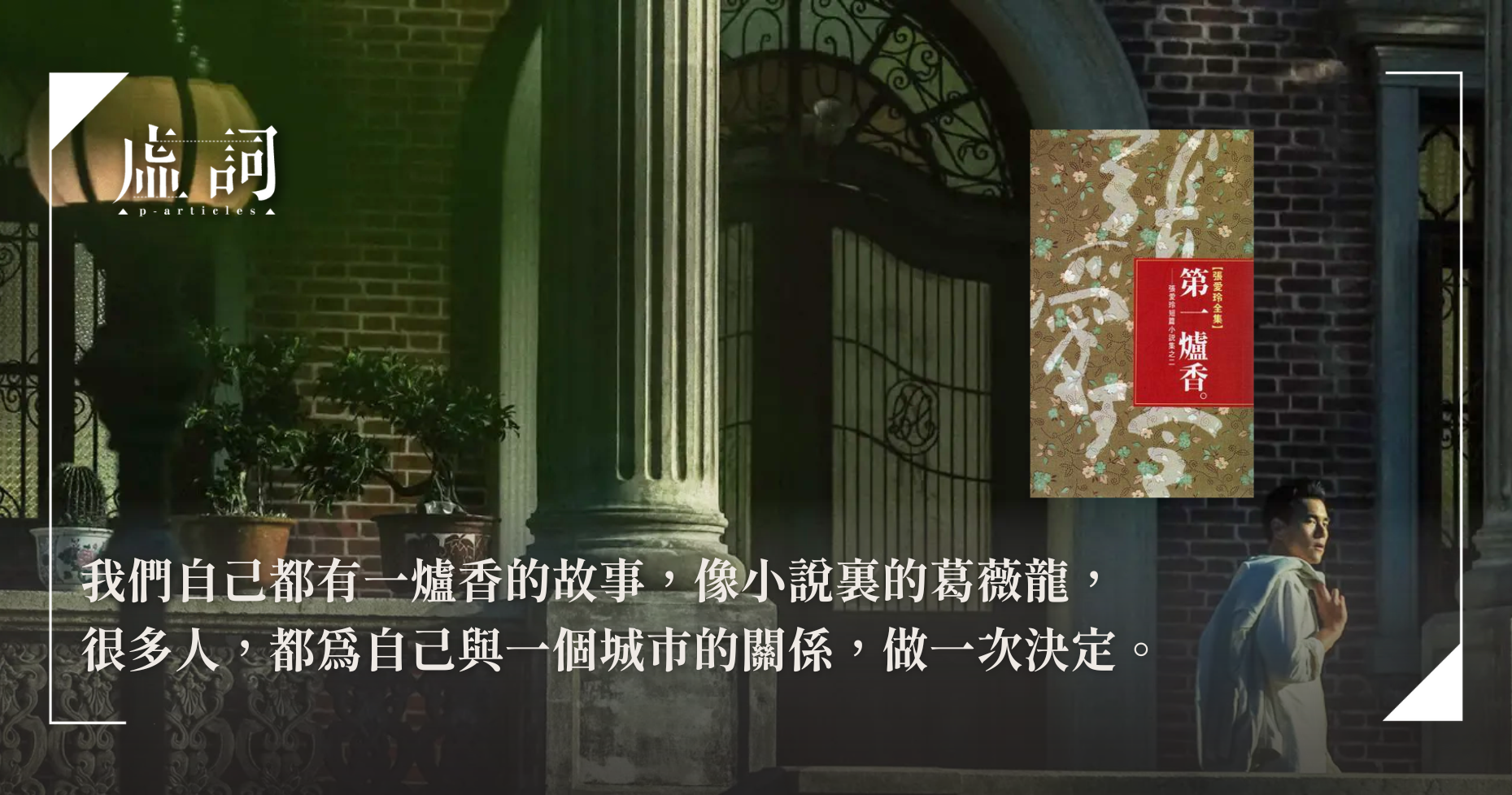一舖清唱:《____小事化有____________》——把歌唱成舞台劇再演成電影的戲法
劇評 | by 新八 | 2024-05-30
無伴奏合唱劇「一舖清唱」最近推出原創音樂劇場《____小事化有_______》,由「一舖清唱」聯合藝術總監盧宜均包辦作曲、編曲及合唱指導,加上著名填詞人梁栢堅執筆,捕捉了城市內小人物的聲音。新八回想十二個獨立的場景,當中充滿電影感的舞台處理,是他認為近年最出色的,觀眾能在〈草書〉感到「又去草被玩一餐,再揈手遊遊閒」的放鬆,〈霞氣〉則述說了淡然哀傷的愛情故事,而導演林俊浩充分利用劇場空間,營造出多變的場景,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劇場體驗,在疲倦的生活中打開了一個休憩的空間。 (閱讀更多)
知道陳雪怎麼帶貨,就知道她怎麼寫小說
書評 | by 陳栢青 | 2024-05-27
臺灣最多產的同志文學作家之一陳雪,於年初推出短篇小說集《維納斯》,作家陳栢青從她的首本短篇小說《惡女書》說起,看她如何從當年的「惡女」蛻變成人妻,卻一路秉持惡女的核心,不必標榜超前,也不必譁眾取寵,僅是忠實地書寫自身,敢於寫人所不敢寫。陳栢青形容,陳雪在《維納斯》裡下手始終殘,依然狠,更顯示了夜市的女兒、老牌同志代言人如何重新召喚同志文學的「商業價值」,讓品牌再生,成為「新世紀網路團購帶貨女王」。 (閱讀更多)
還沒愛夠阿嘉莎:評《阿嘉莎.克莉絲蒂:謀殺天后與她的未解之謎》
書評 | by 張亦絢 | 2024-05-20
台灣作家張亦絢最喜愛的書本之一是《克莉絲蒂自傳》,所以當她閱讀英國歷史學家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的《阿嘉莎.克莉絲蒂:謀殺天后與她的未解之謎》,她指自己在先天上有「非常不利的因子」。當沃斯利的說法與阿嘉莎衝突時,她幾乎都還是站在阿嘉莎那邊。在這書評裡,張亦絢談到阿嘉莎的1926年大失蹤事件,以及阿嘉莎拆解女性的世代心結,而她認為沃斯利面對女性文學世代的方式,雖然不無莽撞、血性的直率態度,但說不定連阿嘉莎都會欣賞。 (閱讀更多)
邊緣與混雜:淮遠〈加拿大鹿〉的身份書寫
評論 | by 麥子 | 2024-05-18
香港身份問題,一直是本地文學歷久不衰的主題,又以上世紀回歸前夕的80年代尤為盛行。麥子以淮遠的〈加拿大鹿〉(1983)為例,展示當中香港身份建構具有「邊緣」和「混雜」的特質,及面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無力感,而淮遠對香港身份在殖民體制下的反思,為後來建立主體的文化解殖運動奠定基礎,也是一個時代變遷的印記。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