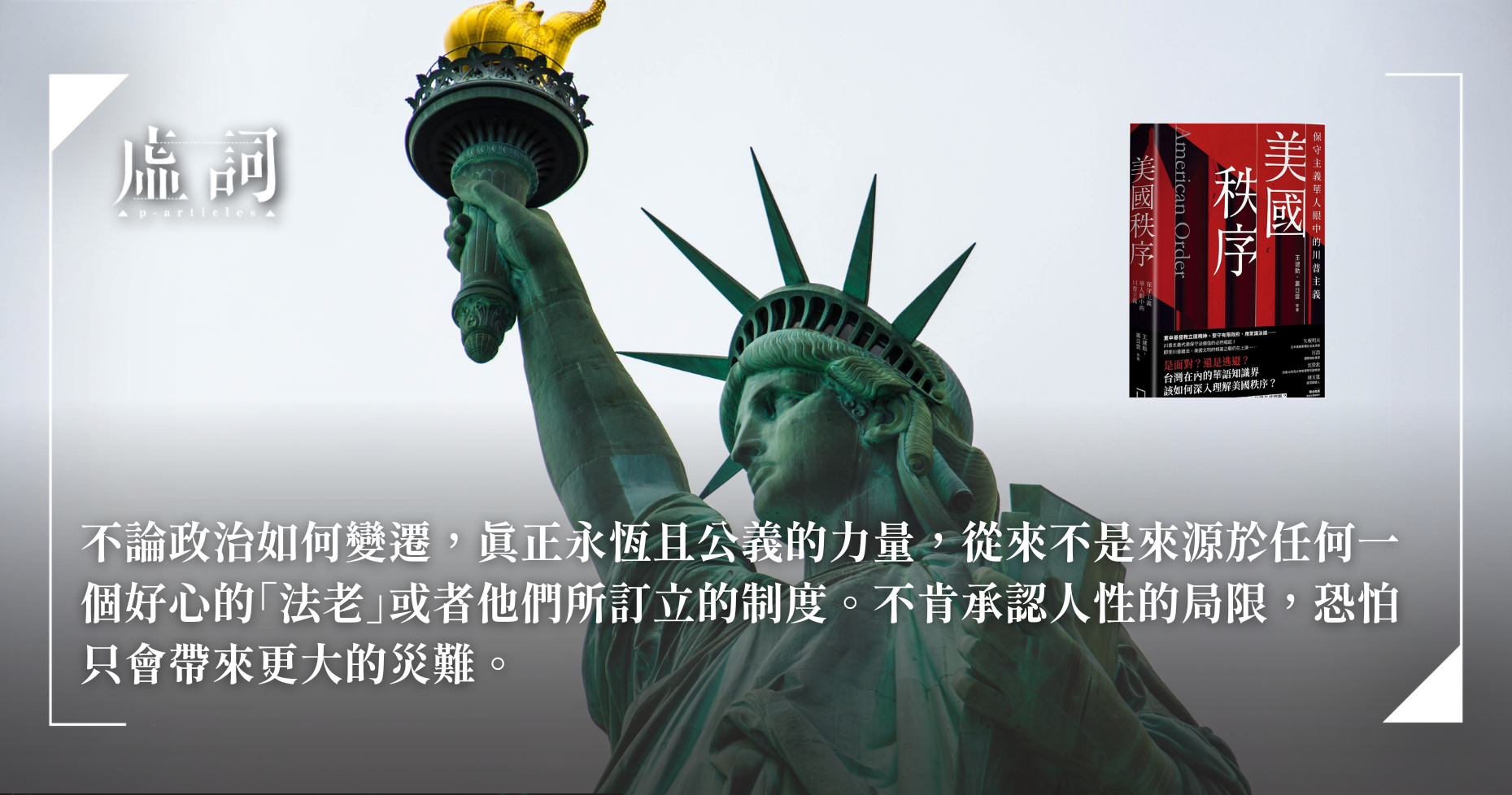川普又來了——《美國秩序:保守主義華人眼中的川普主義》書評
書評 | by Sir.春風燒 | 2025-02-11
在國會大廈圓形大廳,川普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第47任總統,就職演說中稱,要推動常識回歸。
2024年美國大選,「紅潮」來勢洶洶,川普不僅拿下七個搖擺州全部選舉人票、再度入主白宮,更帶領共和黨奪得參眾兩院多數席位,共和黨可謂完勝。如果說2016年川普勝選是一場意外、是對手的一時失手,或者是選民的一時手滑選錯,那麼這次大選釋出的訊號就是:選民的抉擇很篤定,不是誤會。
川普是戴罪之身,身負「封口費案」全部34項罪名;至於個人品格,就為人詬病更深了:傲慢自大、信口開河、煽動民粹、侮辱女性、歧視少數族裔、冒犯LGBT、盲目排外、漠視環保、疏遠盟友、反全球化……簡直罄竹難書。然而,這次大選的結果卻明確告訴人們,原來在多數選民眼中,以上罪名沒有表面看起來那麼重要。我想,選民不是瘋了,只是所惡有甚於此。
過去四年,美國人親歷Covid-19帶來的嚴重經濟衝擊,承受著高失業率、通貨膨脹以及供應鏈危機,許多選民對此心有餘悸,人們清醒地拒絕左派那種「畫餅」式的「獲得感」,而要可以實實在在「獲得」吃進肚子裡的「餅」,因此希望選出一個有能力振興經濟的總統,重新為社會積累財富;再者,外交上,民主黨支援烏克蘭對抗外侮,由此產生的大量財政支出並非出自民主黨的黨費,而是由美國納稅人埋單,然而,俄烏戰場今天卻變成絞肉機,兩軍膠著而毫無停火跡象,陳義過高的理想裹挾著每個社會持份者的實際利益,因此,不難理解許多選民需要一個懂得談判和交易的領導人,帶領國家走出這個泥潭。這個人不必是標榜「我將無我」、從不爆粗、大愛包容的聖人,卻必須是可以幫助美國人擺脫實際困境、踏實生活的普通人。
《美國秩序:保守主義華人眼中的川普主義》成書於2021年,亦即川普連任失敗翌年,是了解川普及其主張的一部不錯的入門書。書中邀請了多名保守主義華人學者及政經評論家,揭橥戰後國際秩序和全球化現狀,在文化戰爭和價值愈發撕裂的美國政治現實背景下重思美國價值,順便帶讀者再次認識川普。
書中多個作者反復提及一個重要概念,那就是「後現代主義」。其中一個作者叢日雲教授指出,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本身就是一場文化戰爭,是「政治常識」對戰「政治正確」,前者代表「現代主義」的價值觀,而後者則是代表「後現代主義」的價值觀。
眾所周知,現代文明的平等觀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無論何種性別、種族、宗教背景,個人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這種平等確保所有人能在同樣的起點上競爭,並通過自身努力達到不同結果。然而,後現代主義者認為,這樣還遠遠不夠,他們要爭取的是結果和享受的平等,經濟上要平均主義,政治上要均等分享權力。譬如,他們認為,參選總統過程中男女平等競爭是不夠的,必須要在結果上平等,也就是男女輪流坐莊;再如,若社會上黑人佔總人口13%,那麼大學教授、億萬富翁、州長的群體裡也必須存在13%的黑人……用結果反推過程,這種歸因方式顯然有悖邏輯,僅根據某些群體在經濟、健康、犯罪率等方面的結果不如其他群體,就反推整個過程中存在系統性歧視,是忽略了「不平等」的多重原因。
激進的身分政治推動者打著平權的旗號,一開始他們要為少數特殊身分群體爭取平等待遇,但隨著身分的評判標准不斷細化,實際上越來越難操作,不禁令人懷疑,強調結果平等不僅無法真正解決不平等的根源,反而會引發更多需求,而這些追求是個無底洞。同時,反歧視的本心,又荒謬地催生出一種逆向的身分歧視,即剝奪先天優勢群體原本擁有的正當權利和平等機會,以達到更極致的均等結果。就這樣,「爭平等」的訴求很快就變質,滑向了「爭特權」。書中有兩段話寫得很有意思:
二〇二〇年五月的「黑命貴」運動也是一個典型。從一個可能過度執法的個案,一下子就上升為全面的種族歧視。左派對黑人的歷史敘事很激進:黑人歷史上受奴役、受壓迫、被歧視,於是他們有翻身得解放的要求。換句話說,他們從受壓迫的經歷,反證他們目前造反的合理性,證成了「造反有理」的邏輯。至於目前他們是否仍受到系統性歧視,他們不允許有爭論的餘地。受壓迫者自然就具有一種道德優勢和神聖的身分。特殊膚色甚至成為身分優越的標誌;人們爭相炫耀自己的特殊膚色,還有白人為獲得較好的出身,冒充少數族裔。他人如果對他們說三道四,讓他們感到受到了「冒犯」,就是種族歧視,就是發表了仇恨言論,就是法西斯主義。同時,他們從結果的不平等反推出造成結果如此的原因一定是歧視,然後提出種族補償的要求等等。
……
身分政治本來是前現代現象,即等級政治。決定身分及其地位的是血緣、門第、宗教等,它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化。到了現代社會,身分政治轉變為階級政治,階級的基礎則是經濟地位。而後現代的身分政治彷彿是傳統身分政治的回歸,但身分不再是由血緣和社會(或權力和財富)地位決定的等級,而是各種文化身分:民族與種族、宗教、性別、性取向等。現代政治產生了人民崇拜,然後轉向平民崇拜,到了後現代則開始轉向一種身分崇拜:崇拜少數弱勢群體的文化身分。現代政治要求對身分差異的寬容、認可和尊重,但在後現代身分政治推動下,卻轉向對少數文化身分的讚賞、人為強化甚至崇拜。原弱勢身分群體要求成為特權群體、成為道德判斷的標準,按是否「冒犯」了他們這種非常主觀的感受,來設立「政治正確」的戒律。同時,如上所述,他們要求按身分均等地分配權力和各種機會,將逆向的身分歧視作為政治的基礎。
川普要保守的價值,正是與後現代主義抗衡的現代普世價值,堅守有限政府、資本主義並重申猶太-基督教傳統,以此重塑美國的經濟和文化格局。經濟上,川普主義主張通過減稅和減少管制重建美國經濟基礎,並提供機會讓普通人實現「美國夢」;而在文化上,川普主義則力圖挑戰進步主義的話語壟斷,捍衛傳統價值和「以尊重民主憲制為前提」的言論自由,對抗政治正確和身分政治的主導地位;外交上,川普主義奉行交易藝術,無論是盟友還是死敵,一律拒絕以「我弱我有理」作藉口讓美國單方面付出、無節制地佔美國納稅人便宜。王建勳教授在書中這樣評價川普主義:「川普主義的作用在於喚醒美國民眾回到由他們自治的時代,而不是被無原則的職業政客和腐敗官僚統治。」
讓我們回憶川普在上一個任期是怎麼做的。2017年,川普簽署《減稅與就業法案》,將企業所得稅從35%降至21%,並減少個人所得稅稅率,此舉推動了經濟增長和股市繁榮,令失業率在2019年底降至50年來最低記錄3.5%。同年,川普宣佈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他認為該協定不公平地限制了美國的能源生產,特別是煤炭和石油行業,導致美國工人失業和能源價格不穩,並可能使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競爭力下降。2018年,川普對東方大國採取強硬態度,對數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又將多家科技企業列入出口管制清單,以減少兩國貿易逆差並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2019年,川普替被伊斯蘭國(ISIS)殺害的無辜美國人報仇,美軍在敘利亞擊斃該組織的首腦巴格達迪,川普在白宮記者會上毫不客氣地說:「他死前屁滾尿流的懦夫模樣,真該讓ISIS的追隨者們親眼目睹。」
以上種種,無不體現著川普主義將美國的國家認同放在首位,也就是川普掛在嘴邊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而「美國優先」是必然與全球主義和國際主義對立的。與左派渴望世界大同、抹掉所有國境、全人類自由進出各國的願景不同,川普主義認為,國家是需要安全邊境的,畢竟世上的爛人、爛地、爛文化還是太多了,面對它們,美國要做的——用網絡流行的說法——就是放下諫言情結,尊重他國命運。要維持美國自由的政體和民主制度,就必須保護美國傳統價值和文化,防止被外來因素所稀釋,而不是追求「沙拉拼盤」式的文化多樣性。王建勳教授在書中寫道:
在歷史上,美國人透過同化和吸收,接納了大量的移民;先是歐洲人,然後是亞裔、非裔與拉美裔移民,他們都在「大熔爐」裡經過歷練之後,變成了認同美國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美國人。但是,隨著身分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同化與吸收的做法和「大熔爐」觀念都受到了挑戰;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要求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語言,崇尚「沙拉拼盤」的理想。一些全球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認為民族國家已經過時,聲稱人們有權移民到任何國家。他們甚至拒絕使用「非法移民」這樣的用詞,代之以「未記錄在案的移民」或「未經授權的移民」,任何反對這些移民的人都會被扣上「種族主義者」或「排外主義者」的帽子。大量支持川普的人生活在小鎮或鄉村。他們不喜歡大政府,不喜歡華盛頓的「沼澤」;喜歡自己生活的社區,熟悉自己的鄰居,不喜歡大都市及其所代表的世界主義。他們認為,美國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和身分認同。他們害怕「文化驅逐」(cultural displacement),擔心原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
為什麼要放下諫言情結?有能力為何不主動助人為樂、扶人一把,讓浪子回頭、變廢為寶、糞坑開出花海?本書最後一文,劉軍寧談美國秩序的根基就解釋道,美國的憲政制度和政體難以成功移植到他國,原因在於這整套文明是建基於在信仰和聖約的,美國的立國根基是與神的聖約,是雅威(又譯「耶和華」)頒布的摩西律法——正如亞當斯所說,它是針對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設計的,無法有效管理沒有道德和宗教約束的民族。因此,只要這種信仰和聖約不被繼承或認同,其他國家無論外表上如何複製這些制度,都無法成功運行。以此反觀最近三屆的美國大選,那不僅是關乎兩個候選人的競爭,更是兩種政治價值觀對立、是「祂」與「他」之爭:一方堅持按照神的公義原則來治理,而另一方則試圖改變或摧毀這些基礎。因此,川普的出現,是美國社會價值撕裂的結果,而非原因。
宣佈「上帝已死」,然後呢?法老、人造神就出現了。神的假冒偽劣替代品往往帶來極端化和意識形態的獨裁。歷史上,左派的極端意識形態和領袖神化,可謂族繁不及備載,人造神以「人民父親」或「指路明燈」的角色粉墨登場,頭戴絕對化的高尚政治理想,身披無可置疑的道德信條,手握無懈可擊的宇宙真理,在人間隨心所欲地壓制異見、推銷虛偽的完美主義、打造空洞的靈魂,而奪去的是實實在在的個體生命和財產。保守主義鼻祖柏克(Edmund Burke)就深刻批評法國大革命破壞傳統秩序、迷信抽象理念、否定宗教、依賴暴力,因此柏克提醒後人,真正的自由與繁榮必須建立在穩固的社會基礎之上。
本書的幾篇文章無不暗示一個觀點,即不論政治如何變遷,真正永恆且公義的力量,從來不是來源於任何一個好心的「法老」或者他們所訂立的制度。不肯承認人性的局限,恐怕只會帶來更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