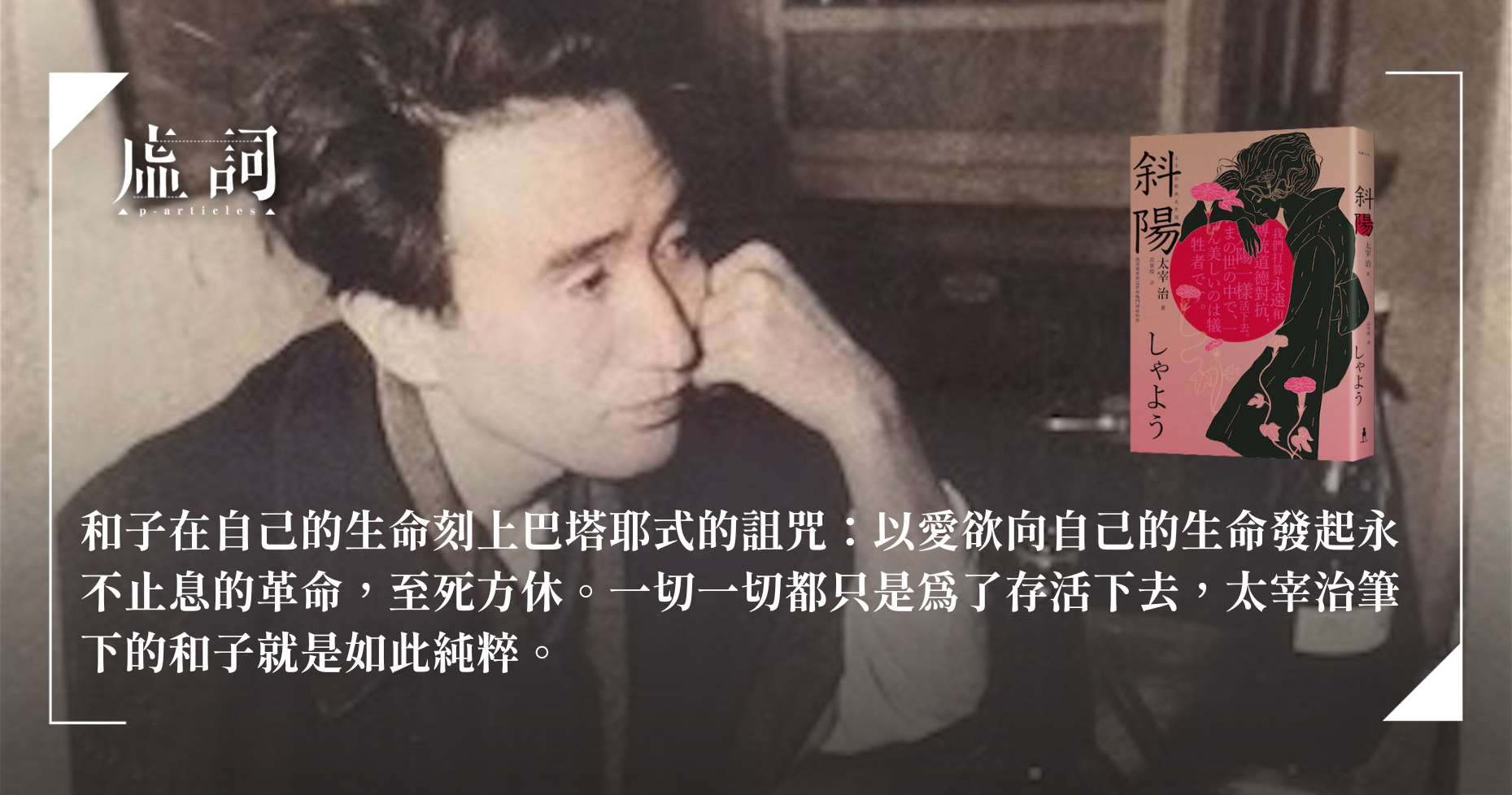為了活下去——論太宰治《斜陽》的美學式生存
書評 | by 海鹽 | 2024-09-05
「以愛欲向自己的生命發起永不止息的革命,至死方休。」
每個時代、每個族群大概都會有關於「人」的理想模型,當一個存在降生於世界,就會被一整套給定的符號秩序所規訓。從日常生活的微小處,一個存在會被教導在人與非人之間作出明確的區分,被教導要遵從性別與層級等相應的秩序。在這裡,存在被生產成一個個合符資格的人,而人的背後則彷彿有一種意志,不停地在凝視、檢查着自身,期望與催促着自身能完美地再現那一個與其相對應的角色與身份。
一場預先設定好的角色扮演,存在因此而被遮蔽。只有經歷偶然的斷裂,人之死亡,始能讓存在顯現,然後為如何肯定自身存在,作出致命的抉擇。
雙重失落:裂縫的誕生
在《斜陽》之中,身於戰後日本的主角和子,就是一個被要求遵循貴族秩序的女性,而其理想模板的具象化呈現,就是她的母親。她羨慕着母親每一個細微的動作,仔細地捕捉及讚嘆母親拿起餐具的姿態、對食物的處理、進食的手勢;崇拜着母親把情感壓抑下去後所剩餘的空靈氛圍;渴求着那副不發一言、毫無生氣的貴族女性身體。換言之,和子想要成為母親。而一切都僅只是渴望獲得母親的關注和愛。
但時代的動盪與局限注定和子的願望將會落空。
作為那個時代的貴族女性,被要求成為男性的附屬物,於是當男性離開,女性生命幾乎會失卻意義,而和子的父親早逝、弟弟離家出走,她的母親因此而每天都待在窗邊,凝望窗外,記掛守候着不在場的他們,這預告着同樣作為女性的和子,始終不能得到母親真正的愛——那種給予男性的愛;戰爭生產着失落的貴族,徒有虛名與貴族的慣習,卻不再有資源支撐他們過着貴族的生活,要生存就必須玷污乾淨的雙手去勞動,於是和子必須要下田工作,一方面和子樂見藉由自己玷污雙手去工作,反襯出母親的出世脫俗的形象,讓母親在其心中的地位更顯神聖,也渴望因此而得到一種近乎卑微的母愛,但另一方面卻意味着和子自身與母親那種不染俗世的嬌柔生活的理想越來越遠。
在這個時代成為像母親一樣的貴族女人還可能嗎?還可能得到母親的關愛嗎?現實無情地加以否定,這撼動了和子一直堅信的「真理」,理想出現裂縫,從中湧現出無盡的痛苦,卻伴隨着自由的曙光,那裡有着不一樣的可能。
初見存在:在憎恨裡面照見自身
和子的弟弟直治,一個與和子的性格及理想截然相反的生命,過着如無賴一般的生活。身為那個時代的男性,他理應要成家立室,並好好賺錢照顧家庭,尤其是當父親早逝,他被期望要肩負父親的缺位,成為支撐整個家庭的支柱。可是,直治卻是終日賣醉,風流成性,總是發着當作家的白日夢,不單完全沒有理會家庭拮据,還反過來向她們要錢,亦從不表達謝意。
而這樣低劣的人,居然能夠得到母親的關愛,而自己竭盡所能去付出,卻不能得到母親的一點關注,對於和子來說,這是對她所追求的母愛的無情嘲弄,她彷如置身於地獄,在心裡面妒忌他、憎恨他、詛咒他。
但是,這種憎恨會不會只是自己一直以來的自己真正想要,卻連想都不敢想的真正理想呢?她似乎在直治身上看到自己被壓抑的欲望——對成為母親般的存在的不滿,以及對自由的渴望——被那個在她視角裡如同無賴廢人一般的直治給實現了。
直治勇敢地活出別的樣子,一個非社會所設想的男人模樣,而她卻不想承認自己正在逃避她真正想要的東西,她想要的並不是想要成為母親一樣的存在,不然她不用無時無刻神化着母親的一舉一動,彷彿擔心若有一天不提醒自己,就會徹底地否定母親的一切似的。於是只好用力貶低直治,用憎恨、憤怒等強裂的情感試圖忽略掉他的存在意義,正如壓抑及忽略自己的願望一樣,好讓自己不必面對心底裡面積壓已久的欲望,因為這意味着她將步入未知,一個非社會所期望及理解的孤獨世界,一切責任都將由自己承擔,伴隨着的巨大壓力及恐懼使她卻步。
終於,直治的老師,上原先生突如其來的、下流的吻使和子的內心產生內爆,她的欲望被徹底釋放。和子覺得她愛上了這個相貌不討好、總是違反着規範、有老婆的老頭,她在數年間無數次地想像他、意淫他,渴望他的全部。
於此,和子的愛欲挑戰着社會的倫理禁忌,弒母,她親手殺死了心中的母親,而象徵着社會理想,以禁忌形式壓抑着愛欲的母親終於死去。至此,和子發現真正的自己是和她以前一直憎恨的直治,本質上是一致的。或許,人們憎恨的他者如同鏡子一樣,反映着自己內心極度渴望卻不敢直面的東西罷了。
致命的抉擇:死亡,或活下去
當和子發現自己的愛欲時,始發現生命的虛構性,原本督信的那一個生活理想,只是其中的一套特定時代給定的敘事、眾多謊言裡的其中之一,而謊言後面是全然的虛無,即存在本身。
謊言在這樣是中性的,並沒有貶意。沒有謊言的人生僅只意味着痛苦、焦慮和死亡,要活着必須要依靠謊言。但是,當欲望帶領生命朝見存在的虛無之後,生命必須要作出選擇,選擇如何肯定自己的存在,要麼是自我了斷,要麼是用欲望——生命的激情——來創造新的敘事,好讓自己活下去。直治就是至死也堅持着自己原本的敘事,高喊「我就是貴族」來了結自己的生命,這是他對自身生命的終極肯定,這不要求着別人的理解,畢竟大部份人到死的一刻都未必能體驗到存在是無,但它要求着存在者要對自己正直與真誠,他確定了自己的生命形式非如此不可。
那麼,和子的抉擇呢?她是否愛着上原先生呢?並不是的,那只是其中一套她為了活下去而創造的謊言,實際上她是愛着自身生命的熱情,愛着自己的生命本身。她說她愛上上原先生的時候,希望能懷上上原先生的孩子;接著,當她真的懷上上原先生的孩子後,她又希望上原先生的妻子能夠抱着那孩子,並告訴她這是上原先生的私生子。這些都是不可理喻、完全不合理的說話,甚至連她自己也答不上為什麼要這樣做。換言之,和子總是追求着不可能性、朝着死亡,她的欲望並不在意那個具體的欲望對象,具體對象是甚麼並不重要,她的欲望的針對對象僅只是內化在心底的理性與理性所設下的禁忌本身,有一種強大的生的驅力驅使她要不停地跨過禁忌,因為她從以往的經歷認識到,待在沉悶理性之中僅只意味着生命力的枯竭,經歷過價值斷裂的她已經回不去了,她必須為着新的價值戰鬥。
於是,不停地跨過理性的限制,沉浸在自己的敘事中,卻又不停地跨越自己為自己所設下的敘事,一種近乎美學的生存方式,正如和子親口所說的「我想確信,人類是為愛情與革命而生」,和子在自己的生命刻上巴塔耶式的詛咒:以愛欲向自己的生命發起永不止息的革命,至死方休。一切一切都只是為了存活下去,太宰治筆下的和子就是如此純粹。
文:海鹽 @hoiyim_re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