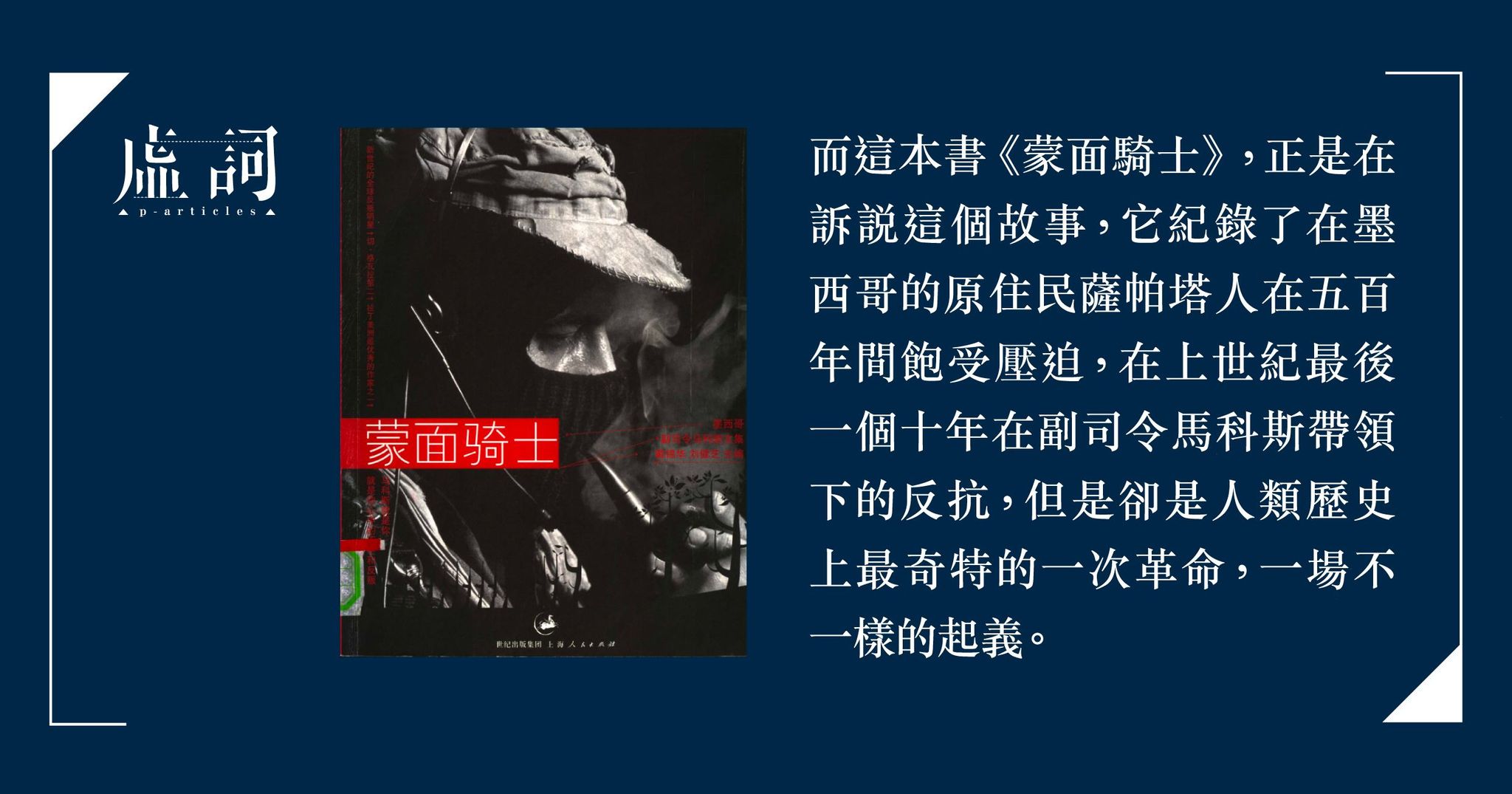評《蒙面騎士》:拿起槍是為了放下槍的革命
書評 | by Louis @ Gunslinger 不曾遠去的硝煙 | 2022-12-23
跟游擊隊員們在晨光乍現的時分穿梭在拉丁美州氤氲薄霧環繞的群山,手握著鋼槍隨時準備為為壓迫者戰鬥,這應該是諸多革命青年心中最浪漫的夢想了。只可惜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握起槍去為革命獻身的機會已然消逝。後現代的革命往往是人們透過社交媒體振臂一呼,呼起不安現狀的千萬群眾憤然走上街頭。可是當運動過後卻是一哄而散,山盟海誓一夜化作烏有,春夢了無痕,一切恍如無事發生,冰冷地刺痛每一個熱切希望變革者的心靈。
縱然如此,但是受夠了就是受夠了(Enough is enough)。哪怕冷戰以降的群眾運動大多以失敗告終,但是受壓迫者的境況和這些男男女女因不公而生的怒火終究是不會消散的,他們的怒火必將會展現出來,永不消滅。而這本書《蒙面騎士》,正是在訴說這個故事,它紀錄了在墨西哥的原住民薩帕塔人在五百年間飽受壓迫,在上世紀最後一個十年在副司令馬科斯帶領下的反抗,但是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奇特的一次革命,一場不一樣的起義。
「我們的詞語就是我們的武器」
世上的革命往往都是在暴力和非暴力之中作二選一的選擇題,但是薩帕塔運動卻是一場異樣的革命。薩帕塔運動是一場「拿起槍但是一槍不發」,突破暴力和非暴力二元選項的革命。雖然薩帕塔人拿起武裝,頭戴滑雪帽揭竿起義,但是他們卻沒有選擇像傳統的革命那樣,用武裝起義的方式推翻政權或者用武力達刻目標。相反,他們「不務正業」,拿起武裝卻血不血刃甚至主動避戰的做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注目。
用戴錦華教授的說話去總結,是「因為(薩帕塔原住民)別無選擇,只有武裝起義,才能讓整個遭受到文明滅絕的印第安原住民的苦境闖入主流社會的視野」。只靠簡陋裝備的原住民深知自己絕對不是全副武裝的墨西哥軍警對手,不過正是因為這樣,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戰鬥的準備。用薩帕塔人的話語就是「我們準備去死,但我們不想死」。他們拿起武器的唯一原因就是為了被聆聽,被世界注視,因為語言更勝槍炮。
「切古華拉第二」
要數薩帕塔運動最吸引人的一個人物,應該就是被戲稱為「第二個切古華拉」的副司令馬科斯。跟歷史上的切古華拉一樣,馬科斯佩著槍抽斗煙,富有吸引力,外貌英俊,文筆辛辣,處處捕捉公眾的想像。然而,馬科斯卻跟歷史上風行雷厲的革命者不同,他的身上沒有血腥革命的血跡斑斑,沒有信奉先鋒黨革命帶來的惡。薩帕塔運動顛覆了二十世紀革命的經典模式,不再是一群或極權主義或精英主義的領導者帶領無產階級暴動,槍桿子裏出政權。相反,薩帕塔運動的武裝起義決議是整個社群決定的,沒有誰是「革命的總司令」,因為革命是由集體所領導。
馬科斯最大的吸引力還數他的文字。作為副司令的馬科斯仿佛有種魔力,他能夠將所有的戰地文章、宣戰檄文以及組織宣言通通化作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當墨西哥政府嘗試詆毁他同性戀的身份時,馬科斯直言自己是「舊金山的同性戀者,南非的黑人,歐洲的亞洲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德國的猶太人,政黨中的女性主義者,後冷戰時代的共產黨人,波斯尼亞的和平主義者,20世紀末墨西哥的游擊隊員,夜晚10點地鐵上的單身女人」,把所有的少數群體串連起來。面對西方記者,他又會打趣地說自己正在準備對歐洲大陸的入侵。如此嬉笑怒罵但又生動有趣的文筆實在令人難以想像他是被墨西哥政府追殺的革命領袖。
在文集中,馬科斯虛構了「甲蟲杜里托」和「安托尼奧老人」兩個極具拉美形象的角色。從甲蟲杜里托是「叼煙鬥的甲蟲」便可以看出,杜里托實質就是馬科斯的化身。馬科斯借杜里托之口,表達出自己渴望成為堂吉訶德式遊俠騎士的渴慕。至於安東尼奧老人則是以一名智者登場,是薩帕塔上千年文化中的人格化縮影。這兩個角色可謂是全書的重點,也是馬科斯對拉美文化和薩帕塔文化理解的結晶。
後記
這本書對於筆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當屬佔全書六分之一,戴錦華先生為薩帕塔運動的長篇大序。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讀起這本書最令人感嘆的是在世紀初新自由主義橫掃一切的時候,原來中國還有左派在乎薩帕塔運動這個反抗新自由主義的微光。戴錦華先生對薩帕塔運動精神的推崇,對女性主義的渴望和高呼「受夠了就是受夠了」的筆觸,更是教人動容。
只可惜以歷史的眼光回望,薩帕塔運動遊牧式的反抗仍然未能影響全球資本主義的秩序,而薩帕塔運動距離馬科斯筆下「選擇當兵是為了不需要當兵的那天到來」距離仍然遙遠。遺世獨立的薩帕塔社區,至今還在面對「娜拉走後怎樣」式的問題。不過無論如何,反抗國家機器決定自立的薩帕塔社區,還是在墨西哥的群山中如他們的目標一樣建立了一個「人人都能生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