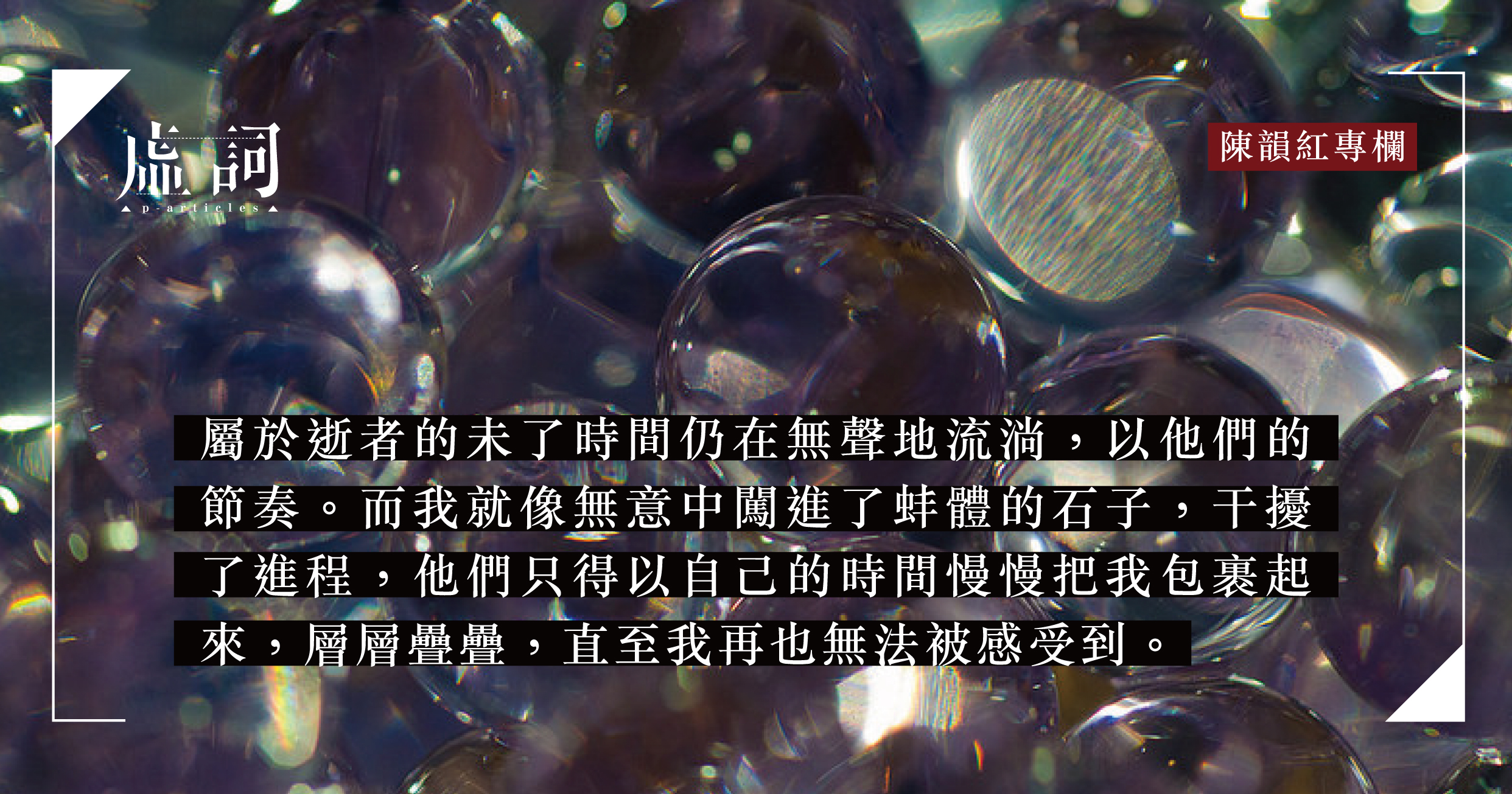明石海峽大橋是現時世上最長的懸索吊橋,建造期間經歷阪神大地震仍佇立不倒,只是地層移動使本州與淡路之間增加了一米的距離,大橋也由原定的3910米延長為3911米,有「珍珠橋」的別號。 (閱讀更多)
【韓麗珠專欄︰越界的誡】把生命綑縛
那時候,我的頭髮跟G的一樣,野性難馴,髮量濃密像許多匹焦躁的馬同時要跑往不同的方向,我從不想拔掉它們,只是想要編一根整齊的辮子,可是我的年紀還不足以理解梳理和編辮子的邏輯,指頭也不夠靈活。 (閱讀更多)
【佬訊專欄】襪戀
佬編的一位朋友,一直對襪子有著莫名的偏好。這位朋友會注意所有人腳上的襪子,在最常見的全棉淨色運動襪以外,對波點間條羊毛fluffy等等物料花紋,都不能抗拒。私底下就算居家,這位朋友也襪不離腳,就連睡覺都會穿著襪子。據稱,全身赤裸只穿一雙襪子,是這位朋友最喜歡伴侶在床笫上的打扮。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