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兩首:〈夢〉、〈走路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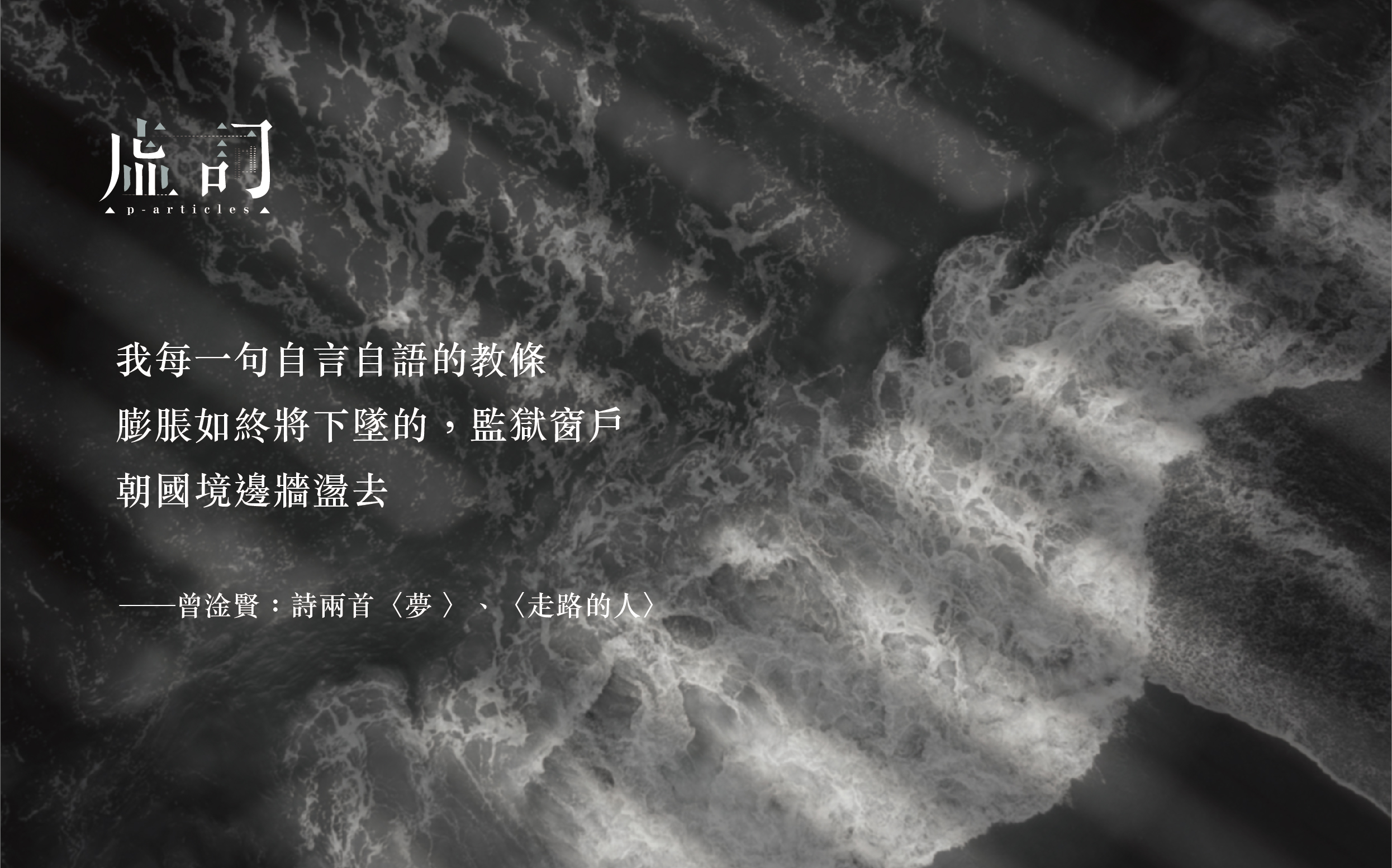
曾淦賢_工作區域 1.jpg
〈夢〉
我做了一個夢
老人與我用古老的語言,互相誤會
又更深沈地潛入另一群
白鷺鷥在五月的湖泊站立
像一所低調的鄉間茅房隨風
搖擺,乾草磨擦的細語飄落
在溫柔夢鄉中的一道水面波紋
當我的宇宙如此寧靜
我不會再想像自己懷內抱著
未曾誕生的孩子,牽著妻
在田野縱橫交錯的小道,散步
揣想晚餐感恩的禱文
幾張嘴巴輕微抖動
恰似與我無關的遠方海洋湧動,但虛弱
在夢裡安眠
收割青銅時代的金黃莊稼
直至黃昏襲來,瞬間入夏
離岸的風,帶著大地蘊藏的溫度
它們離去
我沒有辦法冷卻
地核的熾熱永無休止地離去,散射
歪斜的橘紅色夕陽將擊潰我
秩序永恆如昔,它們校正腦海裡的響聲,敲擊
我每一句自言自語的教條
膨脹如終將下墜的,監獄窗戶
朝國境邊牆盪去
夢是諒解、怨恨、關懷、空洞
〈走路的人〉
每經過疲累的一年
我便獨自穿過崗岩道路
手掌要寂寞的摸著
岩壁上的水痕像淚流的臉頰
一紙快要剝落的肖像畫
繪畫著已經離開的人
海好像越來越遠了
走多少路還是一樣
原地的腳印一樣深刻
遠方路徑的泥土依然平整
我在山中揣想
一個只有飛鳥和花園的世界
那空氣多麼像細碎的浪
撲到我的臉前
又隨寂靜透明的風而散去
要不要排斥所有喧鬧的聲音
像城市在頃刻失去了所有玻璃
一天的澄明
之後是安然無恙的問安
霧景矇矓
我還是沒有走路
大海離我越來越遠了
我只要睡在山地上
不走遠路
只要聽到大地,有海的脈搏
昏迷的暗潮,與他們
隨五月的海流擴散、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