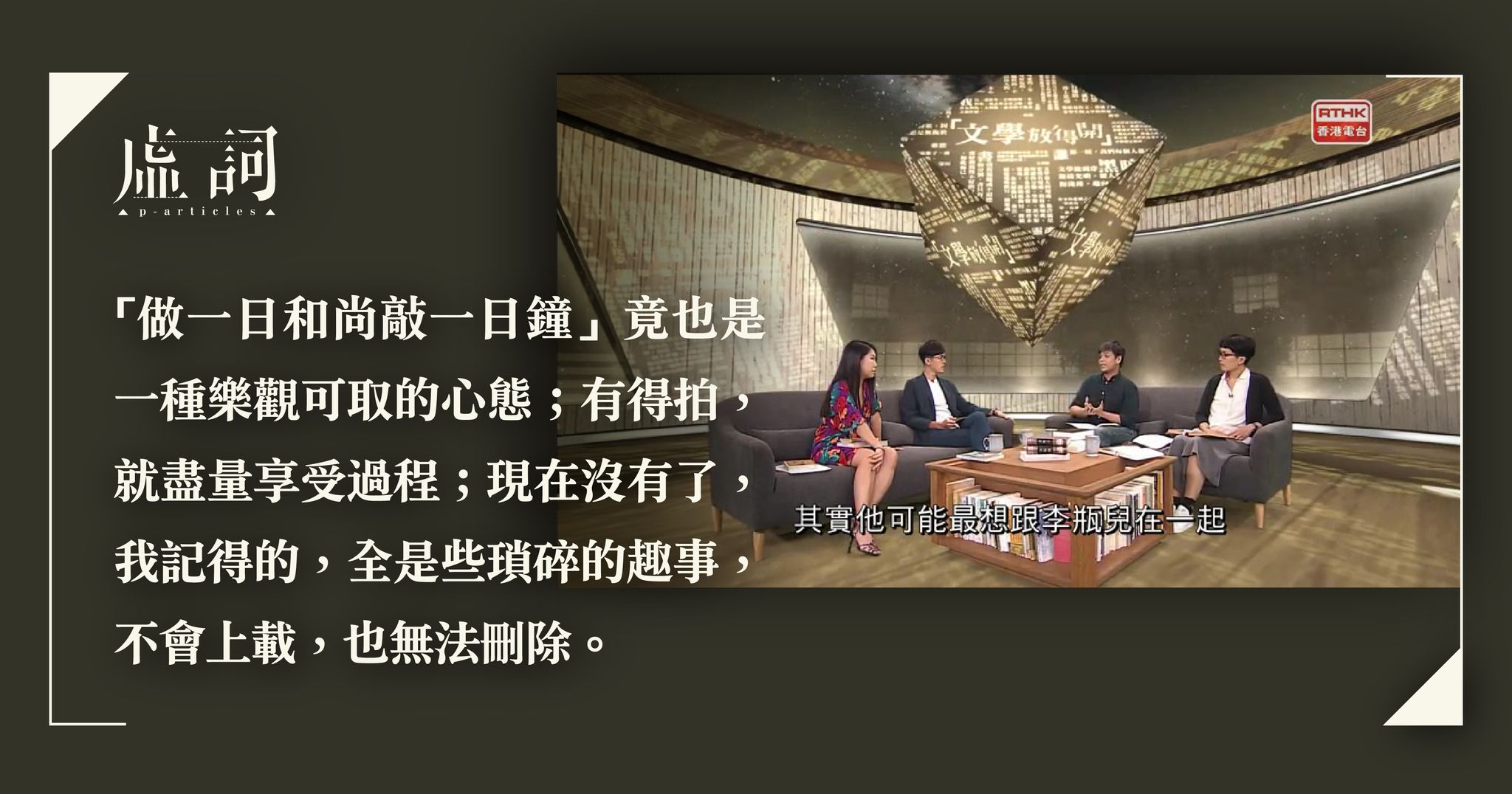不會上載,也無法刪除——《文學放得開》鏡頭之後
張愛玲說:「教書很難,又要做戲,又要做人。」我看上電視做節目也是如此。無論外面發生甚麼事,當日心情如何,化了妝,走進錄影廠,就是另一個人。然而也正因如此,做《文學放得開》,是這幾年生活中最開心的事。現實再怎麼糟,我都可以脫離一會,跟文友談談自己喜歡的文學作品。
喪氣話不說了,志氣bite也用完。只想記下幾個開心的回憶。以下是出賣朋友時段,歡迎進入。
一是錄影《純情金瓶梅》。KY那天穿了一件低胸,米哈跟她說:「你不要坐我對面,我會分心。」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男士要保持專業,很不容易。然後討論節目內容,「潘金蓮醉鬧葡萄架」明顯是眾人念茲在茲的一段,你推我讓一輪後決定交給KY負責概述情節,結果一開機她三言兩語便講完,貨不對辦而完全符合電視尺度。正健大概看不過眼,遂加入戰圈,大談潘金蓮到底是被虐還是被虐狂。如果這一集大家看得過癮,那是因為鏡頭後我們笑到標眼淚。
另一集是更早一點的《古靈精怪》,那應是我第一次跟Nico見面,此人旁收雜學,感覺不務正業。談到《聊齋誌異》中的書生艷遇:「古有蘭若寺,今有蘭桂坊」;那個名叫「網剪」的日本妖怪,傳說中愛在夏天剪爛蚊帳,如果活在現代要剪的是互聯網吧﹖這些爛gag讓Nico笑到說不出話來。笑點低的人其實很可愛,畢竟這世上道貎岸然的人夠多了。
錄影廠的氣壓當然也會隨著外面的世界而變化,會有低沉的時候。正如我在開頭所說,做節目就是做戲,無論心情如何,總得拿出專業的笑容。去年七月二日錄影的一集,某一位講者無端白事NG了好幾次;我建議他大叫三聲「國安大法好」來壓驚,他照做,果然湊效。幽默是我們最後的防線。
拍最後一集的時候,我並不知道那是最後一集,但早就有了「這可能是最後一集」的覺悟。「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竟也是一種樂觀可取的心態;有得拍,就盡量享受過程;現在沒有了,我記得的,全是些瑣碎的趣事,不會上載,也無法刪除。在這樣的年代,參與過《文學放得開》,值得高興也值得自豪。生活在劫難裡,願我們的希望與快樂不被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