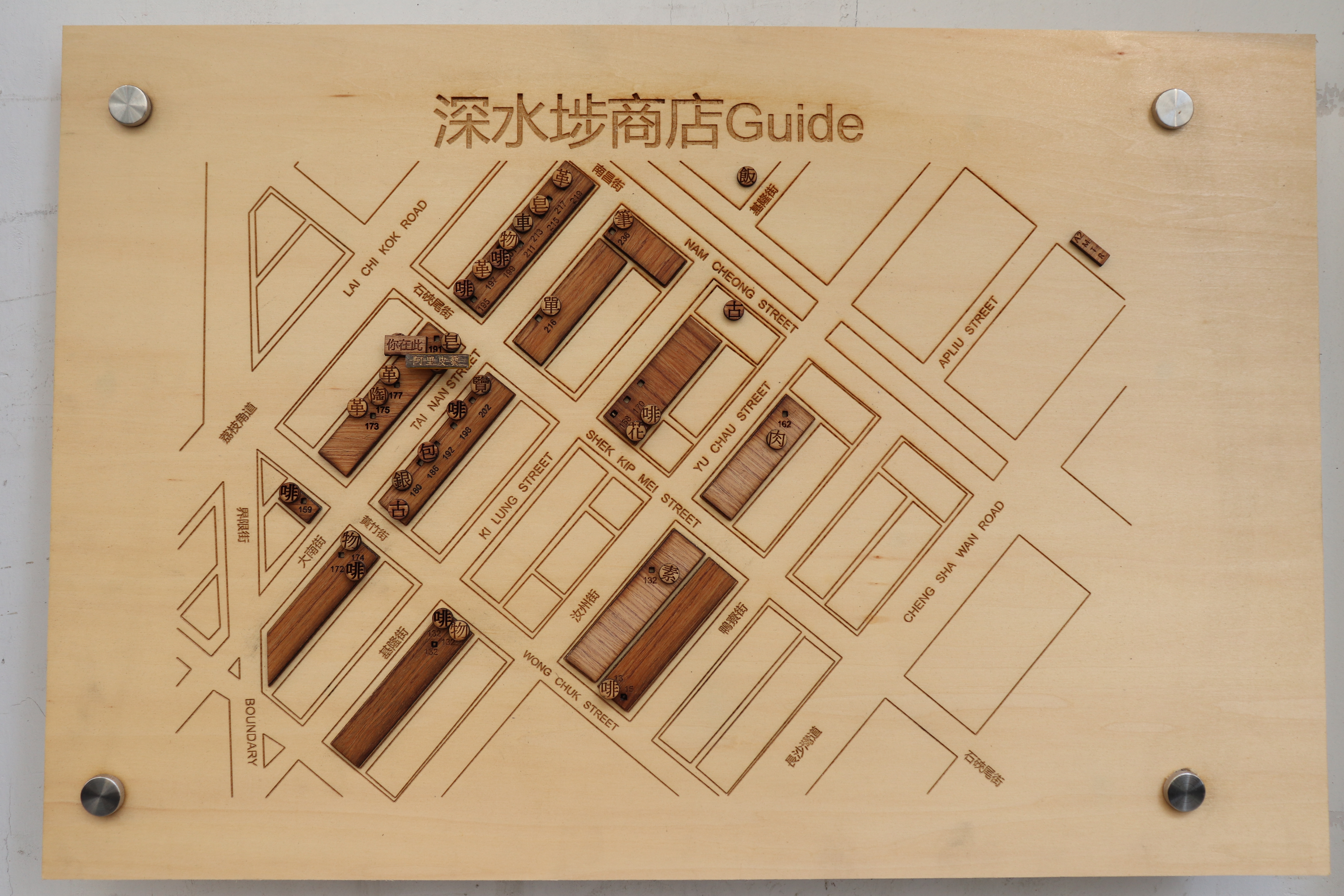【深水埗,我要進來了】林欣傑 X 黃宇軒對談--深水埗就嚟被玩爛?
「Sham Shui Po is the new Brooklyn」的口號,最近在文化圈惹起熱議,深水埗是否逐步走向士紳化,再次成為討論的話題。面對發展商豪言「擺得五年」的命運,「虛詞」找來大南街「openground」的負責人林欣傑(Keith),與香港城市研究者黃宇軒(Sampson)作對談,討論深水埗的未來發展,如何能在既定框架以外尋求突破?
Sham Shui Po VS. Brooklyn
要談深水埗的士紳化趨勢,首先還須從「Sham Shui Po is the new Brooklyn」這句說起。作為區內文青經濟創業者的一份子,Keith說早於三年前已經有人不停這樣講,目的旨在call for action,將這個地方的潛在力量化成金錢交易。「我對這句沒太大反感或好感,因為很視乎邊個講,例如土地/物業擁有者講,跟嚮往外國、覺得個vibe好正的小店店主講,完全是兩個意思。接收者如何接收這個資訊,內化再變成些甚麼行動,是很值得討論的地方。」
因為喜歡區內的氛圍而開店,為該地帶來了另類的活力元素,然而當發展到某個階段,卻惹起財團興趣而將地價炒貴,這是布魯克林士紳化過程的命運。從城市研究的角度來觀察,Sampson覺得深水埗當下的發展,的確與布魯克林很相似。「城市社會學家Sharon Zukin寫過篇文章,叫〈How Brooklyn Became Cool〉,曾經被不少人引用。當很多好hit好chill的鋪頭一齊開,最終卻無可避免地像不可抗力般,令原本好cool的東西消失,變成連鎖品牌;但得意的地方在於,是否一定會係咁?」
因社會運動而衍生的「黃色經濟圈」,也為深水埗帶來微妙的變化。歷經運動洗禮,這些有心的年輕創業者,除了在地區創造了文化價值外,同時亦為市民提供另一種消費模式的可能,讓他們在選擇過程裡加入更多自省,再藉著光顧來表達對共同價值觀的支持,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將深水埗與布魯克林相提並論,Sampson覺得最好的地方,就是藉此思考這兩個地方有何不同。「我們並非要比較她們會否朝同一個方向發展,而是彼此的土地發展機制和發展商運作有甚麼不同,以令過程相似但結果不同。」Keith亦由此引申,90年代由業主主動以低價租給藝術家、hiphop及street art文化重要基地的Fun Factory (2002年前名為 Fun Factory, 後改名為5 Pointz )作為例子,講述兩地之間的差異。「業主突然在2013年把近一萬一千幅graffiti一夜油白,並完全拆毀改建成千多個單位的大廈,當時有八百個artist,因為這件事抗議並告上法院,結果獲賠償六百萬美元,這在香港是天方夜譚。既然土地發展的政策,以至地產商的運作也不同,望著這條如此相似的路,我們在交岔口又可以怎樣做?」

2002年前名為 Fun Factory,後改名為5 Pointz。
「呢度擺得五年,五年之後都要拆」?
四年多前搬來大南街開設藝文地鋪,Keith說「唔使三萬租到兩層」,當時打探後已發現,不少三層高的唐樓早被銀行或地產商「成幢成幢買起」。今年年初,附近鋪位租金突然急漲,加上其他商人近期開始大手買鋪,讓區內的土地業權開始產生變化,也令深水埗士紳化的討論再度發酵。「最近收到李根興(盛滙商舖基金創辦人)對這裡感興趣的電郵,我再向經紀打聽,鄰鋪的租金已比這裡貴上一倍,亦成為新的租金standard。之後再問成交,原來某商舖基金已掃掉五十幾間鋪,就連附近原有的業主和街坊店主也在買鋪,甚至出現爭鋪情況,土地的擁有開始有點變化。」
種種跡象都讓Keith覺得,「擺明有幕後操作進行緊」,但吹風也要有受眾才達到效果,近期深水埗區的成交動作,讓Keith重新思考文化消費背後的價值。「對我來說,文化藝術無論是土地價值或者產業,在香港一向都似沒甚麼角色,然而最近這裡的成交動作,卻似乎並非如此。只是,我們定義的文化藝術,與買入者眼中的是否同一定義呢?好像門小雷曾經在Parallel Space舉辦展覽,當時大排長龍,但這些組織純粹地創造的value,卻沒讓他們賺取太多實質收入,這是很弔詭的地方。」
箇中原因,除了源於「香港有個文化,睇藝術唔畀錢」,Sampson亦引用Sharon Zukin的文章再作解說。「起初在Brooklyn開gallery,因為租金低得無須擔心交租,所以可以搞無法賺錢的東西,當成功帶動人流,alternative的飲食業就透過人流賺大錢。香港沒有這個階段,也沒有畀錢睇藝術的文化,所以經濟節奏很奇怪,藝術很快被飲食取代。當飲食扯高租金,這裡是否還存在純粹欣賞作品的地方,我覺得很困難。」無法支付貴租,商店唯有轉型,Sampson多次合作的「合舍」也不例外,最近開始轉型成半餐飲空間。我們如何理解加租背後所創造的文化價值,以至為何會有「點石成金」的魔力,Sampson覺得正好作為士紳化的新討論。「士紳化本來是指發展令地價上升的過程,但近十年來卻發現,cultural economy受到的關注,比傳統的土地炒賣或投機更強,所以要討論深水埗,亦要考慮到文化力量在經濟上原來也很強大。」
為深水埗周邊帶來改變的元素,除了源自文化消費的力量,Sampson說跟香港市區重建的週期也有關係。「大業主想改變區內氣氛,唯一方法就是收買業權,但這是相當漫長的過程,所以他們就做中短期的計劃,令該區變成其他人perceive可以去的地方,文化消費亦從而誕生,但殘酷點說,只是因為長線操作未完成。」相對的例子,就是鄰近的長沙灣大執位。「市建局收地起樓起豪宅,令該區徹底大換血,但即使很大規模,沒有人特地會講是否士紳化。深水埗目前的情況是,既得利益者暫時無法做到甚麼大動作,就先令這裡做啲中短期嘢,而這個狹縫讓年輕創業者做到他們想做的事,但當上面郁,就隨時要搬。」
要在這個狹縫裡求存,亦如一場時間競賽。不少當區的持份者和發展商也豪言,「呢度擺得五年,五年之後都要拆」。在這段time gap裡,Keith看重的是即使最後無法改變結局,也不能眼白白地甚麼也不做。「同一句說話,另一個社福機構也講過,悲觀地說都係要拆,但拆之前還可以做到甚麼呢?那怕叫價能力高啲也好,中間做到甚麼也好,在這五年裡,我們可以add到甚麼value?」
文青經濟創業者是拉高樓價的幫兇,還是價值創造者?
文青是否士紳化推波助瀾的幫兇,在坊間亦有不少論述,但當城市選擇了以「土地生金蛋」的方法發展,已註定令很多低回報的產業難以運行。然而,這群對香港懷抱美好追求的創業者,背後理念也是希望凝聚更多同路人,他們的經營模式比起一般連鎖大企業,往往來得更加真實貼地。Sampson認為深水埗的年輕創業者,只是希望能有空間,去做自己想做而香港沒有空間可以做到的事。「發展商如何能令人感覺這裡適合放酒店,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令人感覺它不是草根社區。藝術類的店鋪在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幫助了這件事,但對這些店主來說,他們不過是想buy time buy space,我覺得也不能過度責怪年輕創業者。」
另一個文青經濟創業者常被質疑的地方,是推高了租金繼而逼走原有老鋪。然而,Keith坦言從自己與商戶之間的閒聊,得知某幾條街的很多老鋪店主「其實好恨走」,或是等好價將鋪租出,或是靜待成幢被賣走。反而,如何保存舊區的獨有魅力,才是Sampson更為關心的議題。「Artist到舊區非只享用,而是想跟當區有互動,這本身是很好的事。現在市建局花了許多錢也有資助很多文化計劃,其實他們如果真的有心,可把資源和心思多花在思考如何平衡這些創業者的文化力量和舊區本來的價值,甚至可以奇想,可否介入租金暴漲問題。」
從過去多年香港的城市規劃所見,彷彿市區重建已跟興建豪宅劃上等號,但隨著文化消費成為被認可的經濟力量,Sampson說近年市建局的政策亦有調整,像旺角「上海街618」就是例子。「當市建局鏟走一整個區,租出店鋪時,有否想過讓年輕創業者可以做甚麼?有趣的是,市建局已開始懂得這樣做,像『上海街618』就很積極找文青店進駐,由此亦可見年輕創業者或文青喜歡的店舖,已成為一股被recognized的經濟力量。」雖然「上海街618」的評價一般,執行效果也不及預期,但Keith認為這個概念,或許能夠成為尚無租金管制之下的另一條出路。「如果將這個concept放在不同地方,甚至是在一整片區域作planning,又是否可行呢?例如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講明一定要近地產商,一定要在這個地方開博物館,某些區域給特定的持份者經營,發展商和政府交換條件到這個level,我不知道是否要做到咁,但這卻仿似是不做租金管制的其他option。如果政府不做,退後一步想,像某商舖基金買了五十幾間鋪,他會否有這個vision只租予年輕創業者或想開文化藝術的人呢?」
黃宇軒(左)與林欣傑進行對談。
年輕創業者作為持分者的新框架
當發展的想像空間被拓闊,士紳化的討論也不再局限於舊有框架。坊間有種最左翼的說法,認為樓上住草根居民,樓下就只能有草根店鋪,因此文青咖啡店的進駐,會令很多原本的店鋪消失,但Sampson覺得很難如此斷言。「這是個可持續街道生態的問題,如果有人想來開cafe,我由天水圍搭車出來飲咖啡,可否被當成持分者呢?其實都可以係。如何將草根味與文青心目中的chill和vibe混合,就是共同經營的sustainable economy。這些店鋪甚至業主,有否責任令本來的草根店舖得益,幫襯的人有否責任take care of 其他店鋪,都很值得拿出來討論。」
喜歡探聽區內行情的Keith,亦講到自己當初租借大南街地鋪時的經歷。「這個鋪位,之前有人出貴租想做海產,業主唔做;便利店想來開鋪又唔畀,原因是不想打搞隔鄰的老街坊。我不知道多少業主會有這種意識,但如果他們本來有意識,只是不知如何凝聚,民間可否變成一種無形的監察力量?」這種公民社會參與的文化,近年開始在倫敦、柏林等地衍生,居民不再單靠有權力的人負責質詢,而是自行成立監察隊,要求店鋪對當地有所了解才開業。類似的概念,Keith說同樣是他與另外幾位店主醞釀的想法。「若不靠民間的自我監察或凝聚力量,只會大石砸死蟹。柏林玩爛一個地區可找下一個,但香港沒幾多個地區可再被玩爛。」
深水埗是否會如某些人所言,最多只能擺五年,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但隨著財團不斷「種鋪」,Keith深感已對樓上居民逐步帶來影響,最近的討論正好作為尋求突破的契機。「那些將會發生的土地爭奪或買賣,其實我們也沒甚麼角色,但如果連討論也不討論,就真的會由它發生。」因此對他來說,監察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尤其經過遍地開花的社會運動,追求公義的心早已植跟於社區每個角落。「那怕是街坊自己組織,抑或商店街的店主組織,甚至是從業主的層面,也是因為有了這個討論,年輕和老店店主才會開始傾,看看五年可否唔玩完,會否有其他方法冇咁快玩完,甚至永遠唔會玩完呢?」
拆樓重建並非唯一出路
在年輕創業者作為持分者的新框架下,近年興起的咖啡文化,加上社會運動誘發的全新消費模式, 亦令消費者可以因應店主的價值觀決定是否光顧。這種消費的自省過程,Sampson認為更可延伸至其他城市發展的議題。「以前最多講剝削咖啡農,現在會講很在地的政治。對於是否認同店主的價值觀,亦可關乎很多社區的事情,例如開喺邊、會否嘈親隔離等,這些都可以慢慢放進去。」然而,這種共同創造的經濟力量,最後到底會被誰吃掉,Sampson覺得問題所在,是如何讓它不被吸納和變得邪惡。「以前去咖啡店,很少會跟店主咁friend,但現在的消費卻更似走進社群。店主如何賺到錢,我們如何飲到咖啡又可將經濟力量抵抗某些東西,其實彼此可以共同商議一下。」
當文化價值可以反映在地價之上,「市區重建=拆樓」亦似乎是可以扭轉的定律。對Sampson來說,若能保留當區魅力,又留得住草根階層,同時平衡到某種店鋪的經營,加起來就無須只有一條路,關鍵在於創業者做生意之餘,是否有心兼顧區內的周邊社群。「如果新店舖的存在,能令舊鋪和邊緣嘢生存得更好,其實它們不一定是扼殺,反而可能是種促進。」打破既定框架,將輿論轉移到其他層面,也是Keith對後續討論的期望。「大家都只用以前的框框去看development,但如果並非在這個框框的話,我們要怎麼做呢?如果大家都能意識到,當中也有這個value,原來拆樓並非唯一出路的話,就會帶來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