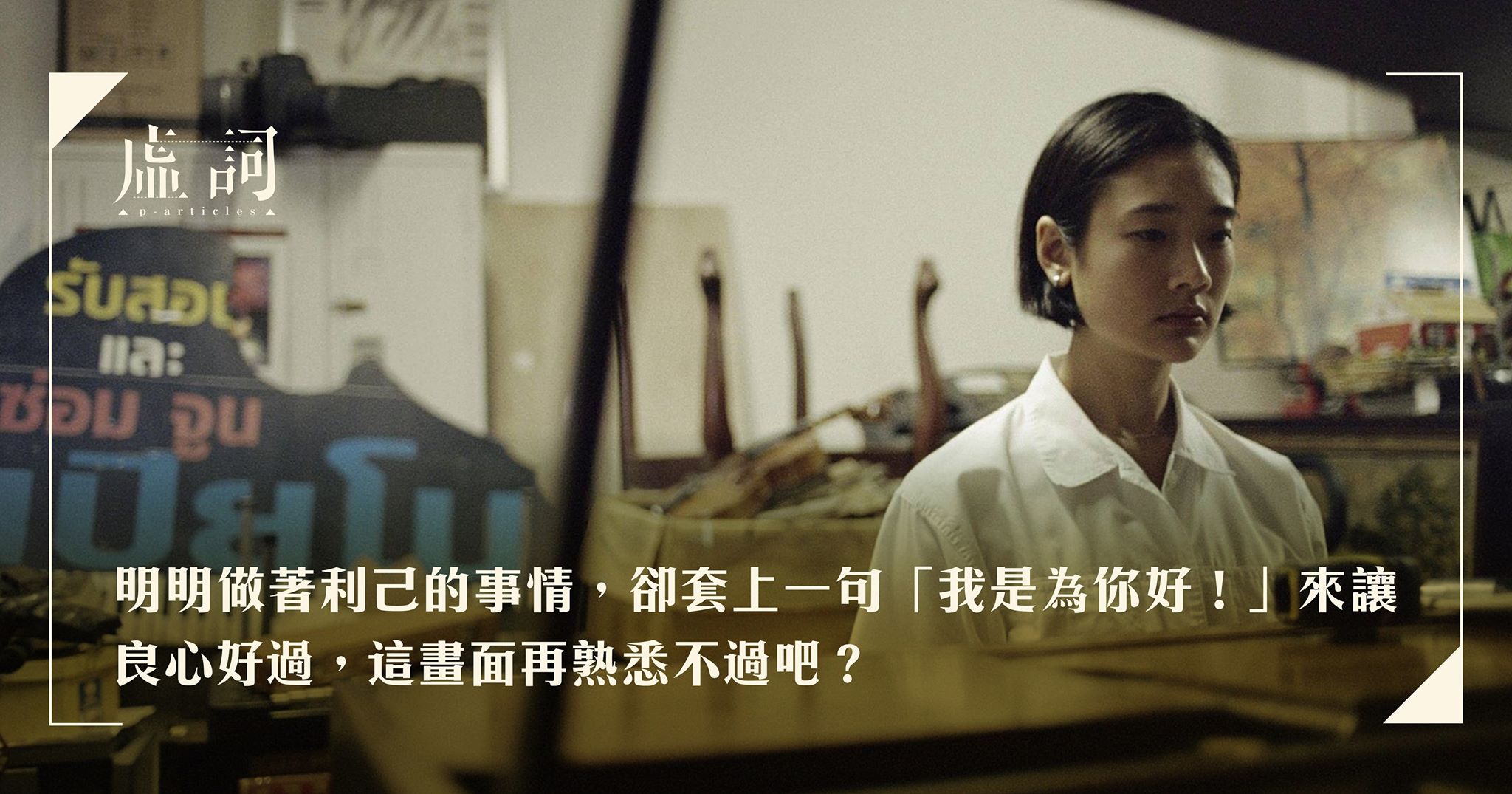如片名一樣,導演納華波全片採取「斷捨離」拍攝手法,從畫面色調到配樂都相當簡潔,澳門「戀愛.電影館」影評人鄧志堅尤其欣賞電影結局,將整個故事從頭寫實到尾。 (閱讀更多)
《追擊黑水真相》:追擊真相,還是追擊揭露真相的人?
小人物面對龐大的勢力,想要利用朽壞的制度去爭取公義,注定是徒勞無功。Robert痛切地認識到,正如一位只完成了基本教育的受害工人所說:平民百姓不可能跟大財團鬥爭,我們只能依靠自己、保護自己。 (閱讀更多)
《家路》:天涯何處可為家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家園被毀,我們又知道如何回家嗎?在日本經歷三一一之後,電影《家路》探討了這個問題。也許災難過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要怎樣孕育新生命,和孕育怎樣的新生命。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