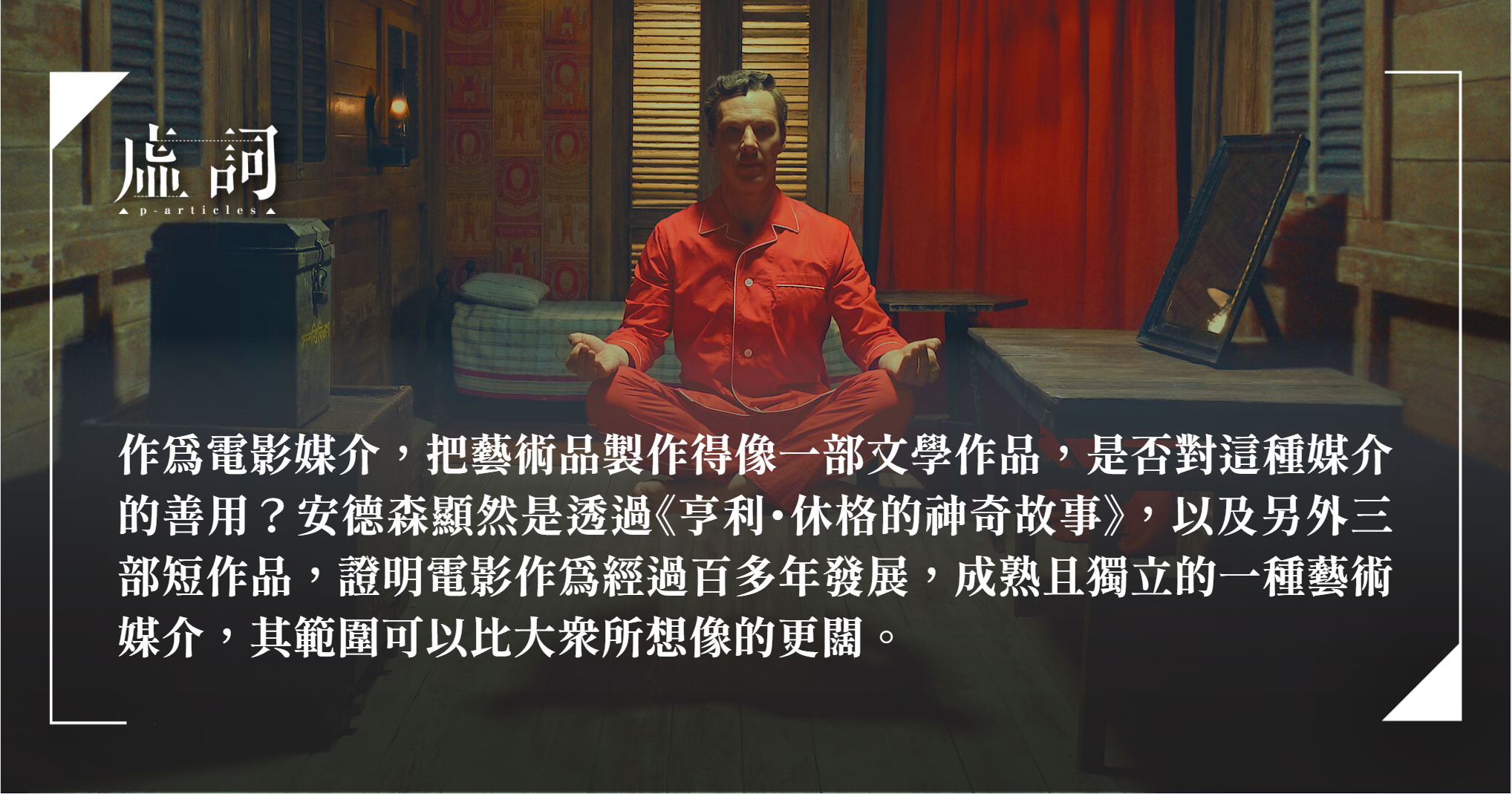《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文學對電影的逆襲
近來,魏斯・安德森(Wes Anderson)以短片導演的身份出席了第八十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帶上了片長41分鐘的新作《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The Wonderful Story of Henry Sugar)。電影講述一個化名為「亨利・休格」(Henry Sugar)的夢想家無意在圖書館讀到一本奇怪的著作,著作裡一位老者從另一位被尊稱為「偉大瑜珈士」的大師身上學得了透視之術。休格因此跟從書中的指引,日夜苦練,能從撲克牌的背面得知牌面的圖案。他亦因此成為富翁。
故事當然沒有在此終結。事實上,電影的敘事者不斷向觀眾強調,故事並不會像傳統般,在某些看似應當終結的地方作結。這裡電影展示了一種三層敘事的視覺:向讀者講述亨利・休格的敘事者,休格的故事,和休格所讀的故事。這種處理手法,是要向觀眾展示一種新敘事的可能性。
《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的原著者是英國童書作家,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而安德森亦並非第一次把他的小說改編,搬到大銀幕上。早期作品《狐狸先生無得頂》(Fantastic Mr. Fox)就出自達爾的手筆。這次的《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連同另外三部短篇在Netflix 上發放,可被視為安德森的一次轉型。
電影鏡頭運用、場景佈置和色調的調節,自然保留了他一貫的拍攝風格;不同的大膽嘗試,在於演員的表演,和對白的實踐。在電影裡,一名演員總肩負了敘事者的角色,把正在發生的事情向觀眾如實報道。本來電影之所以有別於文學作品,是因為電影能透過影像語言,取代一切文字的描述。但這裡安德森決定來一場文學的逆襲,把大量文學獨有的敘事元素,以電影的方式呈現。挑戰了好些藝術家們對藝術形式的固有理解。
在美學上,這裡涉及到所有媒介特異性(medium specificity)的問題。作為電影媒介,把藝術品製作得像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對這種媒介的善用?安德森顯然是透過《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以及另外三部短作品,證明電影作為經過百多年發展,成熟且獨立的一種藝術媒介,其範圍可以比大眾所想像的更闊。
文字的運用是安德森這系列作想要處理的問題,作為改篇,他在自己的神來之筆。以當中的《毒》(Poison)為例,其對白並非一字一句跟隨原著,有導演本人的、戲劇式的詮釋。故事講述一個男子在床上閱讀,發現一條毒蛇悄悄走進了被窩,男子因不想驚動毒蛇,只好躺着不動,靜待敘事者和醫生設法營救。這時男子認為蛇就在自己的肚皮上,只能用不合文法的簡短句子求救。如此,觀眾被迫反思文字的本質問題。
又或者,在《亨利・休格的神奇故事》,導演刻意要和觀眾展示休格所讀的故事書,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符號指涉意味。電影以這種方法,把自身以至觀眾帶到文學,但同時文學的介入又使人不得不反思電影的本身。是文學的一場逆襲,也是藝術形式的一種突破。作為愈趨公式化的荷里活的一員,安德森的嘗試不但大膽,而且尖銳而對題。
自電影發明至今,經多年的藝術化,它對文學寫作有顯見的影響(不論是好是壞)。實情是,不少作家開展了一種以電影視角為本位的寫作方法學。但看電影本身,它作為主流媒介,自身作出的變化並不好。因此,從制度的必要性去看,一切電影的實驗都是值得鼓勵的。
又或許,經歷今次試驗,安德森能以長片的方式把電影和文學作有機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