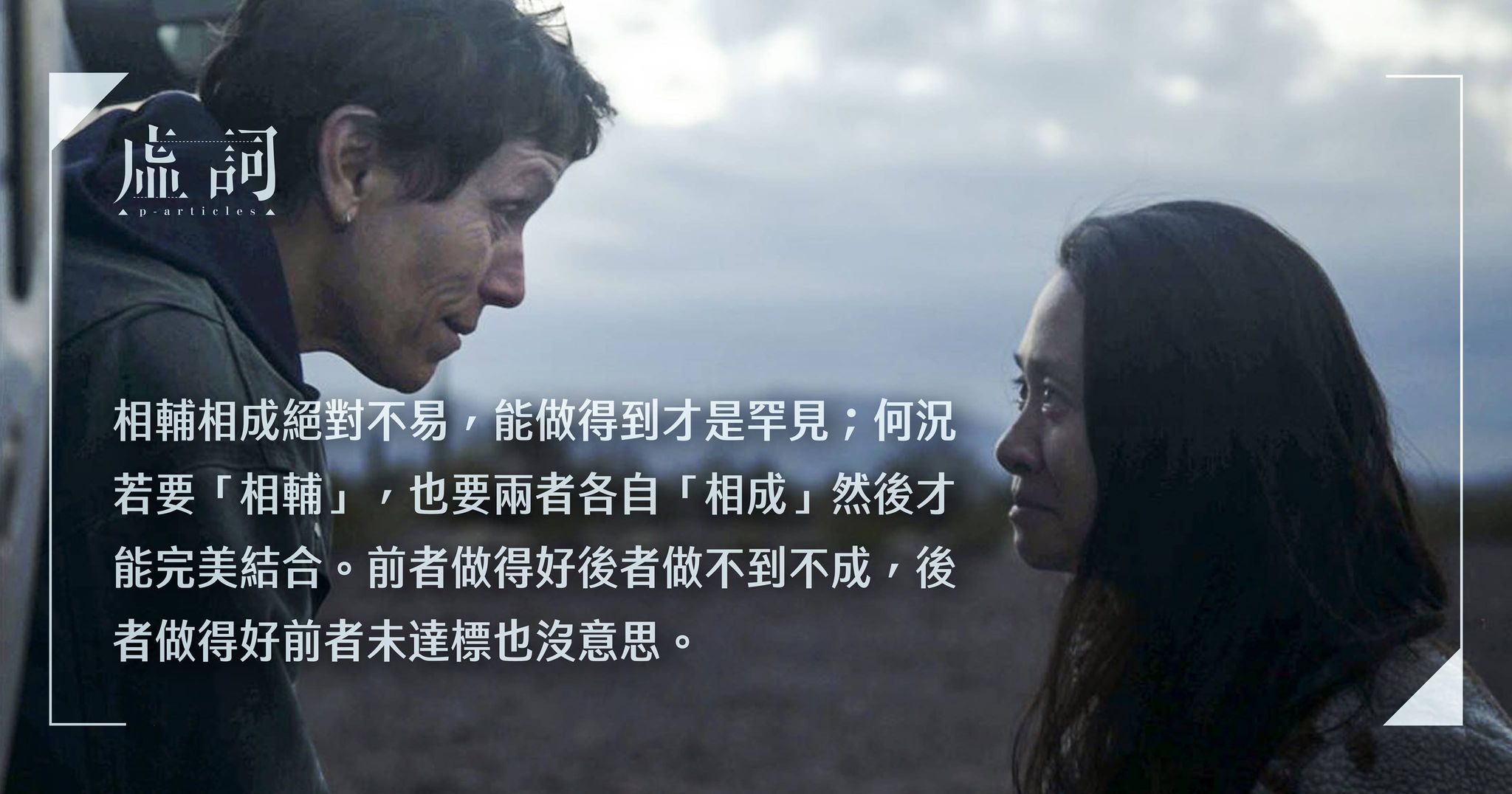閱讀《我香港,我街道2》的兩個關鍵詞
2020年出版的《我香港,我街道》,書中作者都是香港作家,名符其實屬於「香港」的書,不過,一年後《我香港,我街道2》出版,眼界開闊了,不論是香港還是外地的作家,只要熱愛香港,誰都可以寫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發生的事。葉嘉詠從書名的兩個關鍵詞:「街道」和「香港」,細談此書,並了解由「街道」組成的「香港」,再進而了解香港的故事和歷史。 (閱讀更多)
《東京蒼穹下》:我被「社會」逼得走投無路
影評 | by 馮曉彤 | 2021-06-15
人們總是叮囑更生人士:「記得與人保持聯絡,不要脫離社會。」但如果社會並不美好,而人類是不信任的、攻擊性的、敵視的?馮曉彤從《東京蒼穹下》下看出了社會不公義和各種制度對人性的腐蝕。 (閱讀更多)
火,不止憤怒——淺析洪慧《借火》中的「火」
書評 | by 淑清 | 2021-06-13
從詩人洪慧的第二本詩集《借火》裡,淑清看出了「火」的不同意象。詩人「借火」燒「世間所有該燒之人」,「不用改革和火了/我們自己就是」,以「火」傳遞情感及理念。火既是雄性之火,同時也是更高層次的淨化之火、永恆之火。 (閱讀更多)
評舞台劇《時光》——劇場裡的皇帝炒飯
早前在文化中心劇場上演的戲劇《時光》,原著劇本取自哈洛.品特,但新八卻認為期待並沒變成相應的滿足,正如《食神》中的皇帝炒飯,不論賣相如何金壁輝煌,用料如何上乘,最基本的還是:「要用隔夜飯炒呀。」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