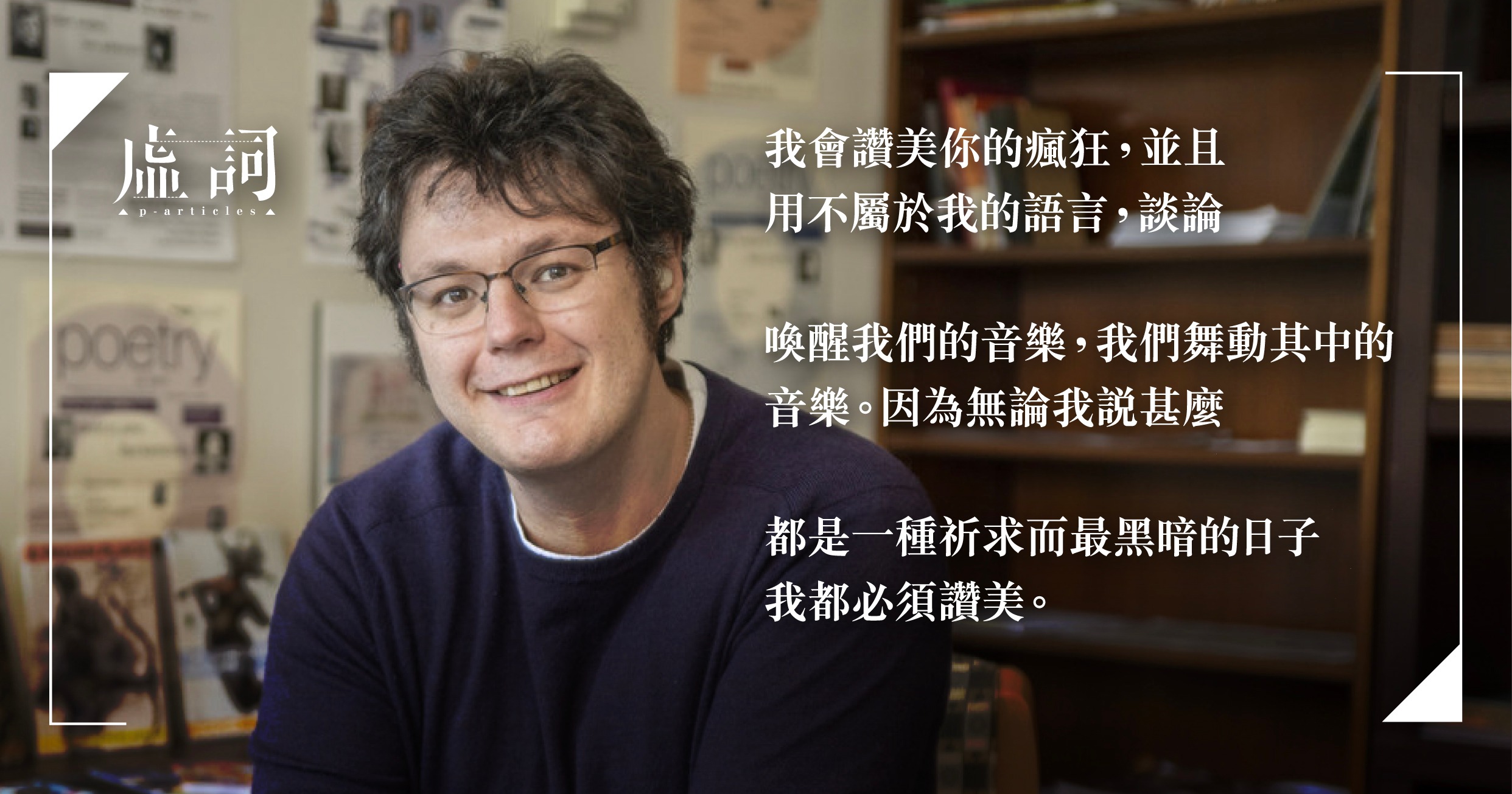侵略詩輯(三):血流激盪整夜,堅信還有下一個黎明
詩歌 | by 羅貴祥、彭礪青、鄭點 | 2022-03-10
烏克蘭局勢變化莫測,此刻難料下一個剎那,傷亡與囚禁,逃離的倉皇,羅貴祥、彭礪青、鄭點寫詩感懷。生命剩下唯善唯惡,終有一天,我們會抵達他們的海港,彼此問起健康和近況,穿越密集的砲火迎接明天。 (閱讀更多)
詩三首:披靈 X 藍玉雍 X 曾子芯
詩歌 | by 披靈、藍玉雍、曾子芯 | 2022-03-03
披靈、藍玉雍、曾子芯分別以〈故鄉〉、〈影子們的花園〉及〈故鄉〉為題,傳來詩作。故鄉萬物,早已寂靜成謎,那條一直沒有盡頭的道路,日漸變為一道漫長的凝視,孤單地想像成一座重重的花園。 (閱讀更多)
侵略詩輯(二):當我仍然可以選擇,這世界還餘有善良
詩歌 | by 飲江、劉偉成、璇筠 | 2022-03-02
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飲江、劉偉成、璇筠寫詩感懷。戰爭打響了,軍人各自在對方的戰場說愛,同時說夢。相互猜疑、糾纏、旋繞,映在眼底是仇恨的風暴,灼熱的真相卻提醒我們,如果仍可選擇,這世間還餘有善良。 (閱讀更多)
侵略詩輯:孩子問我,戰爭是為了甚麼
詩歌 | by 朱少璋、淮遠、熒惑 | 2022-03-01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火遍布基輔等地,朱少璋寫詩致普京、淮遠、熒惑亦寫詩抒懷,要是不再有戰爭,就不再有人寫戰爭詩,然而只要暴君一日仍在,這都成為了絕無可能的想法。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