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酒呀!我叫你酒呀!】你永遠不知道那是最後一次酩酊大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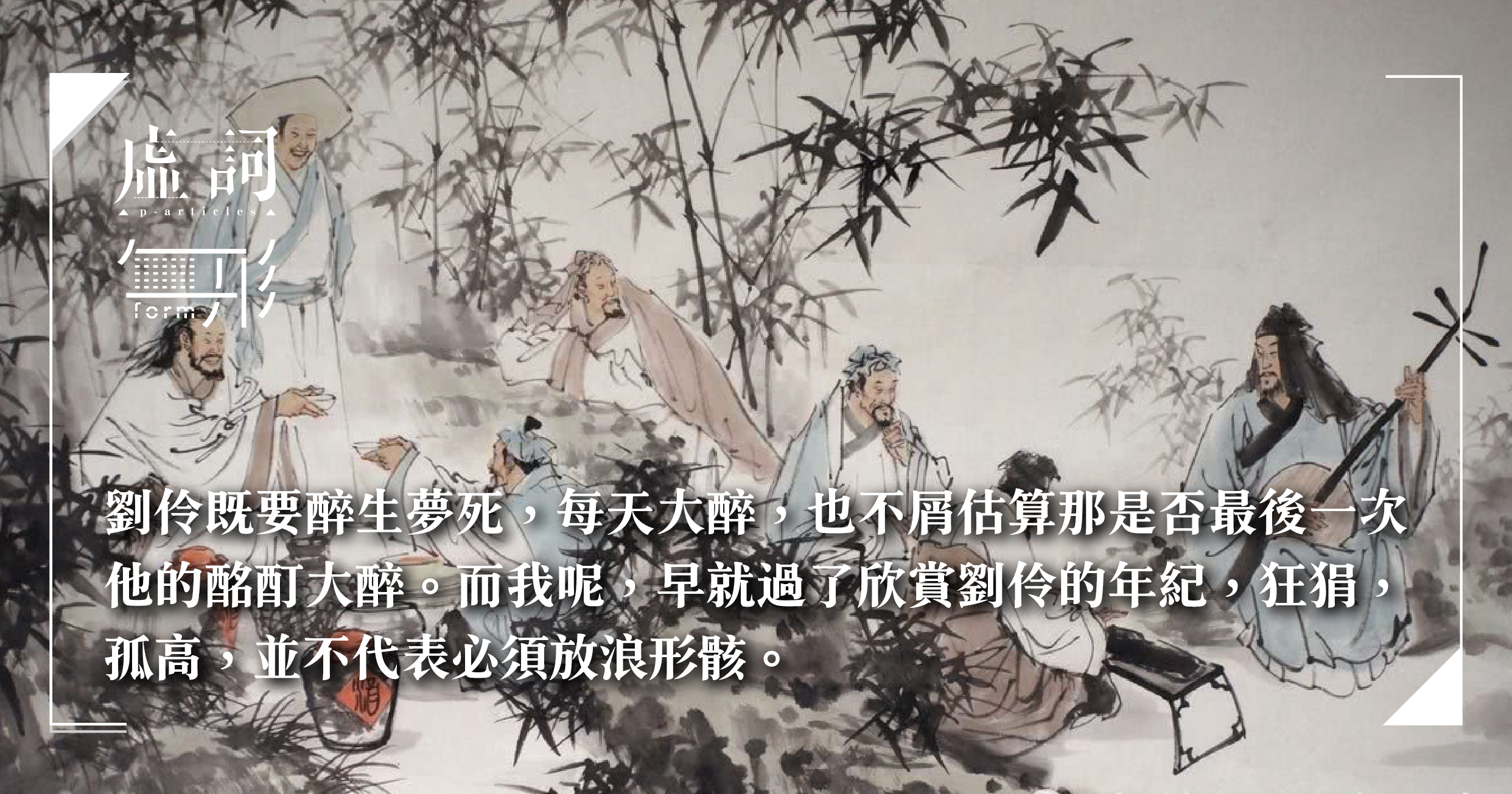
270810896_647887509561648_6262213438385077850_n.jpg
家族中幾乎沒有嗜酒者,更莫說是酗酒的人。這重基因對我產生兩個影響,一是我不用經歷因酗酒而導致的任何家庭悲劇,二是我自小對酒的想象非常貧乏。我不了解酒精為何物,酒醉又是何種感覺,記憶中關於「酒」的形象,都與「色」連接——卻是經過流行媒體磨滑了的潔淨版本。多年前有個經典電視節目叫《今夜不設防》,城中三中佬才子一手摸著酒杯底,嘴巴口沫橫飛說著擦邊的色情話題,席間總有美艷女星作客,眾人話到酣處,適可而止的毛手毛腳自是少不了。節目深夜播出,我瞞著熟睡的家人偷偷收看,似乎開始明白「酒色」的美妙之處——當然這也是一個潔淨版本。
《說文解字》說:「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從水從酉,酉亦聲。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解釋非常有趣,先不說酒為何物,而是說酒的倫理意義:「就」指「導致」,酒能導人向善或向惡,或令事情變好或搞砸。上古傳說,儀狄是酒的發明者,大禹喝至酩酊大醉,醒後大讚酒之美好,但心裡卻知酒之禍害,於是開始疏遠儀狄,也下令禁酒。十多年前,香港某高官被發現與風麈女子外出,最終受壓下台。下台前他留下一句:「… alcohol is not very conducive to good behaviour.」 酒精不導人向善,儼然就是《說文解字》的現實注腳,也說明了「酒色」的共生關係。
但我對酒的經驗,跟色毫無關係。酒於我,更像延綿多年的成人禮。跟初吻和初夜不同的是,你品嚐的第一口酒,未必會在記憶裡留下痕跡,因為少年的你可能會想:酒太難喝了,以後不會再試。結果在某個不知不覺的時刻,你忽然醉了,並初嚐酩酊大醉的滋味。我是在一間露天大排檔裡,初嚐醉酒的感覺,當時肚子裡裝滿了劣質啤酒,混合了不少蠔餅、鵝片和椒鹽九肚魚的殘渣,四周則是一群同宿男生野獸般的叫囂——這絕對不叫「勸酒」,而是一場群體挾逼,以語言暴力逼迫一名未經酩酊的少男完成一場進入成人男性群體的儀式。
那晚我已不大記得是怎樣過的,可能在大排檔現場就已經「劏」(嘔吐)了,或是在回程的士裡?抑或在宿舍大堂的梳化上?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初醉之後,你就成了一個醉過的人,懂得酒精的妙用和邪惡。波特萊爾寫過一篇叫〈人造天堂〉的文章,分別討論了大麻和鴉片,在一些中譯版本中,這篇文章都與另一篇叫〈酒與印度大麻〉的文章如孿生子般共編在「人造天堂」的書目名下。台灣作家唐諾寫過一篇導讀,其中問了一個問題:到底波特萊爾有沒有用過大麻和鴉片呢?我們知道,波特萊爾有巴黎詩人的放蕩,四十來歲就死於梅毒,但這不表示他一定是個癮君子。正如唐諾分析,《人造天堂》兩篇文章寫大麻和鴉片,比較像文抄公,不只引述別人的歷史考證,就連別人感官經驗的大引特引。反而寫到葡萄酒,卻是謳歌的。最終唐諾主觀地猜想,波詩人有用過大麻鴉片。但他倒沒追問詩人,有沒有喝過酒呢——當然,這問題太笨了吧,詩人怎能沒酒呢?這個「怎能」甚至去到一個理所當然的程度,叫唐諾也不大花氣力去寫,波特萊爾是怎樣寫酒的。
那就由我來說好了。波特萊爾寫酒的好處,是他把酒當對象,而不是媒介。詩人說,酒與人相似:「人們永遠不知道可以尊重它或蔑它、愛它或恨它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它能做出多少高尚的舉動或可怕的罪行。我們對它不要比對我們自己更殘忍吧,還是平等地對待它吧。」李白醉酒,會對月說話,對影說話,論境界居然不及波特萊爾:他將酒直接當成傾訴對象,當然傾訴是內在的,「我好像有時聽見酒說話:——它用心在說話,用一種精神才能聽見的精神的聲音。」用精神分析的說法,這是本我與超我之間的鬥爭,暗合「酒就善惡」的古說;文學地說,酒即凡人的詩,用以挖掘內在本我。正如詩人說:「地球上有無數的無名之人,睡眠不足以平復其苦。酒對他們來說就成了詩歌。」
幾年後,我在一次波特萊爾式憂鬱的狀態下,再一次酩酊大醉。這次醉,不再是雄性汗臭式的成人禮,也不是青春的狂喜,而是對自我幽微內心的傷口及焦疤進行揭發和治療。那是一間K房,男女比例均稱,裡面有我心儀的女生。然而由於種種情結和偏執,我無法直抒情愫,只有委婉地憑歌寄意。當年的K 歌,高亢而公式化,往往能刺中心坎,但又永不如想象中那般椎心。此時酒精開始發揮作了,當酒精入血,我內心的憂鬱就被放大,當中雖有對那名女生的愛慕,卻又不只於此,而是蘊含著對時代空洞的疏離感。那幾年我文青氣盛,此時我把歌唱至高點,酒精直接導致我破音,我摔掉咪高峰,狂哭兩聲,頹然地攤在梳化上,斜眼向那女生看去,只覺她的形象漸漸褪色,跟著我所討厭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一同飄遠——
——慢,我似乎搞亂了時空,這不是一個單一場景,而是我三十歲前大量雷同場景和情緒的疊影,後來我稱之為文青時代,一種在自我心理防衛機制運作下的退化情感(regression) 表現:用「醉」來掩飾對自己行為幼稚的羞恥感。就在文青時代結束前的一天,我做了兩件事:一,寫了一首關於失敗的情詩;二,跟友人喝酒,那晚我再一次酩酊大醉,卻不再是為任何文青式的憂鬱,而是用作跟即將逝去的青年時代道別。那是我對上一次酩酊大醉。
此後我才自覺開始懂得酒——不是那種知性上或品味上的懂得,正如我有一些朋友是品酒專家,對各種酒類如數家珍,這點我就完全不懂了。我說的「懂」,是指我知道怎樣在「酒」和「醉」之間保持一個節制的距離,酩酊大醉不是對酒的敬意,酒醉三分醒才是對酒中自我的基本尊重。尤其是,當我回看文青時代的我,每次都將那三分醒一散落地,任輕狂肆意,我就覺得羞家極了。
然後我想到酒仙劉伶。
劉伶最著名的事跡,莫如他發酒癲在家中祼跑,友人見狀嘲笑,他就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家,房屋為內褲,你為何走進我的內褲裡呢?」關於這則記載在《世說新語》的八卦,一般解讀是劉伶等竹林七賢尚黃老之學,自命清高,不屑與俗世同流。另一則事跡則更驚世駭俗了:據《晉書》載,劉伶常常拿一壺酒,就坐上鹿車走入森山,並著隨從把鋤頭帶來,並囑咐:「死便埋我。」這直如一個有自殺傾向的酗酒者自白。據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那個著名考證,魏晉名士流行吃五石散,即是啪丸仔(嗑藥)了,我可以想像,劉伶的醉可能不只是酒精作祟,或更有藥物影響。其實魯迅文中不只說竹林七賢,也有跟建安文人比較。相對而言,建安文人表現得更恢宏,更慷慨,氣魄也大。例如曹操論酒名句:「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據說又是酒的發明者,曹阿瞞畢竟有帝皇之志,整篇《短歌行》熙熙攘攘,微醉沉吟,就是要引出最後一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綜觀建安時代,跟竹林七賢時代的表面統一內裡腐敗的政治環境比較,縱並稱魏晉,卻是兩個宇宙的事。
於是我又想像,曹操要得天下,自然不會輕易喝醉了;劉伶既要醉生夢死,每天大醉,也不屑估算那是否最後一次他的酩酊大醉。而我呢,早就過了欣賞劉伶的年紀,狂狷,孤高,並不代表必須放浪形骸。我心慕嵇康的亮節,也不避阮藉的沉忍,而他們都沒有酗酒的記載,品位永遠在劉伶之上。在我構思這篇文章時,我正與友人在一間安靜的酒吧裡,啖著本土品牌的手工啤。我微醉,耳際略熱,便大談我在荒誕時局裡的忿恨。友人說,你醉了,我答道,別把我推入「說自己沒醉的人就是醉了」的dilemma裡,我只會說,我只是借酒意說實話。而我已很久沒有試過酩酊大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