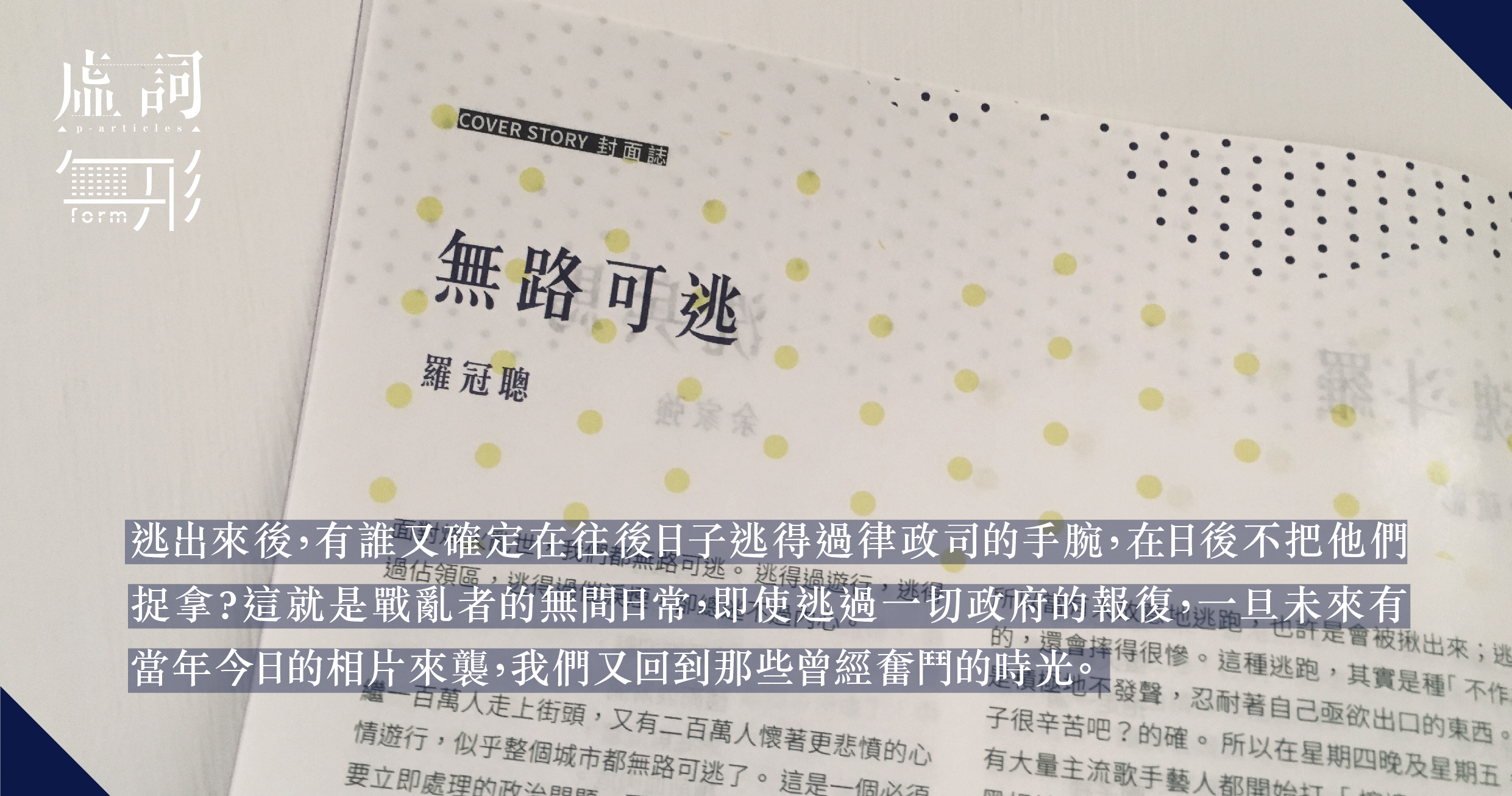徒然集.第二卷:置身冰河年代如此漫長的荒廢
詩歌 | by 浪子 | 2019-06-29
詩人浪子近作組成的〈徒然集〉數篇,由事件而生,從布拉格之春五十年到人權捍衛者甄江華案、再到自己被解除取保候審的經驗,每一行詩都滲出著國家機器的荒誕。 (閱讀更多)
【陳韻紅專欄︰青海波文香】烏鴉白鷺鳳凰
比起其他陸上動物,鳥因著會飛行而較能躲避人類的騷擾,附著每個地方如同它獨特的陰影。從香港到日本,便是從斑鳩與麻雀的世界,進入烏鴉的天地。每次看到漫天飛舞的黑鳥,就像找到掀開偽裝的線索,發現富想像力的影視作品中虛擬世界的原型。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