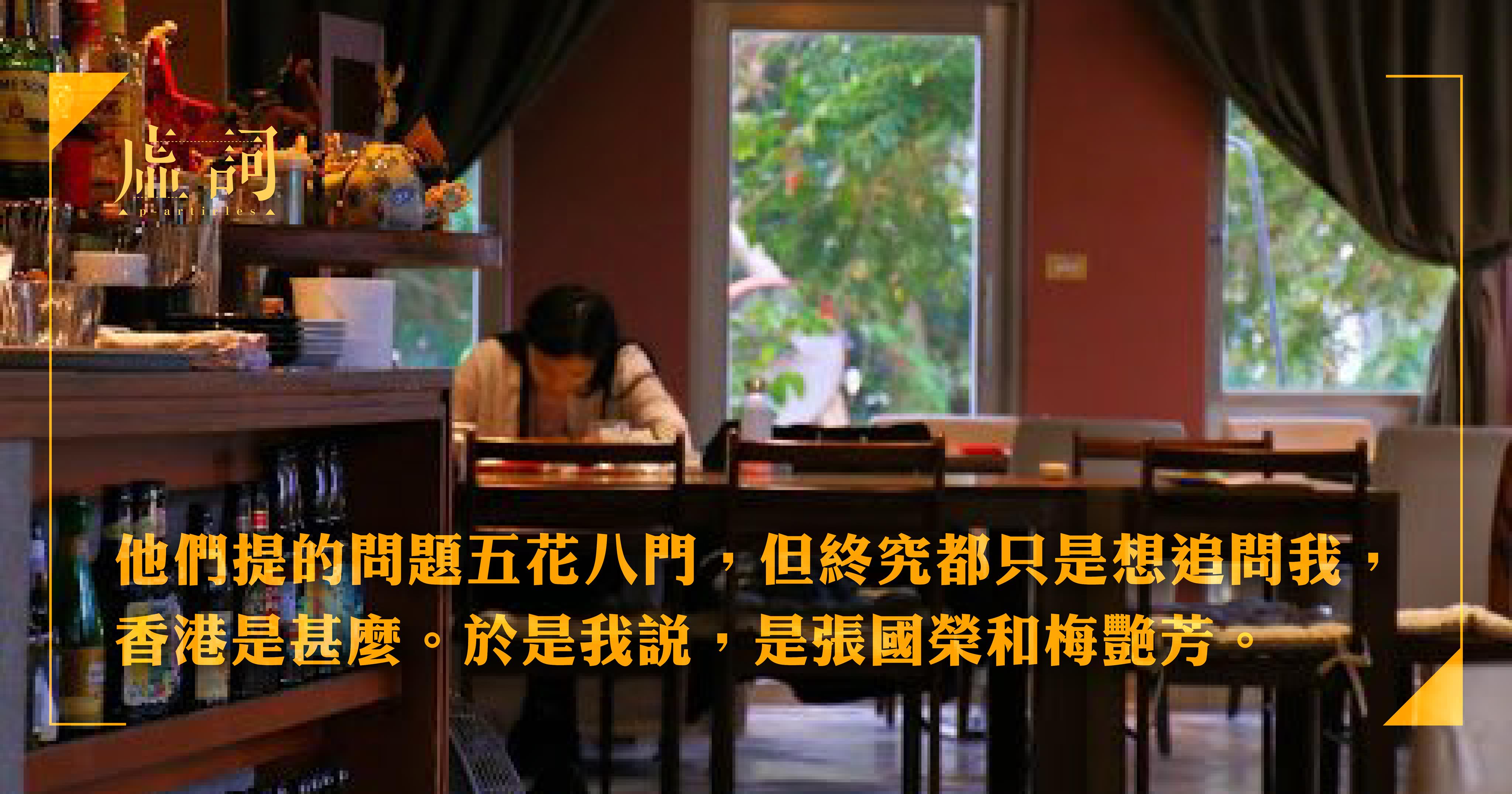貓與狗、蚊納及其他──花蓮旅居誌
1.
公寓大門時常流連一隻貓,叫蝙蝠俠,這是一位香港朋友替牠取的名字。我看着牠身上全黑的毛色,迅速接納它作為這隻貓在我人生中的稱謂。
蝙蝠俠不屬於這座公寓的任何人,準確來說,牠是我們所有人共同飼養的。天熱的日子牠跳上機車的坐墊,天冷就躲進車庫,食物盆裏的貓糧每天都有人補充,偶爾牠會跑到對面公寓的車棚,然後被狗吠嚇回來。
於是我想像這樣的場景:我在雨中抽着煙,由於抽得太急,咳了幾聲,對面的狗就開始叫,蝙蝠俠跑回來,聞我手指殘餘的煙味,漸漸上癮。
2.
每次出門蝙蝠俠都會徘徊在我腳下,當一隻攔路貓,好幾次我因而錯過了垃圾車。
錯過垃圾車的原因還有很多,例如撞了課堂時間、撞了我睡覺的時間、和撞了心情──不想就是不想。積存垃圾的最高記錄是一星期,我能看見半透明的膠袋裏滋生蚊蟲,就多套一個膠袋,把結繫得再緊些。
3.
一開始,我說自己的鄉愁是陳奕迅。Youtube的播放機制否定了這點,初到花蓮隔離十四日期間,我為預防尚未存在的小黑蚊,點了蚊香,然後電腦就播放〈有心人〉,是張國榮和梅艷芳合唱的版本。為了連結這首歌在這個時間節點出現的意義,我列出了以下的東西:
.寂寞也揮發著餘香 原來情動正是這樣>>用香氣誘捕蚊蟲
.從眉梢中感覺到 從眼角看不到>>感覺有蚊飛過,肉眼看不見
.完全憑直覺覓對象>>肉眼無法追蹤蚊蟲的飛行軌跡,要以直覺拍下去
.就當風雨下潮漲>>大雨過後,最多蚊蟲
.如果真的太好 如錯看了都好>>飛蚊症初期的自我懷疑
來到台灣的這三個多月,我接了兩個訪問邀請和一個線上分享會,我曉得自己被找到的原因,因為是香港人、剛到台灣,而且是寫詩的(而且與我的詩寫得如何無關)。他們提的問題五花八門,但終究都只是想追問我,香港是甚麼。
於是我說,是張國榮和梅艷芳。
4.
台灣的同學們都想學那句:「我真係好撚鍾意香港。」
花蓮市區開計程車的姨姨問我,那個被警察撲倒的小女孩,現在如何了。
創作課上互相討論作品,有人出於善意,寛慰我們寫詩不一定只能處理沉重的東西,也可以活得輕鬆一點。只可惜對方未能以自己的作品,說服我這點。
一起來到東華大學的還有幾個香港學生,我們交換了一些事情和細節。
但回家的時候,我只想摸摸門外的貓,想告訴那些叫我不要再回來的朋友,我很討厭這些說法──儘管我很清楚所有言語背後的情緒和緣由。
5.
我漸漸留意到出現在街角的尋貓啟示,有時貼在街燈上,恰巧旁邊趴伏一頭狗,我總忍不住以惡意的眼神去看待牠,並只能詛咒每一頭狗,將在每條小巷裏找不到可以犬吠的人。
6.
在我生活的那條志學街,晚上八點的黑夜與凌晨的黑夜,都暗魅得一般無異。
然後趕在年末,在一間尚在亮燈的咖啡店裏,透過淅淅瀝瀝的記事,完成最後一首詩。就是這樣,我還能寫無關痛癢的事情,寫離香港數百公里以外的地方,然後發現殊途同歸,一些不起眼的細節撲向你。
//我們愛過所有詭異的事物
一隻半盲的貓,我們用倒影去愛牠
一根受潮的煙,有了反抒情的語調
所有流動的時間,都是概念,並且即將薨亡
為了寫出偉大的祭文,假裝所愛的人都死去
為了假裝哀悼把一口煙抽到盡頭
我們慎重地咳嗽,曉得裏面有自己年老的模樣
我們愛上自己的隱喻,以此維生//
──寫在2020年年末,在9803咖啡館(花蓮縣壽豐鄉榮光街2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