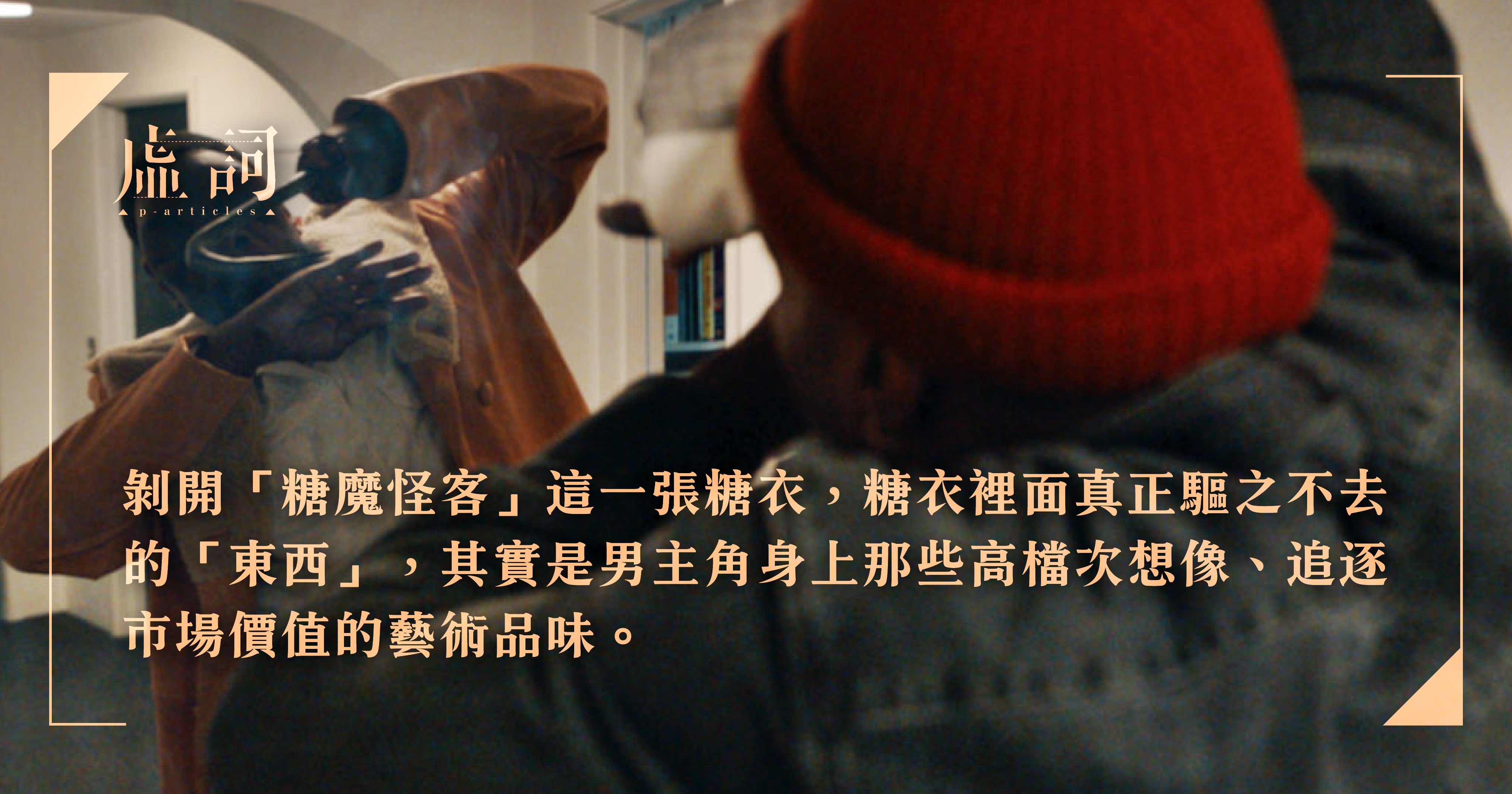《糖魔怪客》:每個庸俗的藝術家,都會變成披著人皮的惡魔
近年荷里活電影有兩大趨勢。第一,只要牽涉華裔演員,無一例外都與「辱華」扯上關係。第二,只要片中主角是黑人,都不用懷疑,故事絕不冷落種族平權的偉大使命。九十年代經典恐怖片《糖魔怪客》(Candyman)時隔廿多年的續作亦不例外。
由於《訪.嚇》(Get Out)和《我們.異》(Us)殺出亮麗血路,將美國白人殘害黑人社群的種族批判轉化為驚慄獵殺題材,成功引起影壇迴響,監製 Jordan Peele 顯然食髓知味,深諳主流觀眾有多麼變態,但凡高舉反歧視、反暴力的政治議題,反而都可以令電影變得更暴力、更醜惡,將經典獵奇血腥片《糖魔怪客》系列回收再續,原因呼之欲出:舊版故事改編自英國作家 Clive Barker 的短篇小說,那個有著鐵臂勾的糖魔怪客,前身本就跟源遠流長的種族歧視有關。

糖魔怪客的真正身份,曾是 19 世紀一位黑人畫家,他專門替白人富戶繪製肖像畫,有一次因畫結緣,與某位白人女子相戀,更令對方懷有骨肉。黑人畫家觸犯白人社會禁忌,被眾人斬斷右手,插上鐵勾,還在傷口塗滿蜂蜜,讓蜜蜂把他叮死。黑人畫家死後便以蜜蜂為暗號,化身糖魔怪客,成為芝加哥黑人社區一個著名的都市傳說。舊版《糖魔怪客》描寫一名女大學生 Helen 深入芝加哥黑人社區卡布尼格林(Cabrini-Green)調查期間,被糖魔怪客不斷追殺。廿多年後再拍續集,故事同樣發生在卡布尼格林,甚至找回同一演員 Tony Todd 來飾演糖魔怪客。而在新故事裡,歷史總是一再重演,年輕的黑人藝術家 Anthony McCoy 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深入卡布尼格林,追查糖魔怪客的傳說,結果走火入魔。
遺憾的是,數年前的《訪.嚇》與今日的《糖魔怪客》再不可同日而語,同類作品拍得太多,對種族歧視的社會批判,早已淪為一個泛濫空洞的議題,美國本土觀眾已看厭,而電影在香港上映僅一兩周,場次寥寥可數,便知道對香港觀眾來說更是缺乏吸引力。但其實,電影正是被它過度鮮明的政治正確光環掩蓋了它本身對離地商業藝術的觀察和批判。
誠然,電影是有明確提到,卡布尼格林過去曾是一個黑暗、暴力,犯罪問題嚴重,充滿歧視仇殺的社區,黑人被白人警察濫捕毒打的情況相當普遍,但在三十年之後,卡布尼格林擁有另一個更為獨特的面貌,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社區重建,已經從九十年代的貧民黑人社區,變成判若兩人,一個奢華而時尚,吸引了無數中產藝術家爭相遷進的熱門聚居地。而這才是新版《糖魔怪客》所有恐怖惡念的真正源頭。
看似自命不凡,實則生活無憂,住豪宅飲靚酒,終日圍著幾個藝術家朋友和伴侶附庸風雅、自吹自擂的年輕畫家 Anthony McCoy,故事一開始便從朋友口中聽聞,在這個名為卡布尼格林的新社區,曾經有個名為糖魔怪客的傳說。怪談是這樣的:只要對著鏡子連續呼叫五次「Candyman」,糖魔怪客便會從鏡子裡跳出來,將召喚自己的人殺死。他靈機一觸,覺得可以大造文章,於是即刻上網查找資料,還要拿著高級相機實地調查,汲取靈感,然後回到家裡,才思泉湧畫了幾幅即興作品,嵌進一面鏡子裡,做了個名為「Say my name」的裝置藝術。即是偷換概念,用最省力的方式現學現賣當是原創作品。但庸庸碌碌的男主角自覺這樣就是所謂社區連結、歷史重構⋯⋯藝評人見識大作,再聽他說到天花龍鳳,結果只一針見血嘲笑他膚淺堆砌,有 hood 而沒內容可言,說穿了都是些陳腔濫調的高檔化技倆。像男主角這一類遊手好閒的藝術家,又策展又做田野調查,表面上關懷社區,致力挖掘城市記憶,以保育議題進行創作,但再多熱情和抱負,都是一種偽善的狂熱。
而偽善所掩飾的是,像藝評人所說,早已見慣不怪,他們最終只是為了能夠用更廉宜的租金,享受更優閒的上流生活,才會選擇進駐一些長期被剝削、權力不平等的社區,再將不值錢的地方改造成高級藝術社區。其實他們的真正身份,無異於資本主義社會裡新一批侵略者。望向鏡子,鏡中的猙獰倒影有如理想自我的化身,才發現自己就是城市裡的嚐血殺人魔。
當然,鏡中惡魔這個設定,有許多心理學的鏡像理論可以引用,或許,是指向一個更終極、更猥褻的他者。不過,首先要從現實層面拆解鏡中惡魔的真面目。原著小說改編成舊版《糖魔怪客》電影的時候,會有惡魔從「鏡中」現身殺人的橋段,是源於八十年代卡布尼格林真的發生過一宗離奇槍殺案。曾有名叫 Ruthie Mae McCoy 的黑人女性報警,聲稱賊人穿過她的浴室鏡櫃闖入寓所,但警方認為太荒謬,並無理會。直至鄰居聽到槍聲,警方趕到現場才發現她身中多槍,倒斃家中。而鏡櫃後面的牆壁,據聞是一個大洞,原來位於卡布尼格林黑人社區的公寓,前身是一些造價低廉的徙置屋,施工期間多有偷工減料,用鏡櫃掩飾牆上破洞的情況非常普遍,而該區許多爆竊案亦從此衍生。

但來到三十年後的新版《糖魔怪客》,鏡櫃後面再沒破洞,連那些公寓都被推倒重建,變成男主角所住的高級豪宅。故此,糖魔怪客亦從真實罪案的原型,變成精神層面的幽靈,就像故事裡面的暗示,那潛伏在自己倒影裡的「東西」,是令人陶醉、莫名其妙的誘惑。然而,聽隨呼召進行殺戮的糖魔怪客,可能都是鏡像上的一種誤認,或一張用來藏起惡意的糖衣。就像糖魔怪客總是一手拿著糖果吸引獵物,另一邊斷手卻連著殺人鐵勾。只要剝開「糖魔怪客」這一張糖衣,糖衣裡面真正驅之不去的「東西」,其實是男主角身上那些高檔次想像、追逐市場價值的藝術品味。照鏡子的人,就是回應著他者的慾望,而真正令人陶醉的,不是殺人鬼魅,是主角企圖借助鬼魅、借用經典恐怖電影角色所換來的巨大商業效益。
故事裡面有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當男主角那幅「Say my name」真的應驗,召喚出糖魔怪客,引發凶殺事件,展示品隨即成為新聞焦點,而男主角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因為自己的名字被公開讀出而感到興奮。從某種意義上他總算因為自己的作品而成名。至於對社區與人文關懷的創作衝動,對種族歧視和社會不公義的關注,難聽一句,都不過是偽善和用完即棄的行銷手段。當然,我們還可以說得再難聽一點,這種「糖衣」的誘惑,跟 Jordan Peele 不厭其煩於《糖魔怪客》再三消費的反歧視、反暴力政治正確訊息,其實如出一轍。又或者,芝加哥有它的卡布尼格林,今日香港亦有迅速冒起的布魯克林,兩者之間有許多相似的案例。譬如說,男主角看中了「糖魔怪客」背後的社會議題,以此博取藝術光環作為行銷手段,就跟某些看似關注政治和民生議題的電影,但從來喜歡將社會責任捆綁到票房數字一樣偽善可恥。
又譬如,那些剛剛看完電影,受啟蒙於動聽的正義口號,要急不及待找地方噴一句「政府做錯嘢就要道歉」,然後轉頭去文青 Cafe 打卡飲啡,享受精品生活的觀眾,還有那些久不久高調宣揚自己熱愛環保,堅持(每周有幾天)擁抱素食主義,其實日日盯著社交帳號追蹤人數的生活達人,剝開糖衣,跟故事裡走火入魔的離地藝術家都沒分別。倒不如先找一面鏡子,說五次「Candyman」,細看那顆光鮮涼薄的善心會否已經屍斑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