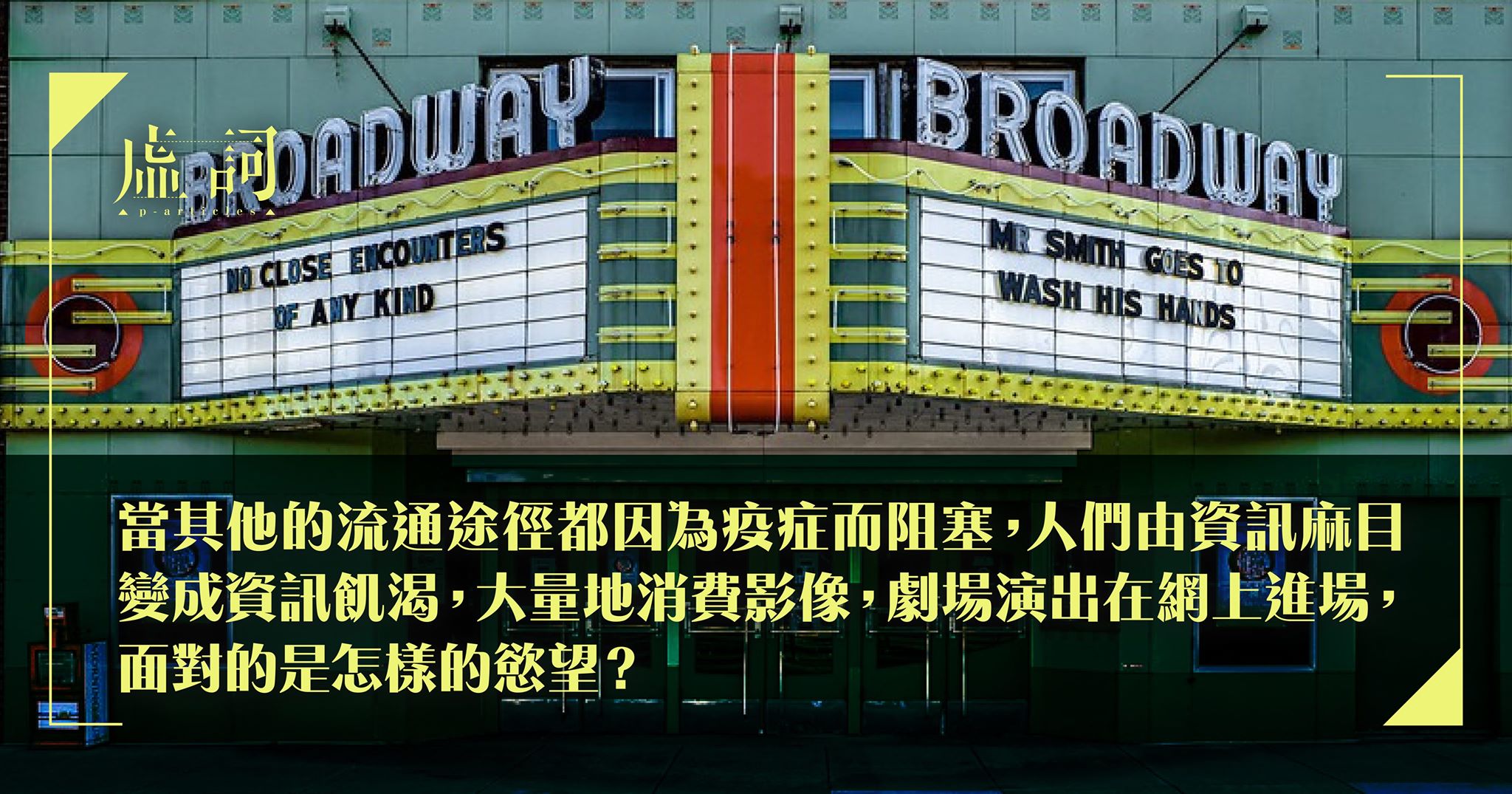病毒來了,網上劇場也來了
病毒來了,劇場關閉了。在虛擬世界比實體世界更貼身的日子,以現場性為本位的劇場演出,突然需要確立存在於網上的合理性。面對電影、電視、Youtube等等的陸續出現、科技改變人類的時空感知以及對「在場」的態度,劇場一直冷靜地守住建築物裡面人與人共時共地的聚集;一旦全球禁足,肉身流動受阻,卻似乎按捺不住,進取地加入影像化大隊。看似實務需要的背後,是身份危機嗎?如果將來只剩下長期依賴互聯網的人類,劇場希望在網上開墾的,是容得下現有本位的空間,還是塑造新的本位?
在2020年初的幾個月,劇場主要以兩種形式在網上出現:一是舊演出的錄影,二是新演出的直播。不多久,就有人問:網上可取代實體劇場嗎?
甚麼情況下,A可以為B所取代?
A和B大致同質,滿足慾望的能力差別不大
慾望的質已經改變,A不再能予以滿足
受眾不怎麼在意慾望的內容,用甚麼來滿足它都可以
我並不想建議A和B分別是實體和網上劇場,因為假使它們之間是取代關係,我不太知道取代和被取代的是甚麼:是所謂的「本質」、時空概念、呈現方式、還是......?實在還沒有足夠的案例和時間距離來討論。在病毒還未離去,劇場繼續關閉的這一刻,我好奇的只是,何以生出「網上直播劇場演出」的想法?它與直播的足球比賽或選美,除了內容,分別是甚麼?
直播的載體是電腦和手機螢幕。假使劇場是表演者與觀眾分享時空規律的文化空間,網上直播的時空規律,如何由身體和螢幕分享?西方繪製地圖的技術,在文藝復興時期獲得重大發展,身體無法觸及的地域,在二維平面上成了可視覺化的「世界」。自此。通過感官或視覺辨識出來的空間無須相同,要跨越也有不同的方法。螢幕是否也像地圖,是只需要視覺就成立的空間經驗?同一個螢幕可以容納不同視窗共時並置,在不同的資訊體之間任意往返的離散個體,還有共享時空規律的可能嗎?
為了要打擊極權謊言,我們分分秒秒追看新聞直播,轉換頻道,「現場」隨鏡頭角度改變,每個現場時間都是即時。弔詭的是,看直播的人清楚知道身體不在場,無力行動就是赤裸的證據。看直播的觀眾,身體感存於直播之外,他需要不屬於螢幕的行動的在地感,來彌補只有視覺的空虛。新聞直播以「現實」為內容,卻不能成為自足的現實體。在網上直播之前的劇場,是觀眾用身體感覺「他者」在場的地方——一個日常生活以外、價值觀迥異、令他察覺到主體的他者。觀眾不在場,甚至連表演者也可能不在的網上劇場,套用班雅明的說法,因為與生產時空斷裂而失去了靈光。它成為了網上無限多的影像之一。實體劇場依賴瞬間即逝的演出抗禦商品化,影像化的網上演出隨時變成瞬間即逝的商品,前仆後繼地快速死亡,為資本主義提供動力。當其他的流通途徑都因為疫症而阻塞,人們由資訊麻目變成資訊飢渴,大量地消費影像,劇場演出在網上進場,面對的是怎樣的慾望?
詩人Paul Valery 早在1928年已經在著作《La conquête de l'ubiquité》預言:「Just as water, gas, and electricity are brought into our houses from far off to satisfy our needs in response to minimal effort, so we shall be supplied with visual or auditory images, which will appear and disappear at a simple movement of the hand」。既然說了100年,對網上直播成為時代無可逆轉的走向,也沒有好奇怪的。誠然,所謂劇場的在場性可以、也應該隨時代而改變。既然觀眾和表演者都不在場,不在場便成為了新的在場。當我們不能分辨出現和消失,新的現實可能出現了。阿蘭.巴迪歐說:「Art does not occupy existing space, it creates new ones」。網上劇場需要一個由想像力開拓出來的新空間,而不是抱着舊空間尋找落腳點。我想借 Henri Lefebvre 提出的三種空間概念中的「再現的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來問一個問題:為甚麼某些演出直播或者事先張揚的舊演出錄像放映,要像實體劇院般在晚上八時開始?有需要在未定性的空間複製另一個的習性嗎?需要在網上存在的,是劇場本位中的甚麼?
假如網上觀看是不專注的美學,不再受制於單一的自主,劇場可以成為驅動這股力量的方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