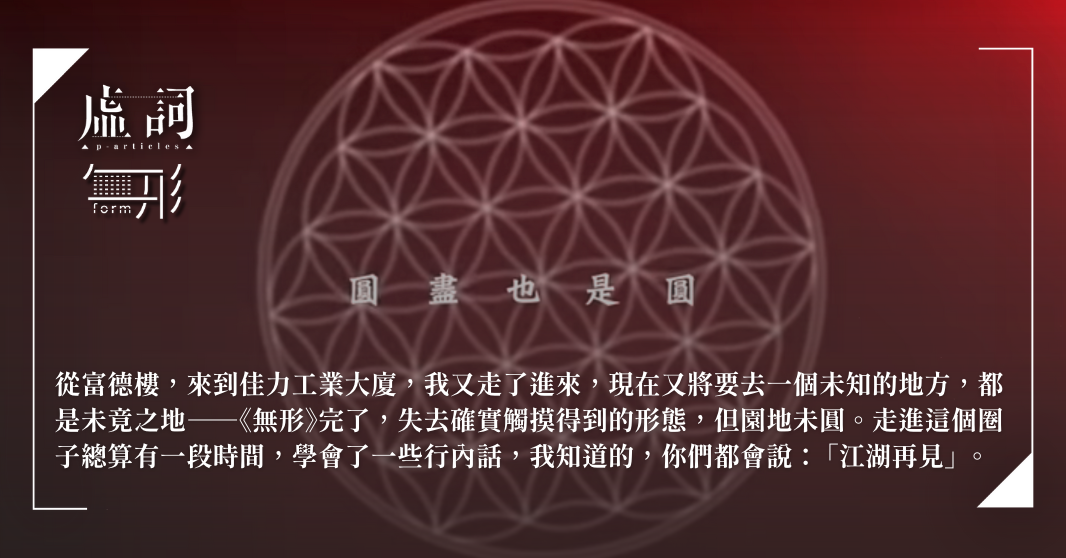【無形・◯】圓盡也是圓
無緣無故怎會以「圓」為主題,本來打算一雞兩味,若得以延續就可以放下沉重的義項,說不了完,猶自可說圓,但《無形》終究逃離不了圓缺的命運。
編輯曾經是遙不可及的事,但我這個職場新丁竟然走了這一遭。重看《無形》創刊的定義,無形就是abstract、invisible、unseen(因某些原因而未被看見)、imperceptible(不知不覺),如今看來是不辯自明。如果把《無形》的生命週期確切地用筆畫一個圓來呈現,八期,我參與的這八期,到底佔了幾分之幾個圓形?我數學不好,不清楚應要計弧線的長度,還是計某個扇形的面積。只知道我的起點,入職就迎來鬧雙胞風波,我說著一嘴很爛的普通話訪問臺灣和上海學者,當時只是惘然。我也整理了文學館發展的時間線,一雙直線描繪出實現與想像的圖景,許多東西消失了又衍生別的東西———像Marvel的洛基告訴我時間是個圓形,離去像歸來,歸來又像離去,更搞不清一切起點與終點了。
在我記憶之中,其實有個更早的起點,而同事們毫不知情。2021年5月,文學館仍在灣仔富德樓,那天在銅鑼灣面試後,心血來潮想到訪香港的文學館,便沿著軒尼詩道西行。我身水身汗推開木門,投來幾雙疑惑的目光,小樺從座位站起來說非辦公時間不對外開放參觀,讓我打回頭。原來文學館是這麼細,香港要搞文學原來這麼不容易。這是緣起。
又說圓形由無限個圓點組成,我能夠站在這一點上,要感謝Emily最初給予機會,之後同事和小樺的指教和包容,也感激被我邀約過的作者們,這些都是得以把圓聯繫起來的點,讓我看見了更多自己和香港文學的可能性。其實,還想鳴謝新蒲崗餐室成為編輯部埋版的集體回憶,那裡的麻婆豆腐飯和芙蓉蛋飯特別討我歡心。(雙魚座總編按:從來冇預我 >A<)
提筆此刻,距離辦公室搬遷還有一個月。我們的工作檯總是一片凌亂,書本疊得高到看不見對面的Michelle和Victor,檯面也放滿了文具雜物,每期埋版的校稿,我們都隨意擺放,讓它到處生成。常聽前輩們說,每個刊物都像一片園地,讓作者們種花植樹,那麼這些校稿散落四周,豈不像撒了一盤種子?我又把幾期的校稿捲成一個圓筒,塞進牛皮膠紙卷裡,它就一炷香似的豎立在我的螢幕旁。
啊,是的,這是一片園地。從富德樓,來到佳力工業大廈,我又走了進來,現在又將要去一個未知的地方,都是未竟之地——《無形》完了,失去確實觸摸得到的形態,但園地未圓。
走進這個圈子總算有一段時間,學會了一些行內話,我知道的,你們都會說:「江湖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