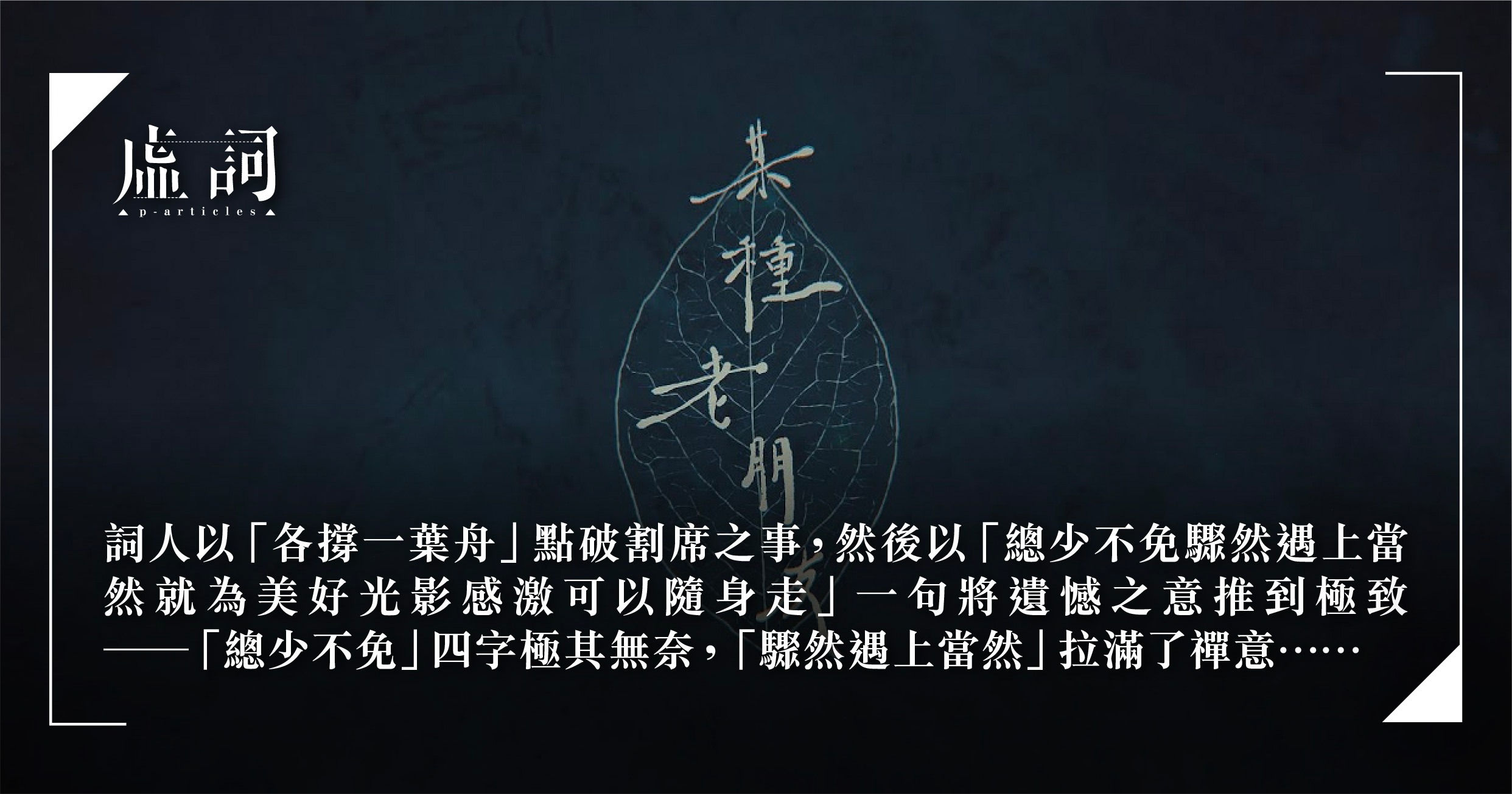林夕的割席美學:《某種老朋友》詞評
其他 | by Sir. 春風燒 | 2023-01-10
人到中年,筆者愈能體會兩句古語。一是《論語》那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二是陳子昂的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兩句話一喜一悲,實則同一個心境。與你志同道合的人雖然沒有生活在你的圈子裡,但他不遠萬里來到你身邊,告訴你「德不孤」,難道不是極為快樂的事?當你困在「現在」這個時空之下,無法掙脫,你精神上的手足是書中死去的古人和未出世的未來人,此生不會遇見,想到這裡,難道又不覺得蒼涼嗎?
三四年來,從有人戴罩到禁戴,再到人人自覺戴罩,最後不准不戴,我們在或多或少、或人為或自然地、或自願或被動地原子化。筆者雖不服氣,但也只得在時代浪潮的神推鬼㧬下逐漸篤信,人難以跨同溫層、跨信息繭房交流。在價值壁壘分明的時代裡,說服對手是不可能任務。尤其面對親近的人,執著與他們辯個高低,除了滿足自己的說服慾以外,不得不承認實際上是徒勞的。既然人類還未進化到按照價值認同來派發護照,割席似乎也難以避免,就讓我們躲回各自的同溫層裡,各自安好。
林夕寫的《某種老朋友》(林家謙唱)大概也可以看成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割席心得。還記得本歌在年初派台時,歌曲節奏綿密正如當時春雨。我嘗邊開車邊看水珠從玻璃窗滑下,一路循環播放著,格外翳心之餘,又佩服詞人可以將深沉的話題流水一般暢順而輕盈地表達。一時如庖丁解牛,下刀即直達情感最深處的要害,精準剖開,游刃有餘;一時又化身顯微鏡,目鏡放大到其他器材難以企及的倍數,本能而嫻熟地觀察玻片中的世情和人情,又在針孔一般微細的傷口裡呈現一個豐富的宇宙,最後寫出一份別處不可得的詳盡報告。
這種把歌當報告來寫的風格在林夕的作品中並不少見。譬如《開不了心》(陳奕迅唱)教人別胡亂鼓勵傷心的人,快樂也要找原因——詞人沒講「論傷感我研究得比你深,你來安慰我,你識條鐵咩」已經很客氣了。高階一點的,與林家謙合作的另一個作品《心靈作家》(鄧小巧唱)拿自己開刀,更是理智剖析、仔細分類到可怕的地步——
- 目標:拼命勵志,做心靈作家;
- 難過原因分析:看了難堪的新聞,對眾生心生惻隱;
- 解決辦法:越忙越能淡忘難過;
- 受傷類型及數目:被掌摑三巴;
- 兇徒作案工具:左手;
- 反安慰話術:我的傷口很瑣碎,不會留疤;
- 最近工作:鑽研去疤。
……
這種既冷靜又哀怨的情況,在《某種老朋友》的歌詞身上也可找到影子。
主歌「突然地疑惑龐大陰影活像鯨魚/只有等你要呼吸了才重遇」首先用「鯨魚」將抽象的「陰影」具象化,因此這種陰影有長度、重量而且會移動出沒,以此營造一種巨大的深沉;而這個陰影就是「你」, 鯨魚願意出水面呼吸自由空氣時,才有重遇的機會,原來割席就是這樣自然而然、悄無聲息地發生的。
「肯與不再肯也未出於自願/胡言後聽你亂語/為何只懂得看書/為何不邂逅奇遇」呼吸不是本能,為什麼要等呢?鯨魚先說它是身不由己的,然後反咬一口:「海底有這麼多好玩的、好吃的,為什麼偏要上來呼吸自由空氣呢?」筆者大膽懷疑,此處兩個「為何」的質問不純屬虛構,是真的有人對他說過類似的話。
主歌第二段,以「殘舊陰影」喻故人及回憶。雖然自己被這塊「陰影」攻擊,但仍舊在心裡找一個位置接納這塊陰影,這就是詞人在《自我安慰》(古巨基)裡如出一轍的價值觀:「回憶贈給我未來能修為/才頓悟共你美好光輝不用去放低」,然後詞人職業本能地對陰影來一頓物理分析:情感出現陰影就像天空出現烏雲會下雨一樣,是尋常事而已,不必大驚小怪,誰先想誰、誰一直不想誰,不是一場較量,沒有輸贏。「我是我間中跟你一些記憶共處/也不再忌諱同住/如皮膚即使碰瘀/從無發現亦痊癒」說明「我」不但沒有為了避忌而刻意忘記「你」,而且還有膽和那些記憶共處,皮膚碰瘀後出手治療只是因為發現了,如果沒有發現它,也沒大不了,也早晚會康復。
副歌指出某種老朋友只可「暫時懷念」,不可在現實中同舟共濟。現實是在湍急的時代洪流下,彼此都自顧不暇,載沉載浮,十分狼狽。此時,鏡頭zoom in到「手」,彼此關係現況疏離得令人難以相信過去曾與對方攜過手、同過路,回憶與現實的落差令人感官錯亂,最後經過詞人「理性地」梳理清楚了:回憶那一款「我牽過的手」和眼前這款「與偉人握過的手」。這雙手牽過我,不代表一直會牽下去,牽手這件事是會輪迴的,正如每副面孔也會從熟悉輪迴到陌生,也如樹葉從榮到枯,走不出這個死循環,長壽成了一種詛咒,此所以詞人寫道「命像悼念長壽」。到副歌下闕,上闕的「某種老朋友」變作了「某種過期朋友」,割席之意愈發明顯,「世上沒人能阻擋細水愛長流」一句除了有逝者如斯夫、時間不可追的遺憾之外,還有輪迴前的人際關係亦不可追的遺憾,此外尚有一層「各人有各人的前途和價值追求」的遺憾。除了面對現實的無奈,還要面對回憶的攻擊,而詞人的應對辦法就是把回憶當成一種詛咒,這個詛咒不但無害而且有情,反正也不會對現實有任何影響,回憶的不堪也就此消解了。
主歌第三段,「就原諒回味從淚水中滴漏/其實沒需要自救/刻意擺脫什麼非永恆這對手」回憶化作淚水滴落,難以挽回,也不需把自己從回憶中救出來、擺脫前事,既知什麼都不會永恆的,又何須刻意擺脫它?記憶早晚會自然凋零剝落的。然後詞人寫道「我在著衫聽到你囉嗦再嘲弄我/看衣領漸染黃後/為何不清洗熨斗/為何潔具亦殘舊」似與主歌第一段呼應,「我」被指摘守舊、不識時務。
全歌最後一段,詞人以「各撐一葉舟」點破割席之事,然後以「總少不免驟然遇上當然就為美好光影感激可以隨身走」一句將遺憾之意推到極致——「總少不免」四字極其無奈,「驟然遇上當然」拉滿了禪意,世事和人情變故不但快而且彷彿是命定的,令人感慨現實難以捉摸,不過,至少美好光影可以如業隨身。既然事情變得如此迅速,「傷春」是沒必要的,因為一轉眼就到了入秋時節,你的傷春情緒一剎那就過時了,於是詞人寫道「沒有傷春的我看一看枯葉伴晚秋/如葉也不必考究每一片將活著多久」,既理智又淒涼。
割席就割席了吧,人與人割席又有什麼了不起呢,反正,我們遲早不也要和自己的生命割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