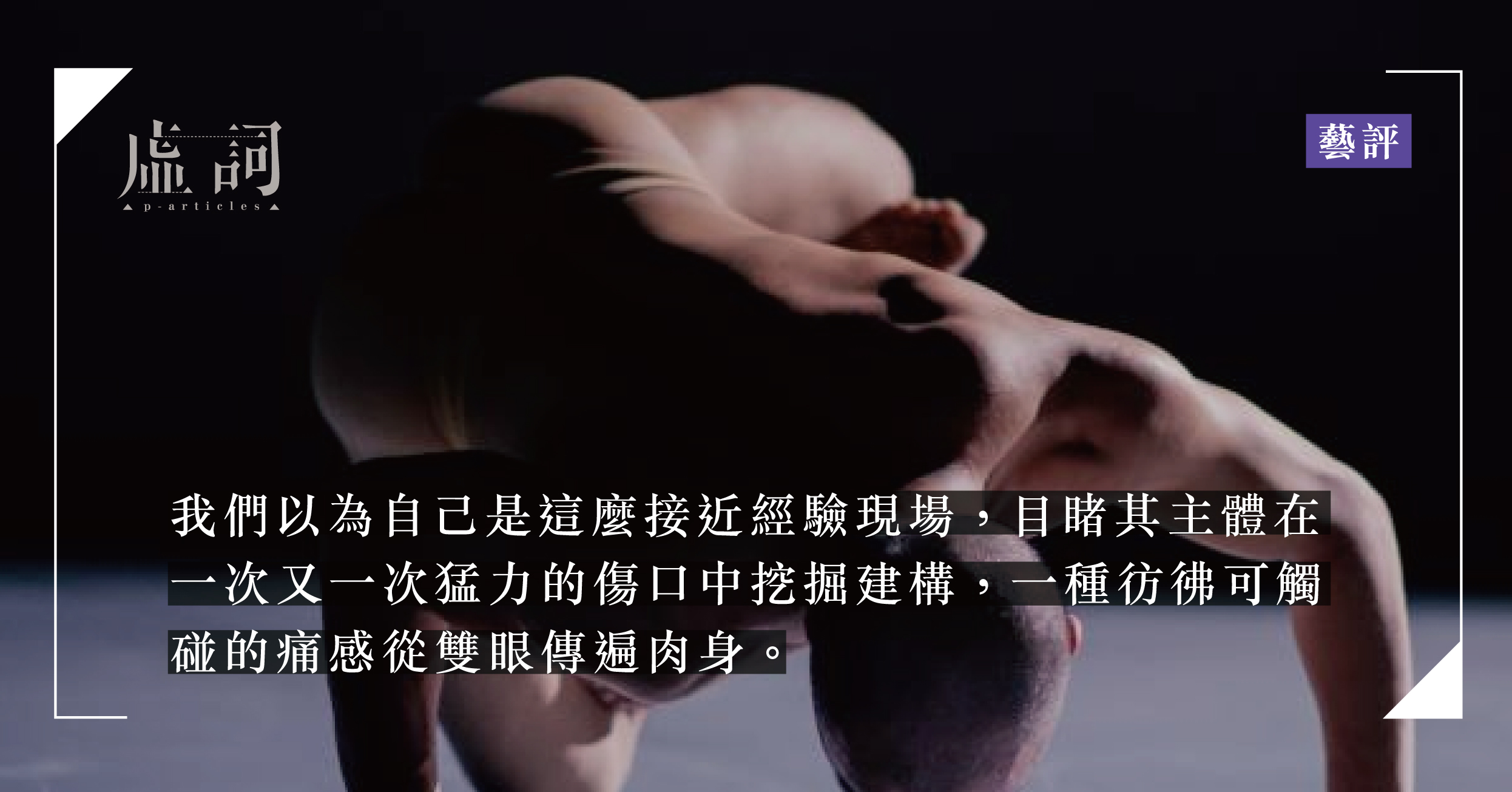Anacostia Community Museum︰服務社區,人人都是策展人
如何建設理想社區?答案或許人言人殊︰有人相信社區少不了街坊交流的聚腳點,有人認為社區必須提供顧及長者與孩童需要的服務,也有人提議成立流動市集支持本地自家製產品。大抵沒有人想到一所鄰里博物館也可以對社區有所貢獻。平情而論,誰需要一座博物館收藏家裡藏不少了的陳年舊物?街頭巷尾的舊故事又何以改變社區? (閱讀更多)
遊玩間,鬆動邊界——「像是動物園(二)」
藝評 | by 陳怡 | 2018-11-27
《像是動物園(二)》(《像》)的點題讓我想起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之著作《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他揭露醫療制度如何將人放進「正常/異常」的二元對立框架,把「正常人」與「異常人」區隔開來,以維繫社會秩序及正常運作…… (閱讀更多)
Whitney Museum︰何謂「政治正確」的主題式策展?
不同類別的博物館各自各精彩,但不同的論述框架、不同的藝術觀點如何交流互通,以至社會大眾也從中理解、欣賞、尊重多元文化所衍生的差異?為甚麼歐洲藝術家挪用非洲藝術元素被視為前衛創新,但非裔藝術家引用傳統方式創作卻鮮有得到迴響?為甚麼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往往被撥入人類學,而非藝術史研究?藝術館如何將原住民、非裔、拉丁裔以至亞裔的藝術理念與創作手法融入主流的藝術書寫,建構出代表美國多元文化的藝術史觀? (閱讀更多)
我手畫我身 裸得大膽潘玉良
這年頭描個裸體大概只會傷害到明光社,沒甚麼好大驚小怪,但潘氏身處名為性別解放、實仍封建迂腐的華人社會中大剌剌以「肉」入畫,理所當然就被視作「傷風敗德」了。上海美專當時的人體素描課起用女體模特兒招來誹議,潘氏乾脆畫自己的裸體,並大膽作為於學校首次公開展出的作品。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