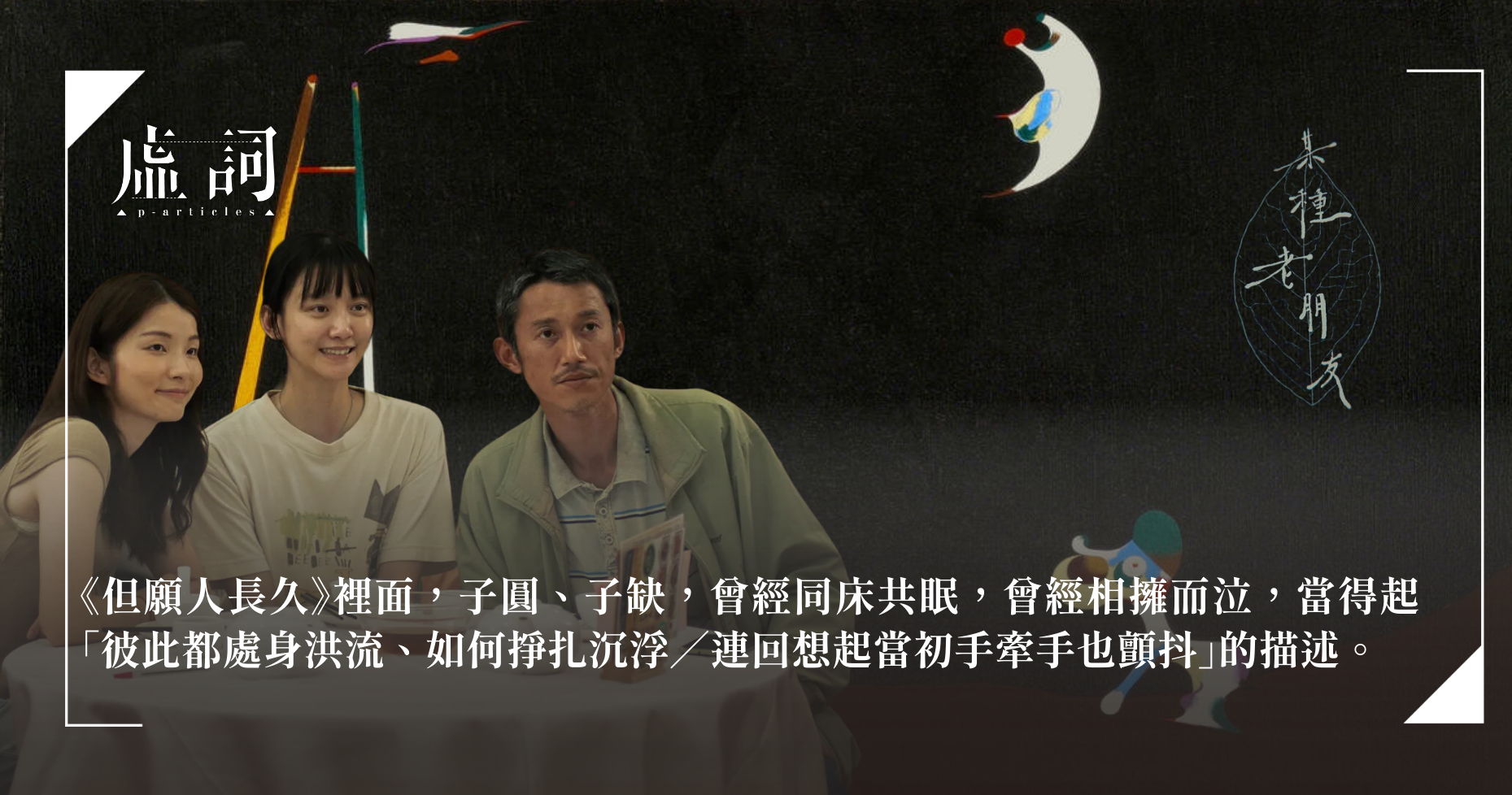月是懸宕在那裡的枯葉——《吠月之犬》、〈某種老朋友〉,以及《但願人長久》
「我夢見我媽媽、我爸爸,た們還是很好的時候;還有我妹妹。雖然我明知那是夢,但是醒來的時候還是會開心好久。」
1
如果現在就能讓我親眼看到一幅名畫,就請是胡安.米羅(Joan Miró)的《吠月之犬》(Dog Barking at the Moon, 1926)吧。去年在香港藝術館的「米羅的詩想日常」(Joan Miró — The Poetry of Everyday Life),展出了九十多件他的作品——那個可愛的穿洞平底鍋、奇形怪狀地看電視的人們、白色畫布上的黑色曲線配上一些基本色塊⋯⋯沒有《吠月之犬》。
不熱衷於研究畫布細部,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如何妙筆的戒指(Miss Mathilde Townsend, 1907)、眼鏡(Charles Woodbury, 1921),都覺得與我無關,所以對於名畫,往往也不太渴望親眼看到。唯獨《吠月之犬》與別不同。
那是因為,至今,我還沒有在網上找到一幀滿意的《吠月之犬》圖片。圖片無論有多清晰,畫面依然保持模糊——這比《蒙羅麗莎》的無論你走到哪裡、女子都依然看著你還可怕。薩金特的戒指、眼鏡,雖則迫而察之,會以為是一滴白色的意外,但是遠而望之,馬上就能意會到那是反光的亮點,並「認出」所畫之物就是戒指、眼鏡。《吠月之犬》卻恰好相反——那片似乎是「月」,那隻沒有保證是「狗」,鐵路或梯子右側的那團又是什麼?色塊篤定得恍如拼貼,沒有意外的可能,但形象卻是詭異而陌生,以至根本沒有能夠「認出」這回事,因此,只要圖片所示的畫中之物邊界模糊些許、裁切比例或顏色更動些許,也會滑向歧義、導向非其所指。
當1997年的子圓(1997,許可兒飾;2007,謝咏欣飾;2017,祝紫嫣飾)回到家,家裡沒人,一把搭在牆上的梯子指向天空,然後子圓意識到——家裡其實不是沒人時,我想到的就是《吠月之犬》。
* * *
米羅生於加泰隆尼亞,1893;1920移居巴黎,受超現實主義文藝影響,後來成為了這個流派的代表人物。人們在談論如何理解他的作品時,往往會提及自動主義(automatism)。而對於如何理解運用相關技法創作出來的作品,我想,有一種方式——像是解讀塔羅(tarot)那樣就好了。在解讀的時候,我們首先有的是一個「情境」,它限定、同時延伸了牌上「情景」的意義。
現在,抽牌的我,「情境」是《但願人長久》;抽到的牌,「情景」是《吠月之犬》。
* * *
Dog Barking at the Moon(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除了標題,似乎,其實就再沒有什麼證據指向「狗」是狗;它(下按每句各自的語境安放代詞)的「臉」毋寧更像是一個人、一個男人、一個老人,有鼻子(白色),有頭髮(黑色),有絡腮的鬍子(紅色)、剃掉了鬍子的下巴(黃色),還有也許是徹夜不眠而然的眼袋(黑色)。他張著空洞、向天的口,如果是吠,那大抵就會是激動而惶恐——但我同時懷疑,如果標題裡面沒有「吠」,把那個橢圓之物聯想成口便沒那麼理所當然,而且據說,牠本來是有話說的,但米羅到最後把話取消了,只剩下無語問蒼天;瞪著同樣空洞、向天的眼,使我們無法肯定,牠/他所吠/叫的對象,是正上方的「月」,還是鐵路或梯子右側的那團什麼。
那團什麼,在我所夠得著的最清晰的圖片裡面,還是顯得模稜兩可,不過,也許可以說,那團什麼,似乎,掩藏著另一個月亮(白色)。那就怪了,右邊不是已經有一個月亮了嗎?月亮不是只有一個嗎?據說,月是故鄉明,但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故鄉?2007年的子缺(1997,彭頌晴飾;2007,許恩怡飾;2017,袁澧林飾)說,「到湖南,た們叫我們香港人;在香港,た們又不承認我們」;2017年子圓「白話」和「普通話」都流利(她還會湖南話和日語),而沒有辦法利落地答出自己是哪裡人。
一個月亮已經關閉了,只留下一點暗示、一道梯子;另一個月亮,以詭異的形狀顯現,而懸宕在那裡,在比較就近的、頭(/口)的正上方。子圓小時候對子缺說,「我把玩具留給了你」;她給子缺緩衝了一些東西,子缺後來學有所成,2010年代因為保護馬屎埔村而被捕,到底是因為承認了香港作為「故鄉」、還是潛意識裡期望得到這裡的承認而作出的行動,也好,她似乎都是找到了一個可資錨定的地方,願意為這個地方付出、一些可以理所當然地宣稱這裡是「故鄉」的人也不會願意付出的代價,因此——與林覺民(吳慷仁飾)恰恰相反——入獄反而有了一種類似「抵壘」(touch base)的意義。
至於子圓,她有蒼老的靈魂。就在1997那年,當她意識到家裡其實不是沒人,而向上仰望梯子的終端時,她已經成為了那一隻「狗」——她首先衝上的,是林覺民在家裡吸毒這件事;她問媽媽,我們什麼時候回去,從那時起,她便知道,一個月亮已經關閉了;20年後,她本來還想著,去那裡看看林覺民口中的野百合時,才得知,連野百合也都已經早就沒了。她這些年來,一直游離,一直沒有固定的「床」——可以安枕如家的地方、可依之人。所有人事,都像離她好遠,(像她帶團時,獨自,在東京的晴空塔上俯視,平淡,也許若有所思——據說俯視往往召喚孤獨。)包括子缺。「好像去年開始,媽媽改嫁搬走以後,她跟我有點疏遠,她可能不想、有點怪我,搬出去住吧。」她這樣跟她的SP小宇(巫建和飾)說。已經沒有辦法了。那夜,她在窗前抽煙,子缺帶著問她去不去跟林覺民飲茶的動機,來到她身邊,吃橙子,到一半沒吃下去,我還想著最後會由子圓吃完;子缺迂迴地說話,問了一堆問題,終於問出口來,而子圓沒答應,只是問,怎麼不吃完它?子缺也只好說:「酸。」
最後最後,她獨自、再次獨自,搭上多年前和父母一同搭上的觀光升降機,升降機可是沿著《吠月之犬》裡的鐵路或梯子,升向明月?明月幾時有?沒有青天,天闊地大,都是漆黑一片,這原尺寸二十八又四分三乘三十六又四分一英寸的畫作。難以想像,當我親眼看見它懸掛在牆上時,它的激動、與惶恐、與一千多平方英寸的孤寂,將怎樣向我襲來。
2
日前(6月8日)參加如同文學社的「MV寫作工作坊」,寫作環節是給林家謙的〈某種老朋友〉(林夕作詞,澤日生作曲)想一條MV(下把這條我想像中的MV用雙引號表示,以與本歌、原片區分)——老實說,起初我真的是,什麼也沒想到,於是呢,我決定先自動書寫一波。我把當時寫的那團東西,以及我後來分享想法時講的那團東西,整合拓展一下,得出來的『某種老朋友』,以下。
* * *
我首先想的是,好像大家首先想的,都是情侶——那可不可以不是情侶呢?「也不再忌諱同住」,似乎,也可以是室友。但直覺上室友還沒有到思考的終端,因為朋友、戰友、密友……之類,都是有聽過的說法。那麼,可不可以,朋友也不是?「我在著衫聽到你囉嗦再嘲弄我、看衣領漸染黃後」,管你管到你衣領上來,似乎也並不是朋友會做的事。
我先想到陳慧的《弟弟》,然後想到《但願人長久》。
《但願人長久》裡面,我最深刻難忘的點,在《吠月之犬》之外,是2017年的子圓,人在日本,夜裡即興地跟小宇去了趟居酒屋。「你們之前感情很好啊?」小宇這樣問了子圓,有關她和子缺的事;子圓回答,「她是個,嗯⋯⋯」怎樣的人呢?我們都沒有聽到,後面也再都沒有提及——被金髮男(各務孝太飾)的酒瘋打斷,子圓始終含辭未吐、欲說還休。
對於子缺,子圓是想想起、想提及的嗎?想的吧,在那個當下。然而金髮男的酒瘋讓她快速地冷靜、冷卻下來——算了,不重要,過了那刻,她便覺得,不提也罷,「突然地疑惑龐大陰影活像鯨魚/只有等你要呼吸了才重遇」,指的大抵是這種感覺,想起、提及的欲望,在那一刻龐大到無以復加,這個「你」(指的是我的記憶而不是你的實體吧)的出現,是我「肯與不再肯也未出於自願」的不速之客。然而一轉頭,鯨魚呼吸過後,又復深潛,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
我所覺得的『某種老朋友』,就是這種欲說還休的感覺,這個欲說還休的場面,大概可以放在歌詞前面。
第二種感覺是,『某種老朋友』,應該沒有擦肩,沒有道別,沒有遇見——因為「暫時懷念某種老朋友」,應該發生在一人之境,平靜,沒有外人打擾——最好也沒有閃回(flashback),最好長鏡(long take),最好極其日常——「看衣領漸染黃後/為何不清洗熨斗、為何潔具亦殘舊」,我想到的畫面,是料理家事的畫面——妹妹在家裡洗衣服,經過久不在家的姊姊的房間,發現,也許是搭在椅上、也許是鋪在床上、也許是掛在牆上,衣服上面落了一層灰(就像子圓是旅行團導遊,所以常常不在),便順便拿去洗洗(這也確實像熱心的子缺會做的事)。我想表現的是那種「缺」的在場,就像,子圓缺席,在場的只有子缺,而子圓的「在場」,要通過子缺來完成。想過信件、日記,但好像都及不上衣服好——衣服總是招魂的法器,像《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 2005)、《無依之地》(Nomadland, 2020)裡所見的那樣。
當妹妹給姊姊洗衣服(也許會是姊姊欲說還休時穿著的衣服),她也應該極其平淡,可以若有所思,但至少要沒有陰翳——「突然又容納殘舊陰影暫住、尋常像天要下雨」。
據說,「老朋友」的意思,是分手的情侶重遇,為了不尷尬,為了安放一個身份、一個自容之所,而稱對方為「老朋友」。這樣解釋下來,那種悲哀很能設想。但我想到,這樣的悲哀難道沒有更悲哀的可能嗎?梁遇春的〈寄給一個失戀人的信〉裡寫到:「照你信的口氣,好像你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秋心你只知道情人的失戀是可悲哀,[…]她雖然是不愛你了,但是能夠這樣忽然間由情人一變變做陌路之人,倒是件痛快的事——其痛快不下給一個運刀如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殺下頭一樣。」宕開一筆——這個比喻,真妙,他雖說是「痛快」,終究是拿死來比喻失戀,這樣進可用「引刀成一快」來安撫對方,退一步來說,也沒有否定對方欲絕的情感。反正,他說情侶分手不是最不幸的;他覺得夫妻之間的心死才是——是不是呢?我覺得,《弟弟》裡譚可意談的每一段戀愛,都不及跟弟弟可樂的情誼來得真摯、動人;兄弟姊妹之間「變做陌路之人」,大概要比情侶分手更悲哀吧,由其是本來像可意、可樂那樣親的那種。
〈某種老朋友〉裡面,貫穿全首的事物是「葉」:一片葉、一葉舟、枯葉伴晚秋⋯⋯原片中也正是用葉。葉隨流水,水面上與誰相交過,相交過又別過,萍水相逢,這大概就是情侶、朋友的處境。不過,如果這兩片葉的相逢不在流水,而是早在樹上呢?如果它們,本來是同氣連枝,不只「只不過借段歲月同睡」的情誼呢?這種「飄落」不是更似「命像悼念長壽」?《但願人長久》裡面,子圓、子缺,曾經同床共眠,曾經相擁而泣,當得起「彼此都處身洪流、如何掙扎沉浮/連回想起當初手牽手也顫抖」的描述。
「你們之前感情很好啊?」
「她是個,嗯⋯⋯」是個怎樣的人呢?就,某種人唄。
『某種老朋友』的最後,妹妹把洗好的衣服掛起來。也許,衣服會因為某些理由,而沒有被弄得特別乾,以致,在掛起來時,水還在往下滴,像極了一場謹小慎微的雨,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會下完。
3
《但願人長久》的英譯,是Fly Me to the Moon,大抵就是〈水調歌頭〉裡面的「我欲乘風歸去」;對子圓來說,這卻是何其虛妄。她有蒼老的靈魂,也許對她來說,說Fly me to the moon,將永遠,沒有 “Fly Me to the Moon”(1954)的意思: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某種老朋友〉只得「一片葉無奈剛飄落背後」,連同《但願人長久》那永遠都沒有到頂、也沒有人齊過的觀光升降機,都沒有飛行的可能。至於《吠月之犬》背後——我剛才說,「狗」據說「本來是有話說的,但米羅到最後把話取消了」——據說是一則加泰羅尼亞的民間故事——犬吠月以 “bow wow”,月如此回應:“You know, I don’t give a damn.” 電影好像甚至連月亮的鏡頭都沒有出現,大抵對子圓來說,其實所謂故鄉,是那一片野百合,已然逝去;所謂月亮,只不過是一片、那片野百合燼餘的枯葉,一直懸宕在那裡、在頭上的暗黑的天。「月有陰晴圓缺」——有晴?已經沒有辦法了,「沒有傷春的我看一看枯葉伴晚秋」——升降機裡的子圓,極其平淡,也許若有所思,但不至陰翳,只是沒有表情;也許,在這一程升降機裡、在這樣的音樂奏鳴和應之間,她是在回想最起初、那程升降機,想像「我媽媽、我爸爸,た們還是很好的時候;還有我妹妹」,一起上升,升向明月,在想像自己乘風歸去⋯⋯不過,一程升降機,很短;她的想像(如果有),只有她自己知道——連我們也不知道。也許,她「醒來的時候還是會開心好久」,也許不,也許「其實也無風雨也無晴,已經是個不錯的happy ending。」(頁11)而「但願人長久」,也許已經是她對子缺,敢許下的最大願望——「共嬋娟」,以隔「千里」的距離。「她跟我有點疏遠」,已經沒有辦法了,子缺也許永遠都不會知道,「她是個,嗯⋯⋯」怎樣的人呢?(——連我們也不知道)如同,子圓一開始就說出了,卻到最後也沒有到達的話:
「喂?妹妹啊,我到了。香港的東西都好貴的。這裡的包子幾好吃的。他們這裡買包子還送玩具,我把玩具留給了你,你看到肯定好喜歡的。到時候你來了,再喊爸爸帶我們去吃,好不?」
參考資料
李日康:〈專訪《但願人長久》祝紫嫣、謝咏欣——以童年治癒一生〉,《花字》第9期,頁2-11。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Dog Barking at the Moon,” https://www.phila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53949?.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Dog Barking at the Moon,” Looking to Write, Writing to Look, https://www.philamuseum.org/learn/educational-resources/dog-barking-at-the-m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