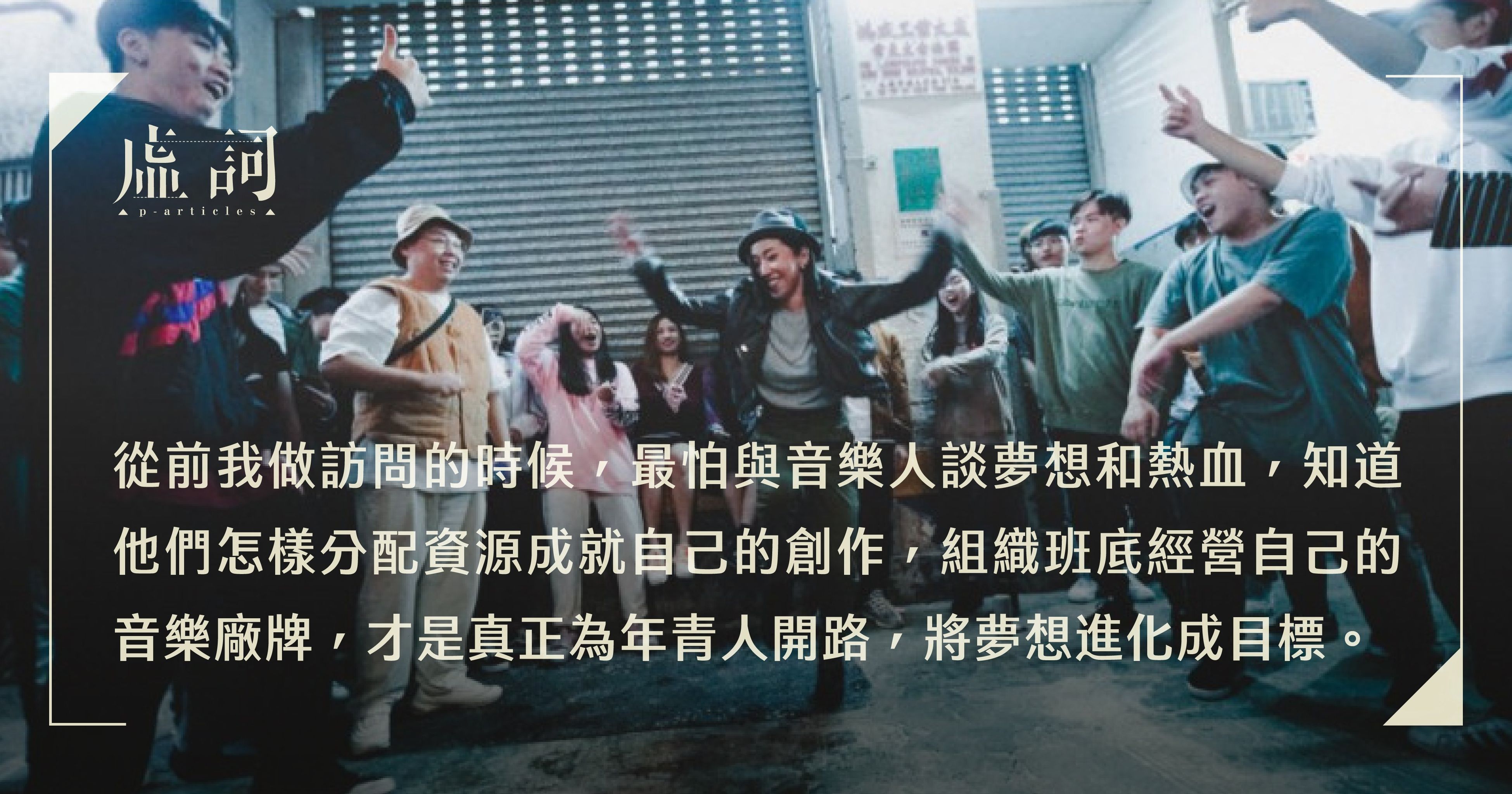影評 | by Moment Hung | 2021-03-25
前音樂記者Moment Hung評《狂舞派3》,借hip hop表達利益與創作之間的矛盾,雖然電影沒有為對抗地產霸權提供結局,但他認為創作者與平衡利益與立場之間,是可以有真正出口的。 (閱讀更多)
《夜香.鴛鴦.深水埗》的「一炮三響」
影評 | by 後浪 | 2021-04-01
《夜香.鴛鴦.深水埗》自上映以來,雖是本地小品製作,卻獲得不少觀眾支持,後浪細評戲中三條短片及一條紀錄片,是如何呼應香港味、對自由與未來的想像。 (閱讀更多)
零碎的記憶結集——論游靜《另起爐灶》
游靜的雜文集《另起爐灶》再度復刻,書中包含短篇小說、文化評論、散文、當代思潮等,江俊豪形容像是「家書」。但家的想像,今日卻比文集所寫的舊日往事更難以想像。雜文是零碎的記憶,但記憶的結集如《另起爐灶》,卻是現在整體歷史的一點憑藉。 (閱讀更多)
無垠的根:《好好拍電影》與香港身份
影評 | by 藍筠雅 | 2021-03-23
文念中執導的許鞍華紀錄片《好好拍電影》,正好為其四十年的電影人生作一總結。許鞍華的電影從來不易梳理,而在多年好友文念中的鏡頭下,除了關注社會議題與人文精神以外,更挖掘她在香港長大的童年,與祖父、父親、友人在於古詩、武俠電影與文學的淵源。 (閱讀更多)
《靈魂奇遇記》:夢想非唯一的生命路標
影評 | by 吳騫桐 | 2021-03-23
吳騫桐從《靈魂奇遇記》回視貫穿電影主題的爵士樂,重視即興表演的爵士樂,其核心元素正是「自由」,沒有固定的演奏規律,任由樂手變化音調節奏,強調的正是:主體將一己困苦的生命轉化成藝術性、精神性的涵養,那感受世界的自由心靈。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