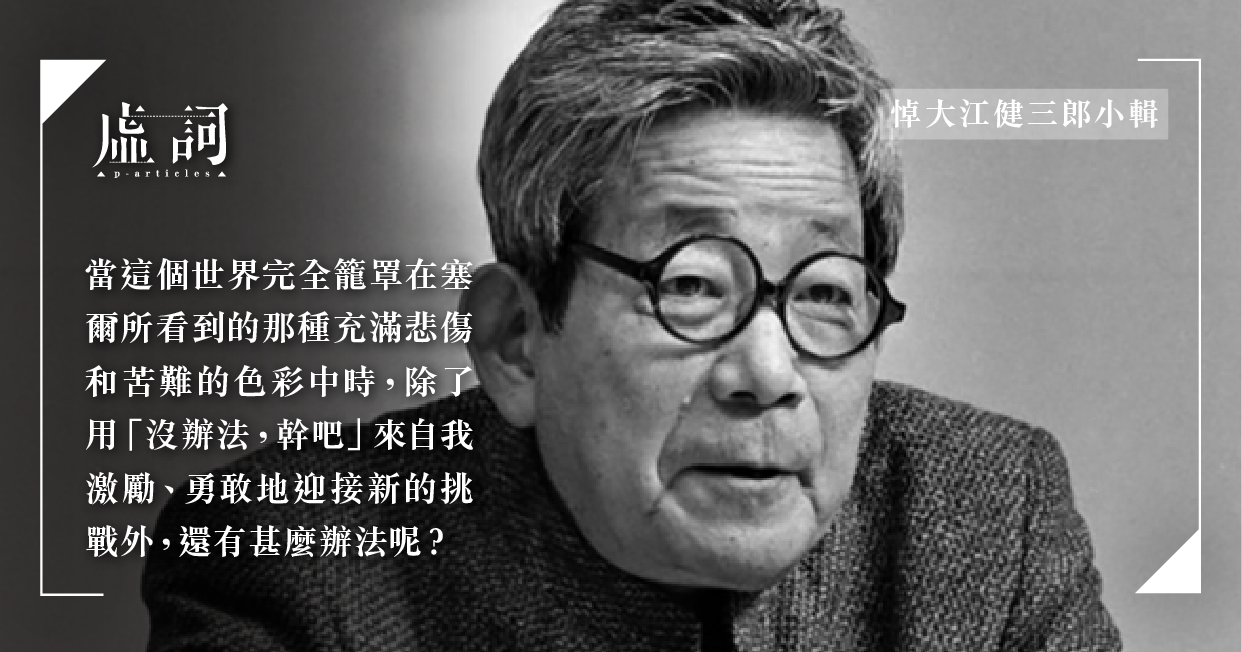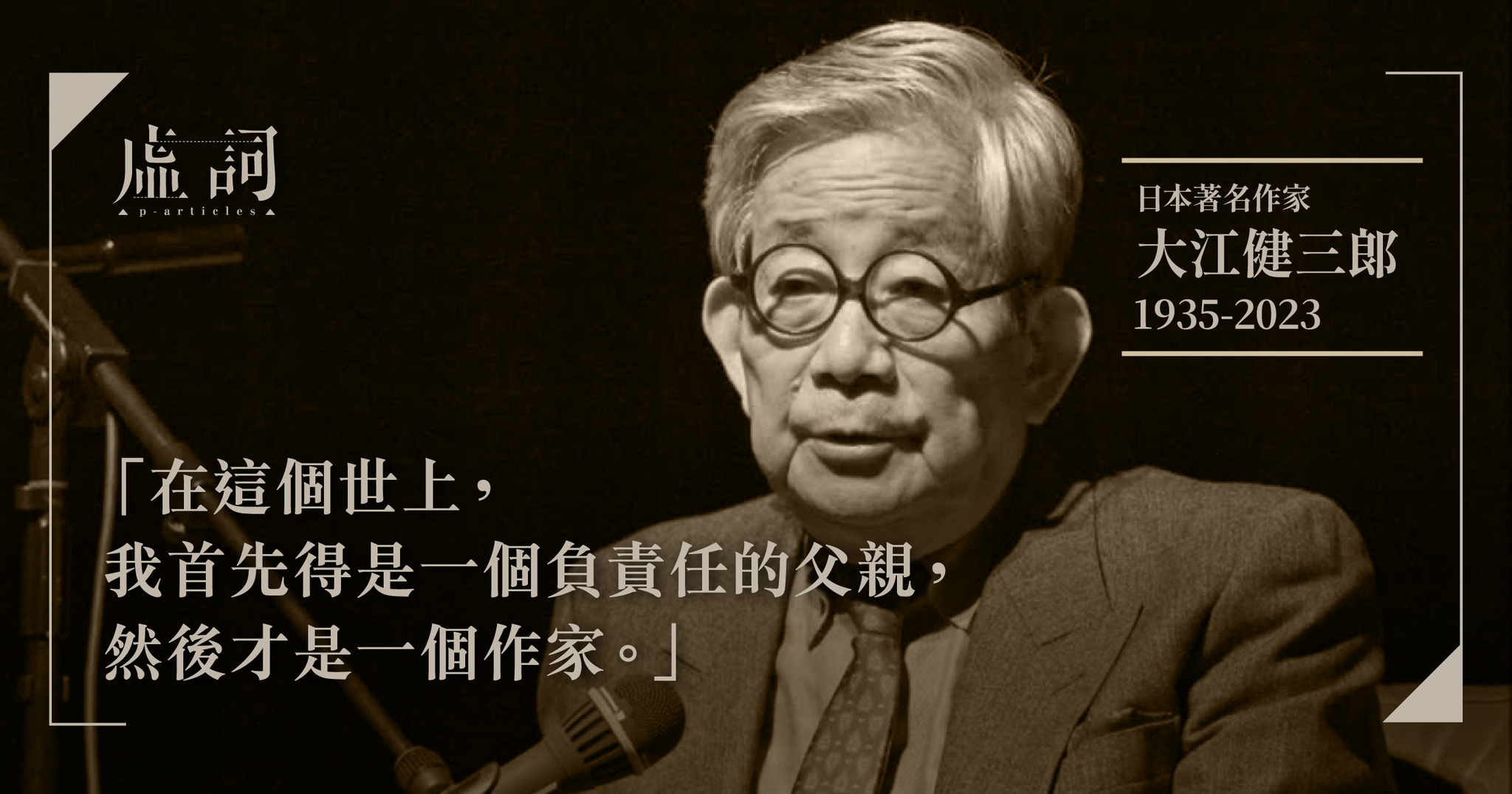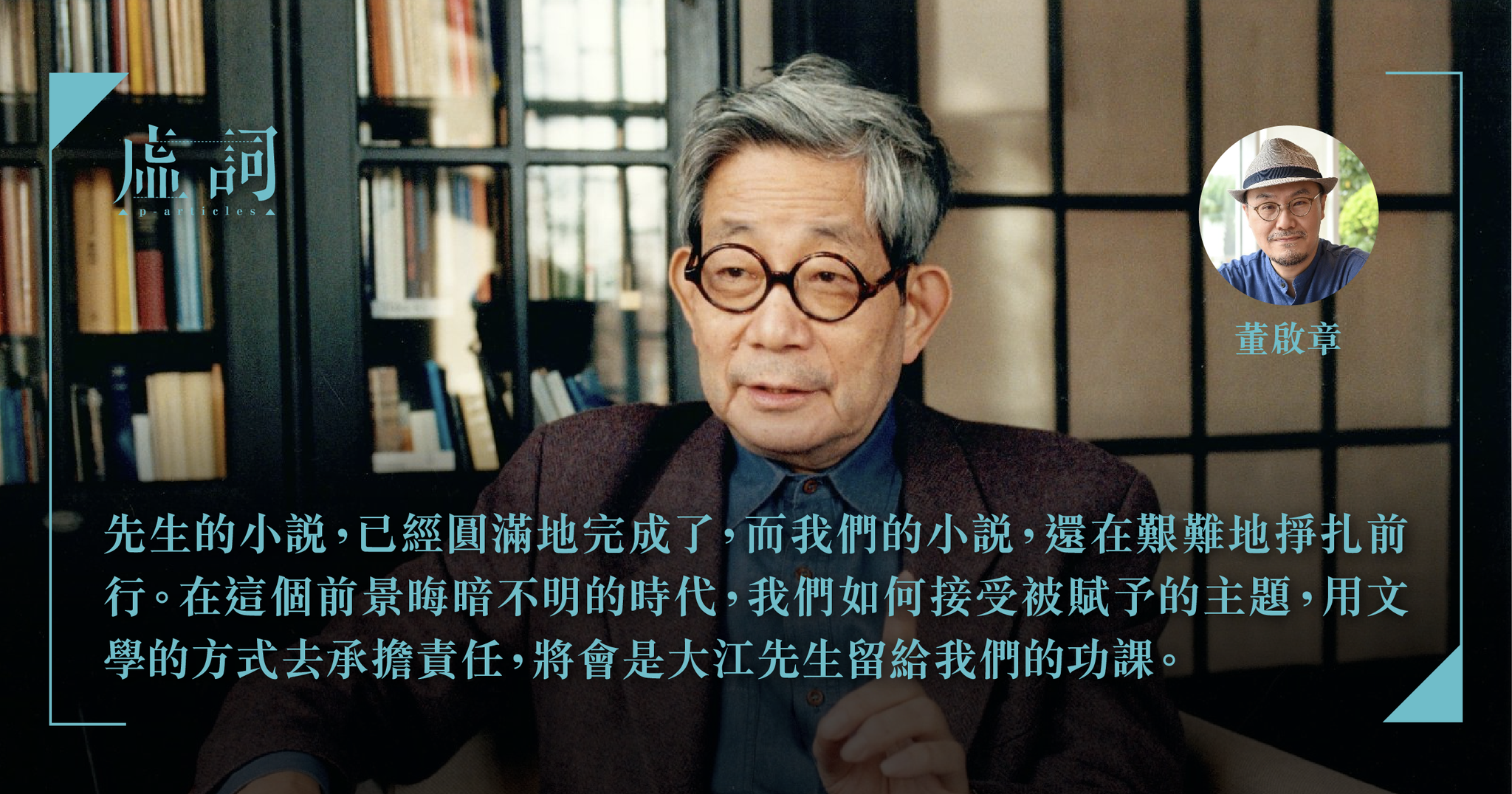悼大江健三郎小輯
專題小輯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3-04-06
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於2023年3月3日離逝,享年88歲。董啟章自言大江健三郎是他最崇敬、影響他最深遠的當代作家,這位高產的作家,堅持以「曖昧」戰鬥,小說以繁複和艱深著稱,深入政治、社會、宗教思考,以及知識與文學的討論。至於鄧正健則視大江健三郎為一位父親,因為大江健三郎小說創作的關鍵起點,正是他那個被稱為殘障的兒子大江光。他以向死而生至走近終點的心靈,表述出對未來孩子「共同生活」與「和解」的寄望。
在文壇獲獎無數的大江健三郎,曾獲頒川端康成文學獎、朝日獎等多個獎項,代表作品包括《個人的體驗》、《我們的時代》、《性的人間》等,1967年連載的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榮獲「谷崎潤一郎獎」,作品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1994年更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表揚他對「現代人類狀況的震撼描寫」,瑞典文學院形容他的作品「以詩的力量建構出一個幻想世界」、「存在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大江健三郎也成為繼川端康成後,第二位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
在〈時代賦予我主題〉一文中,大江先生引用南非作家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說法,認為「不是作家選擇主題,而是主題選擇作家。」先生繼續說:「如果自己被這個主題選中了,自己接受下來,想要負責任地寫下去,那麼對作家來說,就是加入到時代中去。英語有個詞commitment,在法語裡叫engagement,我想就是『加入』的意思。戈迪默是說,所謂加入到時代中去,就是用自己的一生去表現自己被賦予的主題,就是不停地寫作,以求能在死去的時候說,我完結了一個故事。」大江先生自言,時代賦予他的主題有三個。第一、是戰後的解放感,也即是民主主義的精神;第二、是核武器造成的痛苦,以至終身反核的責任;第三、是先天殘疾兒子的出生,令他下定與殘疾兒共生的決心。如果要加以補充的話,我會說:第四、對以天皇制為象徵的權力的批判,以及對暴力反抗的思考;第五、探索沒有宗教的靈魂修煉的可能;第六、面對老年與死亡,如何通過想像力行動起來。
在《寬鬆的紐帶》的前作《康復的家庭》裡,大江首次用這種散文文筆書寫兒子大江光,也描述了後來稱為「寬鬆的紐帶」的家庭關係。跟他從年輕時寫《個人的體驗》就開始的小說藝術思考歷程不同,這兩部散文集是他步入晚年、成為老人時寫的。他成為自己的樹,遇見仍是年輕父親的自己,如果說《個人的體驗》等系列小說創作是生命創傷體驗後的心靈康復治療,這兩部散文集則是多年以後,大江對總體生命感的整合,借榮格之話即「個體化」,儼如畫出一張曼荼羅,它逼近生命的本質,也逼近生命的終點。而在大江這個老年的生命點上,「個人的體驗」早已不再是個人,而是滿佈紐帶的共同生命感。我總覺得,雖然大江的書寫裡到處都是大江光的身影,但光終非一切,或即使說主要部份也不是。光只是紐帶群的節點,連結著大江健三郎的全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