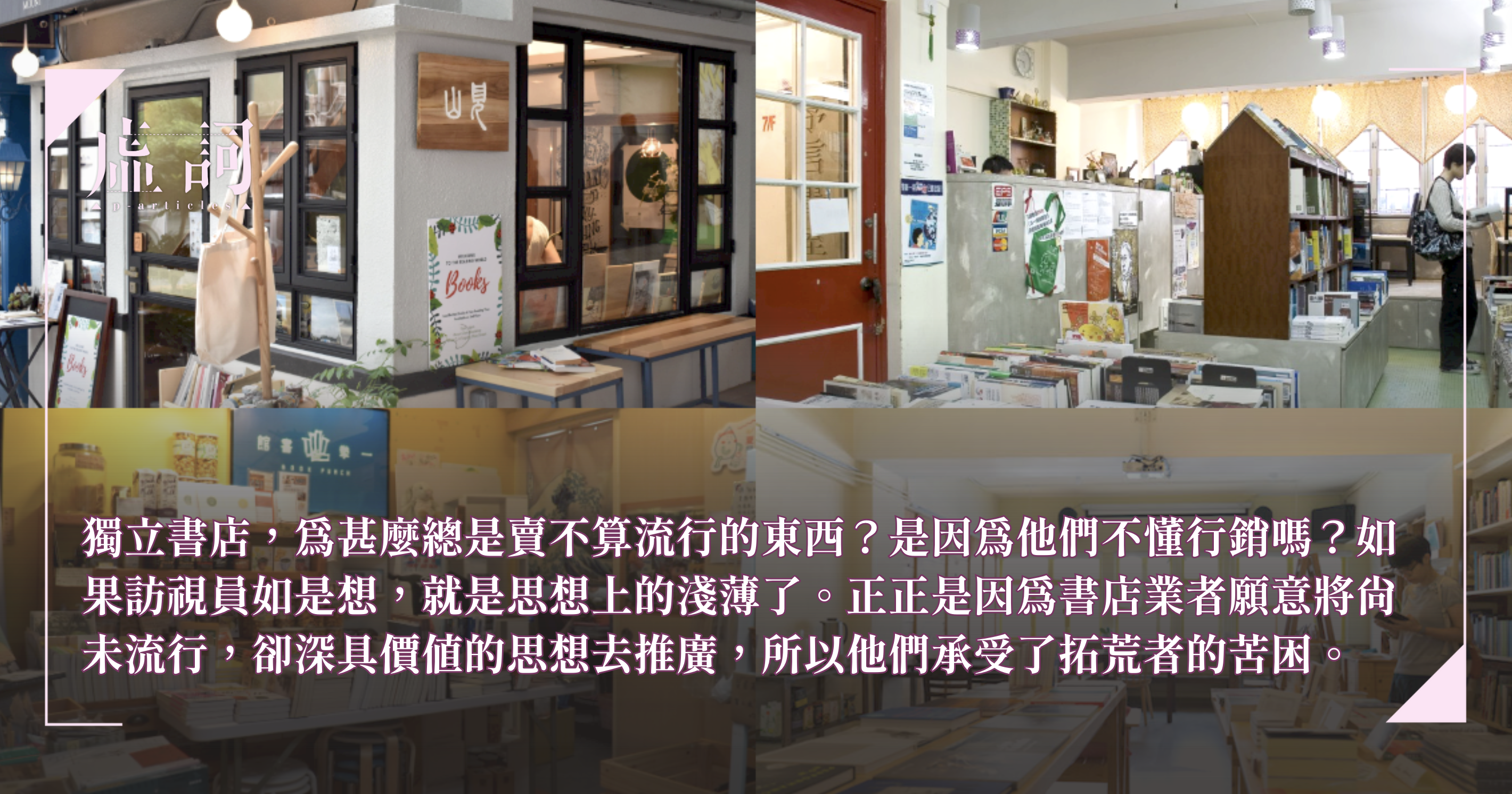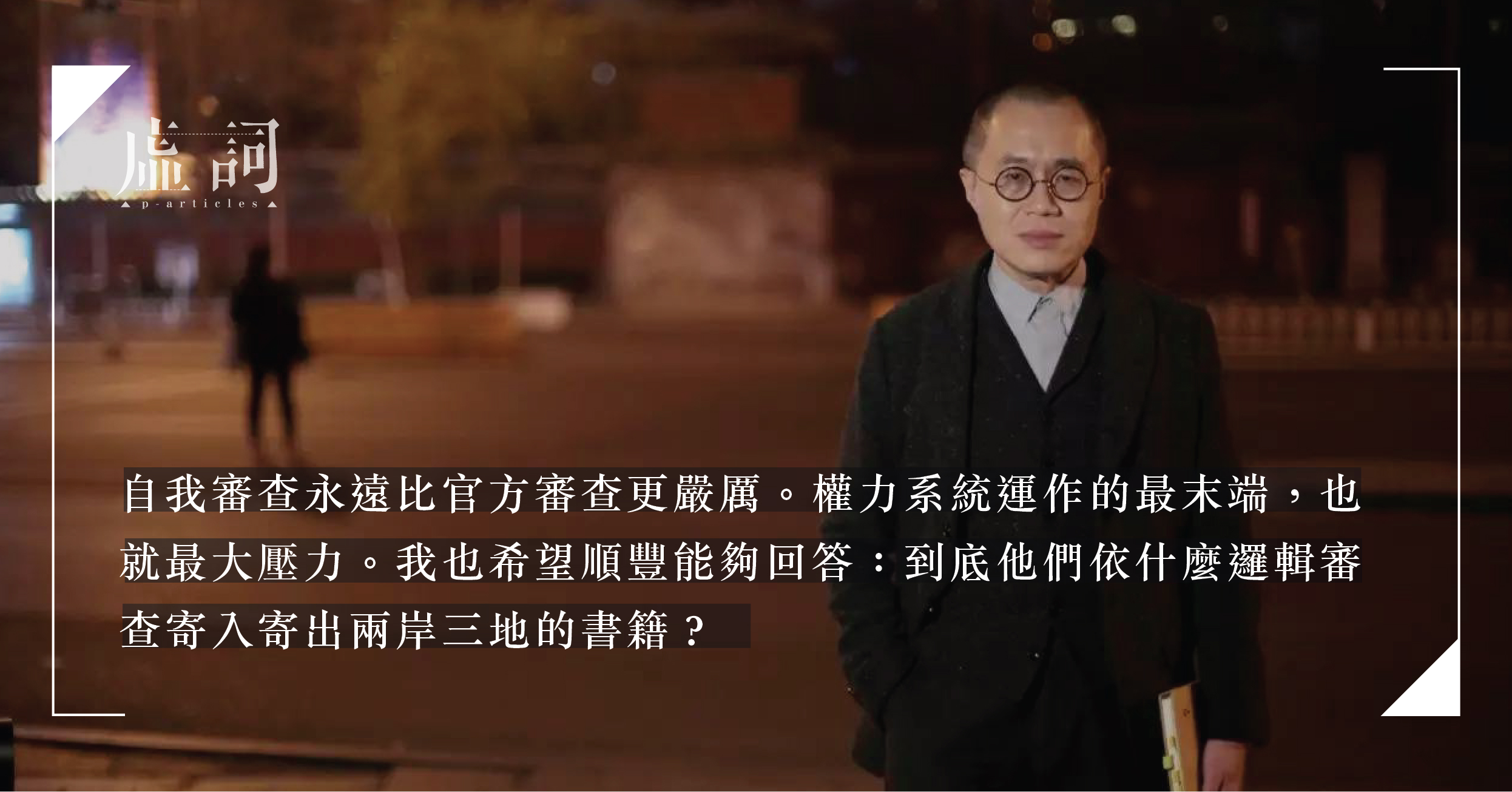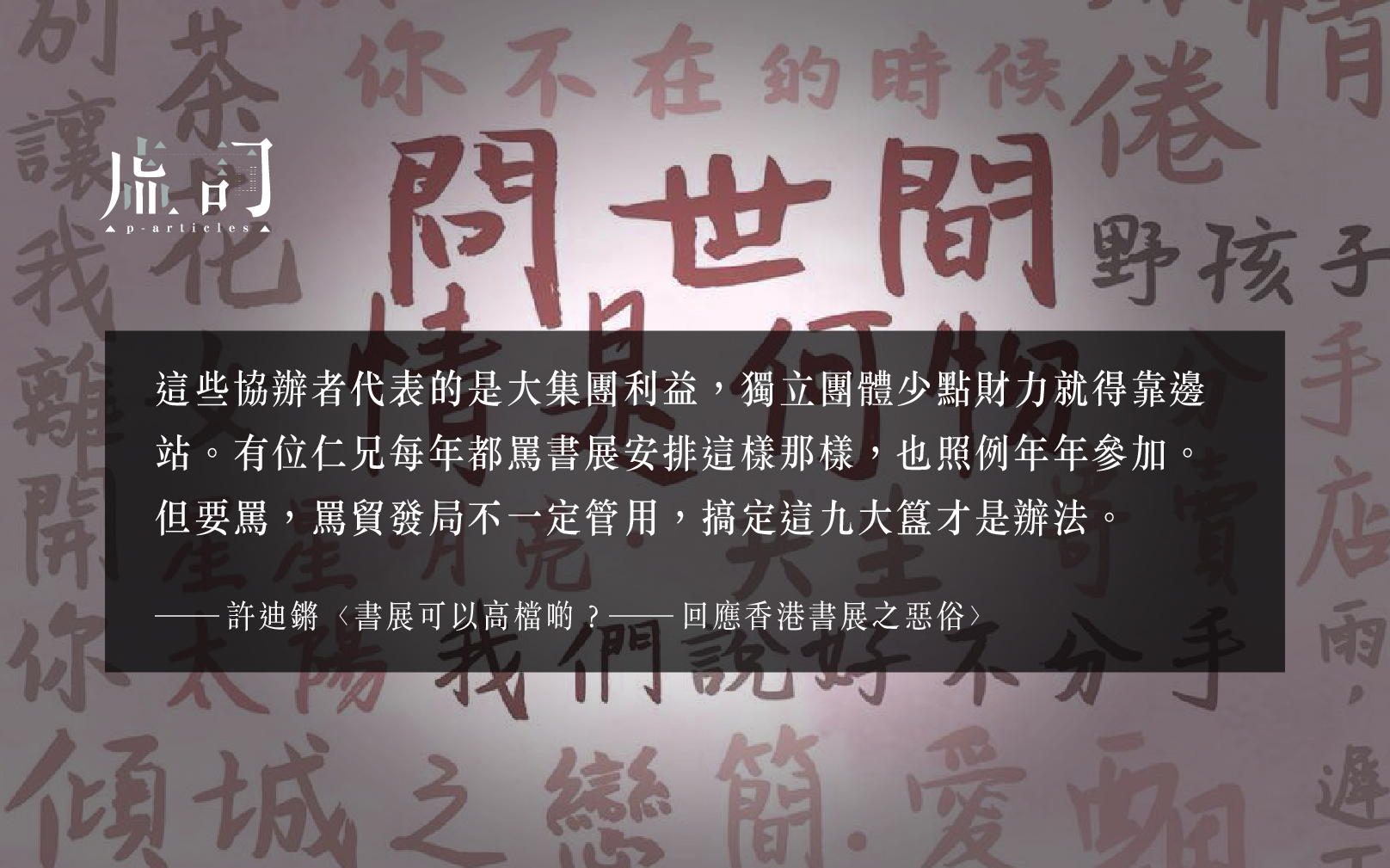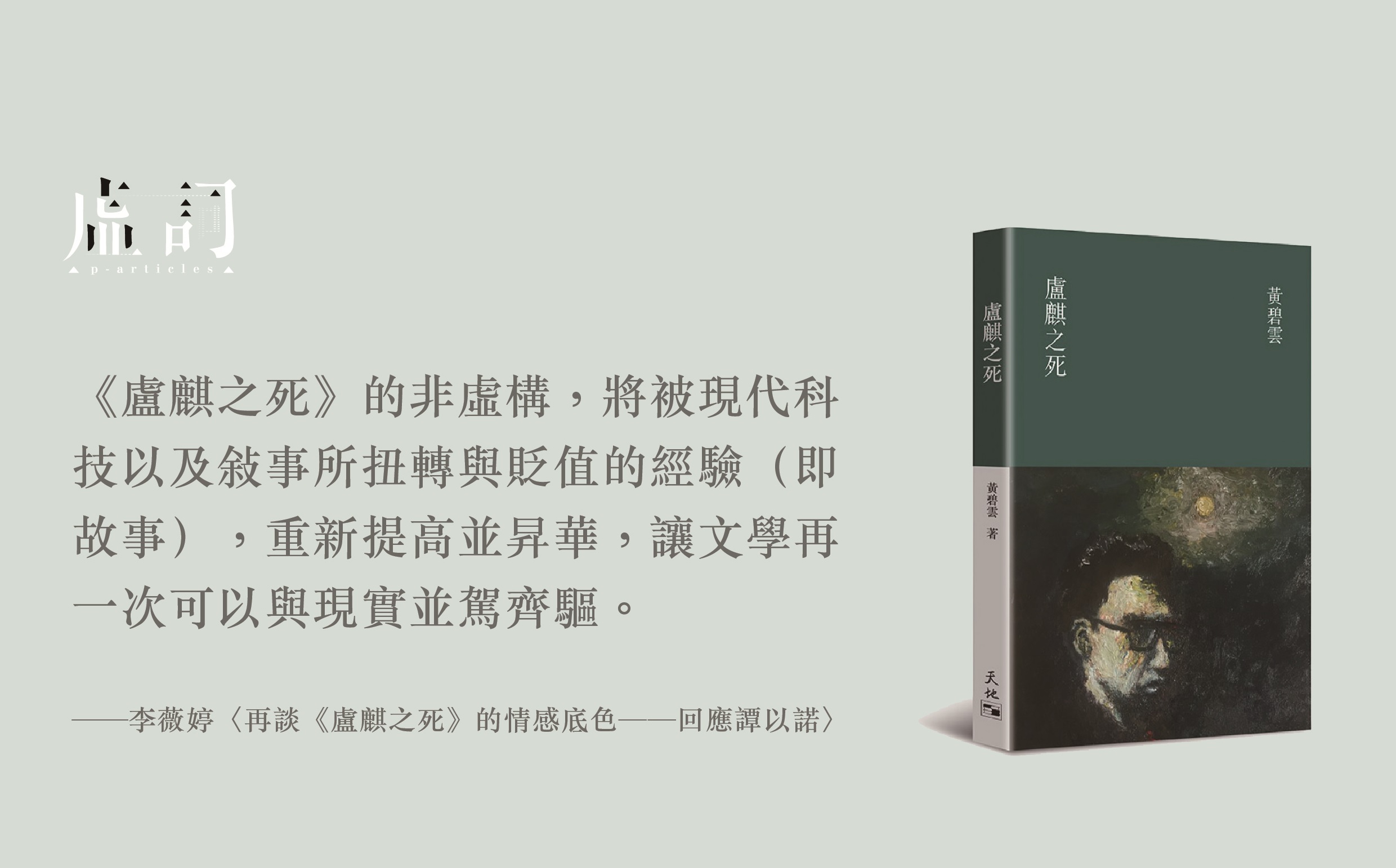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回應"

搞軭
小說 | by 周丹楓 | 2025-11-13
周丹楓來短篇小說,書寫一位十萬訂閱的YouTuber開箱十萬訂閱銀牌時,回顧自己過去的點滴。本為普通上班族不甘平凡,決心投身YouTuber行列。他從零開始,經歷無人問津、朋友鄙視、家人反對的低谷。他拍過電影評論,轉型做遊戲新聞,卻始終載浮載沉,更一度迷失自我,自覺是人生的「NPC」。在放棄邊緣,他受觀眾啟發,以「搞軭」世界的方式開創「我喺NPC」系列,以荒誕無厘頭風格意外爆紅。

莊梅岩發公開信斥政治打壓 質疑APA自定紅線 要求校方回應訪問取消原因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5-09-01
曾獲7次香港舞台劇最佳劇本獎、2010年獲藝發局頒發年度最佳藝術家獎、香港著名劇作家莊梅岩於今早(1日)透過社交平台發表公開信,表示自己去年接受香港演藝學院40週年校慶的舊生訪問,惟至今訪問影片仍未見上載。她在追問後獲悉,校方稱因無法上載至內地社交平台「小紅書」,遂將其影片從系列中剔除,並未主動通知她,令人質疑校方是否自設紅線及其限界在哪。莊梅岩在信中表明對此處理感到失望與痛心,並要求校方在三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回應四項疑問,同時將此事公開以示澄清與抗議。在公開信的結尾坦言,此舉可能令她的名字變得更敏感,未來租用母校場地或作品上演將會更困難,但她依然選擇發聲,旨在「奉勸各位,適可而止,別做得過份了」。她感慨道,若此信無法引起反思,「就讓這封信成為我在香港演藝生涯的墓誌銘,我亦無憾。」

十年又過去 都市傳說麥浚龍《風林火山》Trailer曝光!網民:電影似時間囊 網絡瘋傳4月上映引監製親自回應⋯⋯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5-03-24
由麥浚龍(Juno)執導、耗資四億打造的鉅製《風林火山》,由宣布開拍計起可謂「十年又過去」。3月17日,《風林火山》在香港藝術中心古天樂影院放映了約15分鐘的影片片段,還配以導演Juno的訪問,讓受邀嘉賓終於可以揭開這部電影神秘面紗。影片中出現大家耳熟能詳的「銅鑼灣落雪」場景,更有有金城武瞓西隧神秘劇情。網絡上更傳言電影將於4月上映,但隨即引來監製親身回應⋯⋯

不只「工」更是「人」:讀《香港移民家務工創作者作品選集》
其他 | by 別學優 | 2025-02-19
最近一名外傭因患癌被無理解僱一事鬧得沸沸揚揚。別學優看到此事慨嘆萬分,決定從書櫃拿出《香港移民家務工創作者作品選集》重讀,書中收錄了56份作品,大部份來至移民家務工,當中包括攝影作品、散文與詩。編者在介紹時說:「我們希望選集的內容能指向[移民家務工]各式各樣的流動身份:母親、女兒、姊妹、朋友、戀人、作家、藝術家、攝影師和講故事的人。」別學優認為此書的使命對在港的外傭尤其重要,因爲他們往往被視爲純粹的勞動者、「經濟貢獻」。對於在港的外傭,這個使命尤其重要,因爲他們往往被視爲純粹的勞動者、「經濟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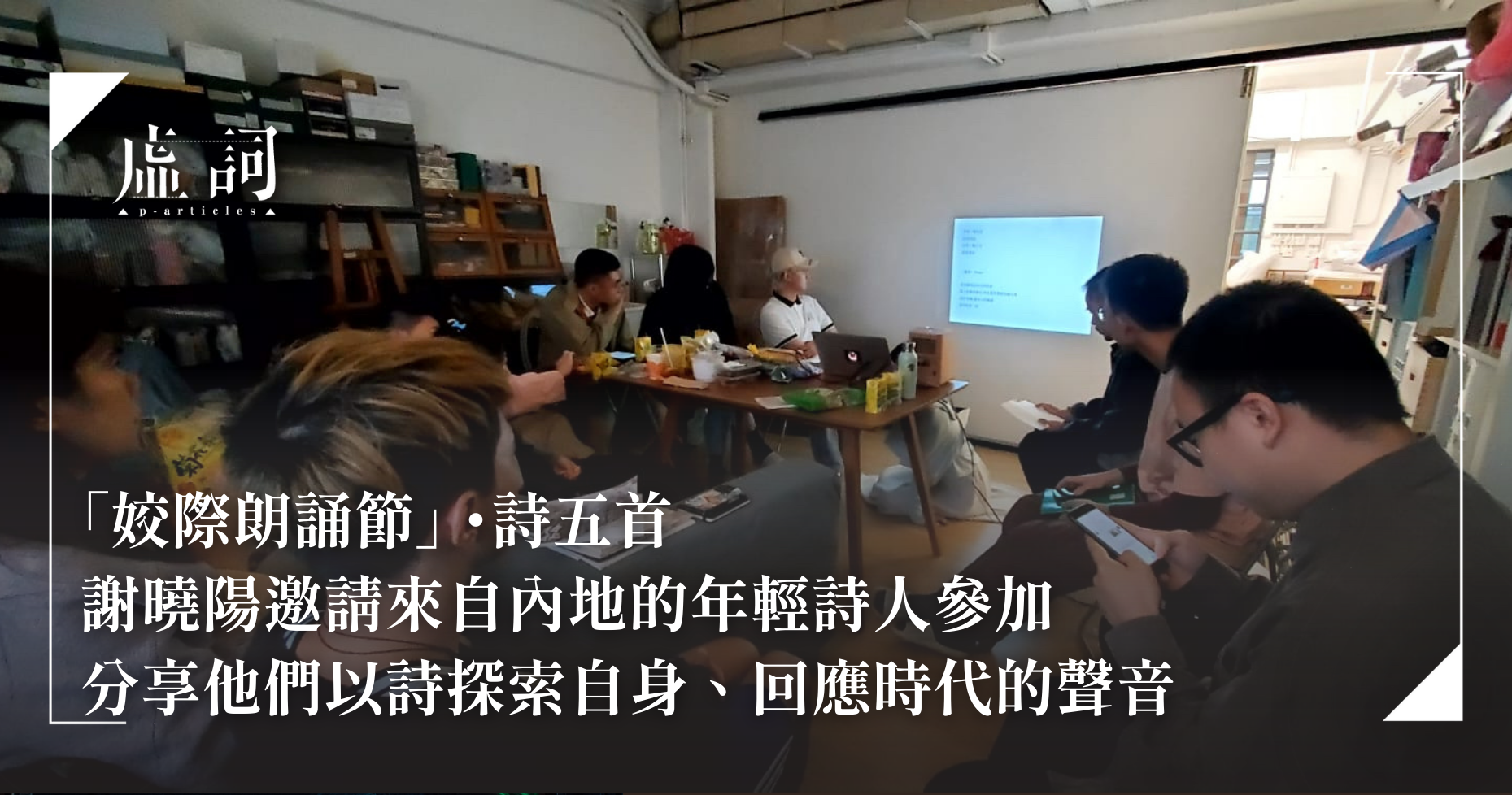
「姣際朗誦節」・詩五首:〈咯血的風鈴〉、〈玻璃水母——給一位朋友的禮物〉、〈借禪〉、〈寺印兩枚〉、〈一日的永恆〉
詩歌 | by 黃語蝶, 孫鑰, 李盲, 柯博凱, 談炯程 | 2025-02-14
「姣際朗誦節」是一個為詩歌而生的聚會,每月舉辦一次。舉辦人謝曉陽認為透過以粵語朗誦詩作,在聲音中釋放文字的力量,讓語言不只是紙上的印記,更成為震動空氣的靈魂。她表示,「姣」不只是大膽、張揚,更是一種對表達的熱愛與無畏。是次「姣際朗誦節」將詩歌版圖再次擴展,邀請來自內地的年輕詩人們參加。謝曉陽明白,縱使他們未必以粵語書寫,卻同樣帶著創作熱情,跨越地域,以詩探索自身、回應時代,並透過「姣際朗誦節」分享他們的聲音。黃語蝶如風鈴在安寧與懷疑之間顫響;孫鑰如水母般游弋於流動的夢;李盲讓禪意在數碼時代碰撞出荒誕的火花;柯博凱以俳句層層疊疊的呢喃;談炯程捕捉各種光影,低語日常的靜謐與無限。

【馴化事件】沐羽、梁莉姿回應「被馴化」爭議: 寫字的人無法被馴服 作品作為面向凝視的答案
報導 | by 沐羽, 梁莉姿 | 2024-10-10
《文訊》「被馴化了」一語從評審對沐羽與梁莉姿兩位香港寫作者的感嘆而生,兩位寫作者於事件發酵以後各自作出回應。 沐羽言,在頒獎以前,《文訊》舉辦了一場閉門對談,由三位八○後作家來與我們這些九○後切磋交流。其中一條問題是:「文學在一種政治高度關切或互為表裡(或拒絕互為表裡)的狀態,存有何種功用?此外,這樣的功用是否會被輕易收編?」雖然「收編」與「馴化」的強度不一樣,但兩者意涵接近。沐羽認為,香港人應該是最難被馴化的人群了。文學所強調的又是一種批判精神,它是自願不被馴化的藝術。從中沐羽提到傅柯講述基督教發展了一種牧領的治理方法,透過大規模的馴化過程,每個人都要被治理然後被拯救。對沐羽而言,他認為文學就是去表達一種自主權,此前提下寫字的人是無法被馴服的,唯有文學可以馴化他,而他亦始終在嘗試馴化文學。 梁莉姿回應指,剛來台灣的第一年身邊話語都在告訴她香港多麼可憐悲情,當中亦有許多對香港鞏固印象而帶來的誤解,但她認為這不止於理解與否,簡單粗暴的二元對立,她要問的是,要怎樣面對不同意的凝視?她寫一本書去描述凝視與被凝視之難,想描摹更凹凸的輪廓與不客氣地挑釁。但字一旦寫出,就必然被納入、捲進浪潮,落入凝視之中,話語(被)成為對立。面對這樣的處境,對她而言,作品就是她的答案,是她面向凝視的答案。

從〈無人之境〉談哀悼──讀葉梓誦的《斷層路徑》
書評 | by 海鹽 | 2024-10-01
海鹽在讀葉梓誦的《斷層路徑》時,見到當中提到在「往事的種種罪疚與哀傷並不能消除,只能不停地重複着哀悼的手勢」。令他聯想起陳奕迅的〈無人之境〉所表達了對愛人分離的傷痛與追憶,以及遺忘的困難。當一段感情結束,外界要求人們將對方藏進心底,彷彿要抹去一切記憶,然而這種遺忘的要求反而顯示了遺忘的不可能性。歌詞中的「共你隔着空在秘密通電,挑戰道德底線」猶如生者與幽靈之間的隱秘對話,這種交流不斷生成與變化,強化了幽靈的存在。 他亦寫到他方這一詞彙令人思考,除了地理上的遙遠,它也可以指向內心深處的記憶與情感。在電影《情書》中,主角的目光始終追隨已故的未婚夫,彷彿在與過去的幽靈溝通,漸漸與當下的現實斷開聯繫。要將目光從他方拉回當下,需要不斷地哀悼與重複,從而讓幽靈的面容變得模糊。在書寫中,面對內心的痛苦,海鹽試圖建立一套新的文字系統來表達那些無以名狀的情感。他知這是一個艱辛的旅程,但仍舊希望能夠透過這些書寫,找到生存的意義與出口。並希望得到w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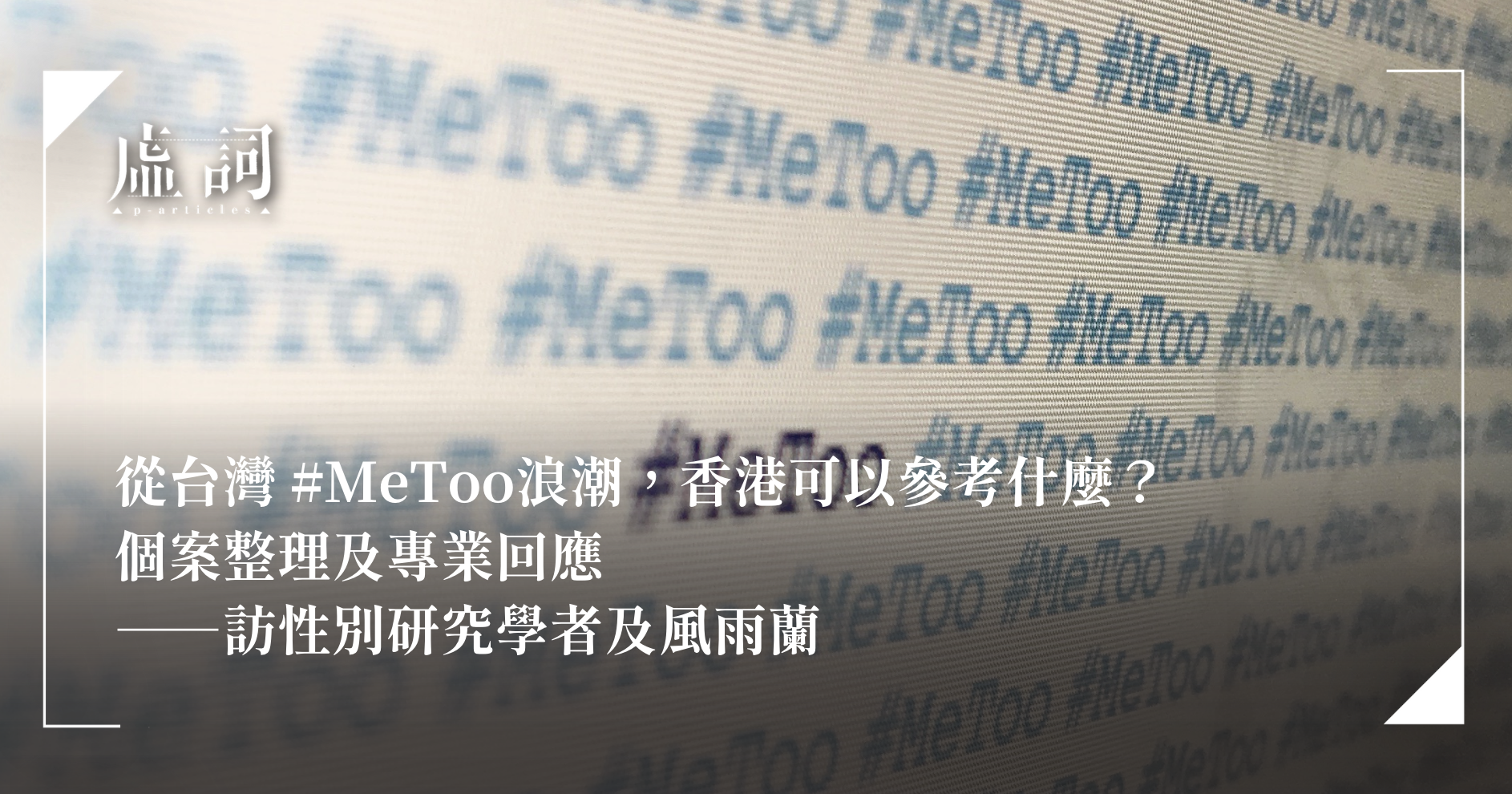
從台灣 #MeToo浪潮,香港可以參考什麼?個案整理及專業回應——訪性別研究學者及風雨蘭
其他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3-06-25
#Me Too運動,是一場自2017年底始於美國,旋即席捲全球的反性侵及性騷擾社會運動,運動的核心宗旨在於「用同理心實現賦權」,讓不同種族與階層的人都可參與,並互相團結起來。然而,這場運動發展以來,也引發很多爭議及討論,如對於構成性騷擾的條件、性表達的自由、如何確認指證的可信性、對受害者的協助和支援等等。這些對Me Too支持者和批評者而言,都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而有效的討論,正是性別平權上重要一步。

回應金像獎風波及機制爭議——訪新晉導演、業界代表、文化評論人
專訪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3-04-25
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可能是歷來賽果最受外界質疑的一屆。新一代電影以過半數提名,撐起了半張提名名單,惟最終得獎比例卻相對少,引來坊間質疑:到底金像獎有否真心希望扶持新人、推動世代交替?再加上《給十九歲的我》獲最佳電影的爭議,更增加了外界對金像獎機制的質疑。網絡狠批者眾,但真正在做電影的人怎麼看,到底新世代電影如何能夠有更多支持和機會、機制能否更開放和公平,這些問題都需要具體而切實地談論,也需要業內人士的真誠回應。

「香港文學季:水土不伏」前言——以文學藝術回應時代,讓幽微的美好生長
無秩序編輯室 | by 香港文學館 | 2022-11-07
海港與島嶼,經歷無數變遷、潮漲潮退,從文學世界中,我們總能回顧一二,重新建構變幻以前的社區。今屆香港文學季以「水土不伏」為主題,透過文學,我們創作、感受,連結這座熟悉且獨特的城市,以文學藝術視角重新觀察「水」在香港所擔當的角色,重看舊日回憶,認識本土歷史,再往理想出發。

回應當下,超越時間限制的書寫——鄧小樺 X 何雪瑩「斑駁療傷,理論日常」讀書會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1-10-27
香港文學生活館早前與獨立出版迷你書展主辦「斑駁療傷,理論日常」讀書會,作者鄧小樺與城巿研究者何雪瑩,在評論人江祈穎的主持下,跟一眾讀者相聚富德樓,漫談在書寫中如何讓昔日與當下對話,亂世之下怎樣面對挫折與療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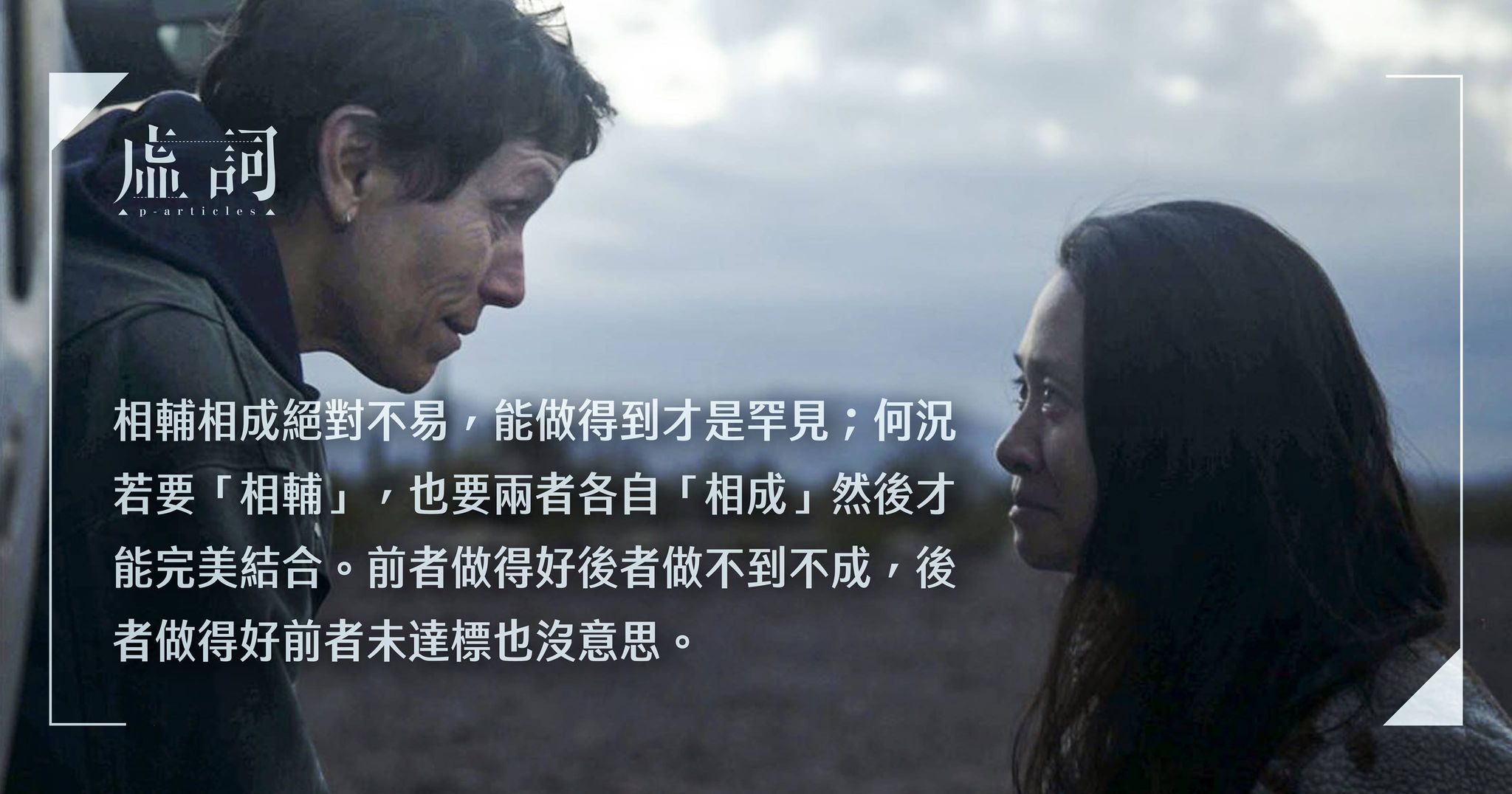
《浪跡天地》:談評論者的「思維陷阱」,對劉建均影評的幾點回應
影評 | by 陳廣隆 | 2021-08-11
近讀劉建均早前對《浪跡天地》的評論,陳廣隆認為它是相關影評中,寫得甚為出色的一篇,有些論點更值得仔細討論,並對此作出幾點回應。當我們回憶觀影歷程時,如何明確分辨自己到底在甚麼時候生出怎樣的情感並得出怎樣的結論,陳廣隆借這篇文章嘗試分析。

【教育侏羅紀】追求良善的路:回應教育局的「不知道」
教育侏羅紀 | by 余是說 | 2021-09-23
奧斯卡經典電影 Good Will Hunting 本有追求良善的意思,面對當前的困局,同行善良之路或許就是教育的真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