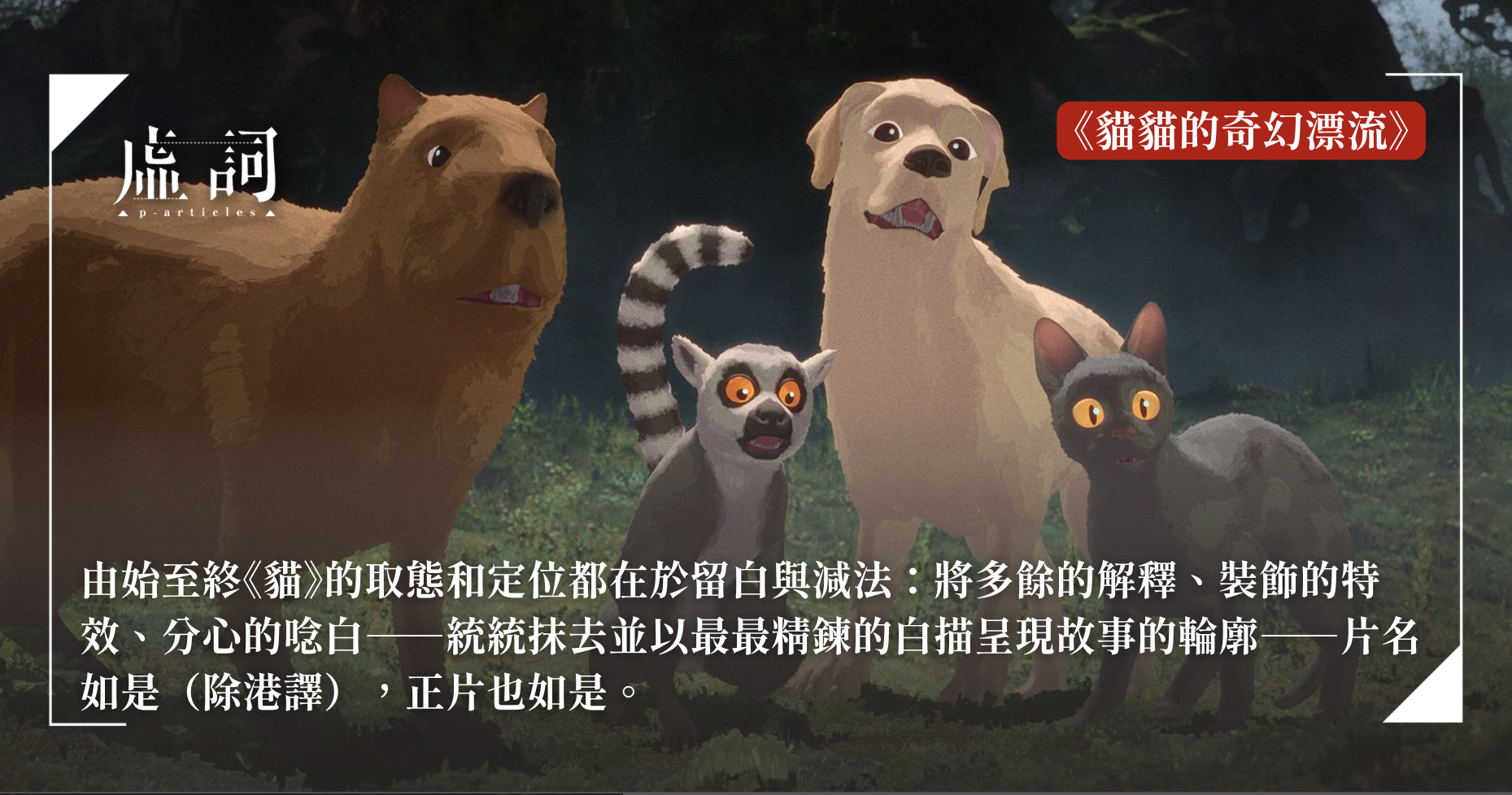看《貓貓的奇幻漂流》雜感
影評 | by 泊泉 | 2025-05-07
是因為看到奧斯卡和金球獎最佳動畫獎的名銜才購票進場的——本身因為香港譯名「貓貓的奇幻漂流」過於子供向而有所卻步,所幸機緣巧合之下還是決定一看無妨。後來,上網搜尋得知原片的拉脫維亞語片名‘Straume’(有流動、水流、溪流等意思),和英語譯名‘Flow’,兩者其實均不是香港譯法那份「在地」得喧賓奪主的商業佐料味,反而更似是略帶禪思的某款茶香。因對戲名的先入為主而差點擦身而過這回事,真的「好彩有入場,差點又被陰了一鑊。」
2024年上映的跨國合作動畫片(拉脫維亞、比利時、法國),全劇不含對白的設計透露點藝高人膽大,而又實在合乎情理。《貓》的作畫風格和作為動畫大國的日本動畫相比,其實並沒有在作畫的技術層面上佔多少優勢或突破,甚至可以說《貓》的畫風趨近於《薩爾達傳說》那種「你知道是為了便利動作流暢性而不得不在畫質上作妥協」的那種折衷,而在日本動畫中舉足輕重的「聲優」配音一環更是完全不適用於不設對白的《貓》——可見,由始至終《貓》的取態和定位都在於留白與減法:將多餘的解釋、裝飾的特效、分心的唸白——統統抹去並以最最精鍊的白描呈現故事的輪廓——片名如是(除港譯),正片也如是。
如果說有些電影頗像小說而有些似散文(相信合適的例子大家都可以順手拈來),那麼《貓》大概裹著詩的質地。於是抱著「既然是詩想必就沒有標準答案(也就不大可能被指責為誤讀吧!)」的想法,暢快地消化著那一堆堆溢於言表的細節,並安心地,哼起了這篇觀後感。
1. 人
由故事最早期貓寄居的空屋,裡面的紙繪、木雕,到逃生的木舟,再後來漂流途中遇到的手鏡、器皿、水球,乃至後期小島上的串旗——人類始終缺席,卻又始終無處不在。事實上連電影簡介也毫不避諱地點明了「充滿人類痕跡」這弔詭的設計,顯然這悖論般的背景設定是作者刻意為之。
故事開初,災難發生,水位上升,所有動物輪流登船避難。有人因而聯想起聖經裡的天罰,但聖經裡的四十夜大雨是為了審判作惡多端的人,反觀《貓》中人類終究不在場,那麼若然果真是天譴,懲罰對象又該是在場的誰?而若抽離宗教的框架,「降罪」的主體可不可以是自然本身?——祂可能正因溫室氣體而惱怒著,又或者,一切只是祂百無聊賴時打的某個呵欠。
可能是近年看了不少「人類為延續種族存活,必須搜索地球之外適合生活的星體」為前設所衍生的星際冒險電影,如近期的《米奇17號》(Mickey 17)、經典的《星際效應》(Interstellar)、《異形》(Alien)等。不禁想像,打從故事開端這座荒落的星球,會不會已經是人類為避難遷移之後所發生的故事?若是,那麼到了故事後期鶴鷲升天謎團,也有可能如同當日諾亞挑選乘客般,在《貓》中實則是由已經駕馭大氣層的人類所邀請。
而無論是哪種推論,不論星球不論動物,似乎都在經歷著人類所留下的爛攤子。「到底人類離場之後,一切會否變得更好或更壞」,又或者,自從人類離席,所謂「好」和「壞」的概念也隨之煙滅,而故事的重點,可能正在於非人的故事本身、漂流本身。
2. 球
被繩網包裹的球同樣貫穿了整部電影。當黑貓在舊居附近的岸邊觀察水位,同時已發現了球。那時狗狗們集體啟航,黑貓沒有跟隨,到後來水位持續攀升,黑貓被逼到了貓型岩嶺的頂端無路可逃,水球再次浮現,本以為黑貓終於要孤注一擲了,結果貓還是躑躅不前。大概所謂潛能、本能,或慾求,也並非一遇上甚麼危機關頭就能傾瀉而出的,像一道日久失修的逃生門,可能到頭來,還是會在決定逃逸那天才發現門栓早已生鏽上鎖無法打開。
只知道球是藍色的、透光的、具浮力的,至於質地、物料、用途等,我們只能一知半解。而舉凡圓球狀的,尤其被包裹、綑綁的,都容易讓人聯想到作為某種「內核」的存在——即藍球極有可能象徵了某些無以名狀之物事的核心——它不一定是屬於誰或代表誰的,也不一定是恆定不變的,甚至,不一定是可解的、或可感的。
但我們都知道最後一次在暴雨中溺水時,黑貓用力地,終於攥緊了它。
3. 鯨
黑貓在劇中第一次溺水時,與海底的距離曾經只有半步之遙,而最後拯救了貓的,正是素未謀面的那尾鯨。
但《貓》的編劇又似乎不打算單憑該次拯救讓鯨背負上刻板的「善」的印象,而是,更為抽離更為中立的某種形象。連黑貓也知道,那其實不過是鯨魚一次無心插柳的「唞大氣」,如同一屏始終冷靜的浪,有時戴舟,又有時覆舟。可能《貓》中龐大且離群索居的鯨魚,之於細小的貓和貓的朋友們,也不過是深不可測的大自然之替身,舉手抬足,都在提醒你們:它既可以在你落難的時候背你離開水底;也可以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裡,措不及防地,動搖你以為安定了的船。
最後鯨魚擱淺,黑貓上前,蹭了蹭鯨魚,見證一場風暴的漸逝;同時等待——下一場暴雨的開幕。
(然後鯨魚於片尾重回海洋,牠畢竟是比較適合以鯨落的姿態劃上句點。)
4. 鶴
在鶴群圍捕黑貓,將貓逼至懸崖時,最最遺世獨立的那隻鶴為了原則、為了貓,竟然冒大不韙地挺身而出,以致與「同伴」反目成仇,雙方大打出手,結果鶴的右翼受傷(直到故事終段牠羽化升天,翅膀卻始終沒有痊癒),最終更被「同伴」狠心拋棄,只能拖著傷痕累累的折翼看「同伴」們遠走高飛。
解救他者,有時並不必然建立於立場上的利害瓜葛。像鶴未曾受過黑貓的小恩小惠,仍在萍水相逢時向對方慷慨分享了自己狩獵得的一尾魚(雖然被同伴搶去了)。甚至發人深省的是,到底「同伴」的條件是否必然建基於同樣的物種、相似的模樣、共同的家園?鶴的「同伴」們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同伴嗎?貓和貓的朋友們,又稱得上是鶴的同伴嗎?
無論如何,登上黑貓一夥的船上之後,鶴依然自發地擔當起掌舵人的角色。雖然在是否應該拯救受難的狗狗們之時,鶴的冷靜略顯得不近人情(但有沒有可能,得以翱翔自如的鶴早已見盡過人性的惡,又或者在更早的時候,已在行經別處時,如同鶴早遇見過黑貓般,也曾遇見狗狗而領教過狗狗的自私,因此才拒絕讓牠們上船呢?),但在其他夥伴搶過掌舵的崗位之後,晃動不斷的船隻反證了鶴一直以來的默默付出其實是多麼的不容易。
但是鶴也不曾抱怨。牠只是選擇了在某個暴風雨的日子裡,拖著尚未痊癒的折翼,勉強地,獨自飛往孤島。黑貓追趕而至,貓和鶴在島嶼頂部的壇上一齊失重,然後鶴便羽化升天。鶴的離場可說是整部電影裡最為抽象又最為唏噓的一幕,我們無法知悉鶴的離開是主動的或是被動的(是失望還是病重)、是心理的還是物理的(是索居抑或離世)。所謂「水至清則無魚」,在生活裡選擇恪守原則的那人總是比較疲憊。
保有善良無疑是艱難的,但更難的,必然是付諸實踐。
5. 狗
拉布拉多是唯一一隻由始至終仍對黑貓釋出真摯善意的犬。打從他們初次在叢林中共同遇溺並一齊得救,拉布拉多犬便對黑貓(莫名地)親近如故。拉布拉多熱情而黑貓內斂,兩者在相處間的一進一退儼然如現今人們刻板印象中的「I人(內向者)與E人(外向者)的相處之道」的展現。或許,I人有時果真是被E人「收留」的。
而後段加入上船的其他犬隻則似是為了反襯拉布拉多的忠心和真誠。例如在船上時,甫登船(作為被拯救者)的狗狗們毫不客氣地便把黑貓狩獵所得的魚兒一掃而空,接著又對狐猴的收藏品動起歪念,雙方爭持不下,最終更導致狐猴愛不釋手的手鏡,連同彼此的信任,一併碎得分崩離析。但最大的反襯仍屬劇情尾端,水豚受困搖搖欲墜的樹上岌岌可危,眾人傾力救援,拉緊繩索。性命攸關之際,一隻兔子躍過,狗狗們(除拉布拉多)居然見利忘義,一股腦的轉身便離去,追著那逃逸的兔子而捨水豚不顧。
「狗」是他們的共同標籤,是他們相近的血脈、輪廓、習性——但一個個體的本質是否能被「種族」所定義或框限呢?拉布拉多起初和別的狗狗們共同出航,後來不知因何故而分道揚鑣,最後即便在黑貓的船上重遇,最終拉布拉多仍然選擇了與背景各異的黑貓一夥為伍。在這紛亂而又逐漸緊緻的時代裡,有時不禁反思,我們終日追尋著的所謂「根」、所謂「本源」、所謂「認同」,會否有時更容易在某些遠方覓得呢。
談回狗狗的背叛,可以說其實狗狗也非「邪惡」而只是「不夠成熟」嗎(如此說來拉布拉多其實也並不「成熟」吧,但兩者行為南轅北轍)?大概也不錯。但若肆意縱容自身的動物性,知悉自己的無知而又執意保持無知——先不論「對錯」——大抵是注定了會釀成悲劇的。
6. 鹿
黑貓第一次見到鹿群是在災難前夕,那時牠在奔馳的鹿群中徬徨無助,只能蜷曲閃躲。
黑貓第二次見到鹿群是在最後的島上,為鯨魚送上祝福之後。那時黑貓身板挺直,倚著夥伴,眼神堅定,不再游移。
鹿最直觀的意圖是被視作「災難的警號」。換個更深層的角度,鹿其實也映照著黑貓「直面災難時的態度和姿勢」。
7. 貓
貓或許正是所有困頓的寫照——是所有觀看著,並且咀嚼、消化、反芻這部電影的觀眾:我們都曾在某個生活的節點上選擇過疏離,寧願緊抱未必安穩恆久的日常,仍頹敗地拒絕變故,卻終於在反覆的被動經歷和摩擦間,與世界生出聯繫,甚至,在又一次準備墜落之前,依然對那些曾經路過的物事有所牽掛。
看了某些觀眾評價,說《貓》其實就是一套沉悶至極又故作姿態的藝術片,說那些觀後貌似獲益良多的觀眾說穿了也只是國王新衣的圍觀民眾,為了不被揭穿是濫竽充數而只能似懂非懂。我想了想,其實自己上述所寫的也確實可能充滿過份解讀和誤判,但,這其實又有甚麼關係呢——願意思考總比放空好,而願意冒險又比躺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