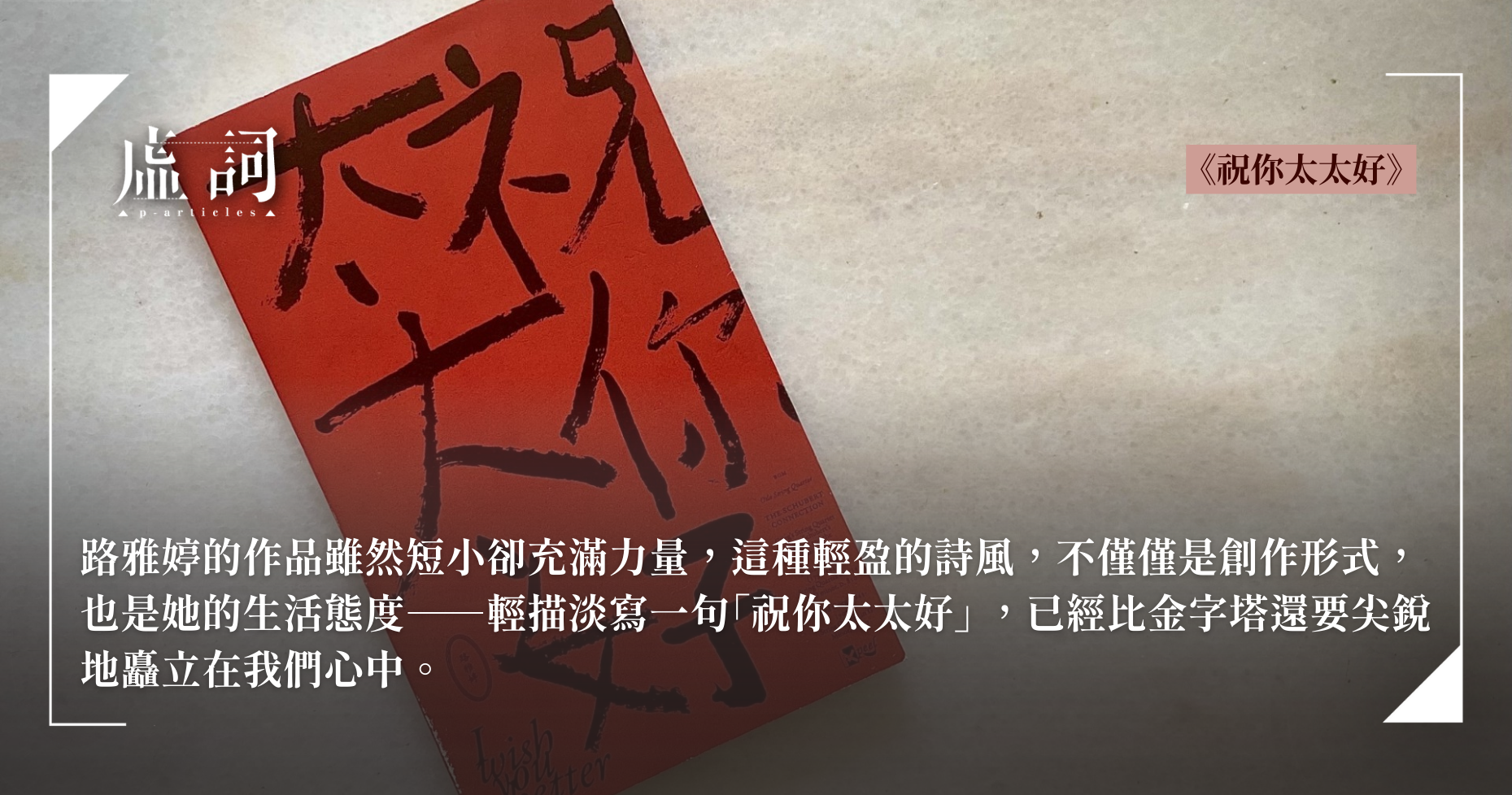短詩的輕盈魅力:探析路雅婷的《祝你太太好》
路過芳芳美容美髮
芳芳不在
《在去宏達北路郵局的路上》路雅婷
最近出席一個文學頒獎禮,新詩評審說他無法認同短詩,「好的東西沒一件是容易的,建金字塔、羅浮宮會容易嗎?好的詩是有架構的,精緻的……」這使我十分納悶,這反映了:一、短詩沒可能在文學比賽獲獎,二、他喜歡金字塔和羅浮宮——莫奈筆下那種簡陋農舍大概就不是什麼好東西了?如果把這種眼光套在藝術,不夠大的畫面、沒有景深、陰影,也統統不算好畫了。
或許他意思是:短詩沒法充分展現作者的文學實力,那可能是僥幸,是靈光一閃,是曇花一現——可這不就是詩的本質嗎?最近讀到北京八十後詩人路雅婷的「非賣品」詩集《祝你太太好》(傳說是她不想去申請ISBN,所以詩集成了朋友間口耳手相傳的非賣品),書內統統都是短詩——句子短,行數也少,卻讓我感受到短詩的力量和魅力。
路雅婷的詩肯定不是金字塔。書中何小竹與她的訪談提到,路雅婷說自己「本名很普通,跟所有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一樣,一抓一大把」,然後她又改了個同樣普通,「一抓一大把」的筆名。有些詩人志向宏大,以歷史和社會責任出發,寫以巴衝突、烏俄戰爭,路雅婷卻寫《一隻蜈蚣飛到十七樓》、《雞眼膏好用我也推薦給你》、《夜裡沒人跟我搶秋千》——你以為她是隨心作詩,她卻是特地辭掉正職去寫好這本詩集。
《祝你太太好》看似是一堆生活中的無聊瑣碎事,卻讓人想起種種社會現象。以書中最短的詩《在去宏達北路郵局的路上》為例,寥寥兩句就令讀者不禁想:這人找芳芳幹嗎?芳芳是誰?這個帶著香氣,實際上又有點俗氣的名字,在城市中是怎麼樣的標誌和存在?芳芳是真名嗎?還是店名?為什麼要改這個名?女生找芳芳是為了聊天?男生找她是另有所圖?世上有多少個芳芳,在各大美容美髮店,成為城市人心靈的停泊站?這一切問號,已遠遠超出了詩的字數,路雅婷也不想解答,保持詩的輕盈和愉快,繼續在城市遊走。
有時她帶著行為藝術家的精神,拿慣常事物來做小實驗,如《在沙發底下撿到一粒赤峰瓜子》:
我要把它帶回故鄉
從北京坐火車到赤峰
在那裡將它安頓好
再從赤峰坐火車
回到北京
回來時
可以坐慢車
這使我想起一個藝術家朋友。話說2020年有新聞傳出,香港機場三跑工程填海的海砂,是由中國抽砂船從台灣的馬祖和澎湖一帶非法盜取,再供應至香港。於是朋友計劃做一個藝術作品,從機場抓一把沙,再坐飛機到澎湖,把沙子還給台灣——不過幾年也不見行動,大概放棄了。路雅婷不知是帶著何種意圖,想把地下角落的瓜子帶回赤峰?但她確切地用她的詩把北京的瓜子和內蒙古連結起來了,讀者得以用新視角審視身邊習以為常的物件,重新想像它的供應鏈和各種連結。從何小祝的訪問中,路雅婷說相比結構,她更注重詩歌的暗流;「比如河面上漂著一個塑料袋……我更在意的,是形成這些運動軌跡的『動機』,即河水有多深,有多急,下面是不是暗藏礁石,或者存在著一些超出我日常經驗的東西。」看來她就是喜歡用簡短淺白的文字寫那個塑料袋的浮動,留下無限空白去讓讀者猜測底下的種種。
熟悉了她的手段後,可以發現她寫愛情和親情也有類似的技巧:
《我喜歡你》
像童年時拔掉小鳥的羽毛
把蚯蚓一切兩半
像撕裂蝴蝶的翅膀
敲碎蝸牛的殼
像把螢火蟲
留到第二天清晨
像…像…
我就是這樣
喜歡著你
《紙船》
邊接你的電話
邊用一張單據折一隻小船
那是五歲時父親教我的
折疊的關鍵在於最後一步
從中心線的位置朝兩側拉伸
——伸到不能再伸
迅速把裡面的部分往外翻
翻出來,撐起,再調整
我總是卡在這一步
找不到轉機
我想掛斷電話
再問問我的父親
《我喜歡你》先是描述了兒童的殘忍行為,卻不帶半點批判,然後把這些行為與「喜歡」劃上等號,間接承認了自己在愛情中各種不成熟、不當的表達,卻又不透露半點歉意,半點委屈——讓塑料袋繼續輕輕飄,底下的暗湧卻已令讀者感慨萬分。《紙船》表面是談電話,實際上「我」的思緒已飛到老遠,從紙船想起童年的溫馨時光,也掛念起父親來,卻依然氣定神閑,就算真的掛斷電話打給父親,大概也只會莫各其妙地問翻船的方法,誓不談塑料袋底下的種種。
短詩的精妙在於以最少的字數激發讀者最大的想像和思考空間。路雅婷的作品雖然短小卻充滿力量,這種輕盈的詩風,不僅僅是創作形式,也是她的生活態度——輕描淡寫一句「祝你太太好」,已經比金字塔還要尖銳地矗立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