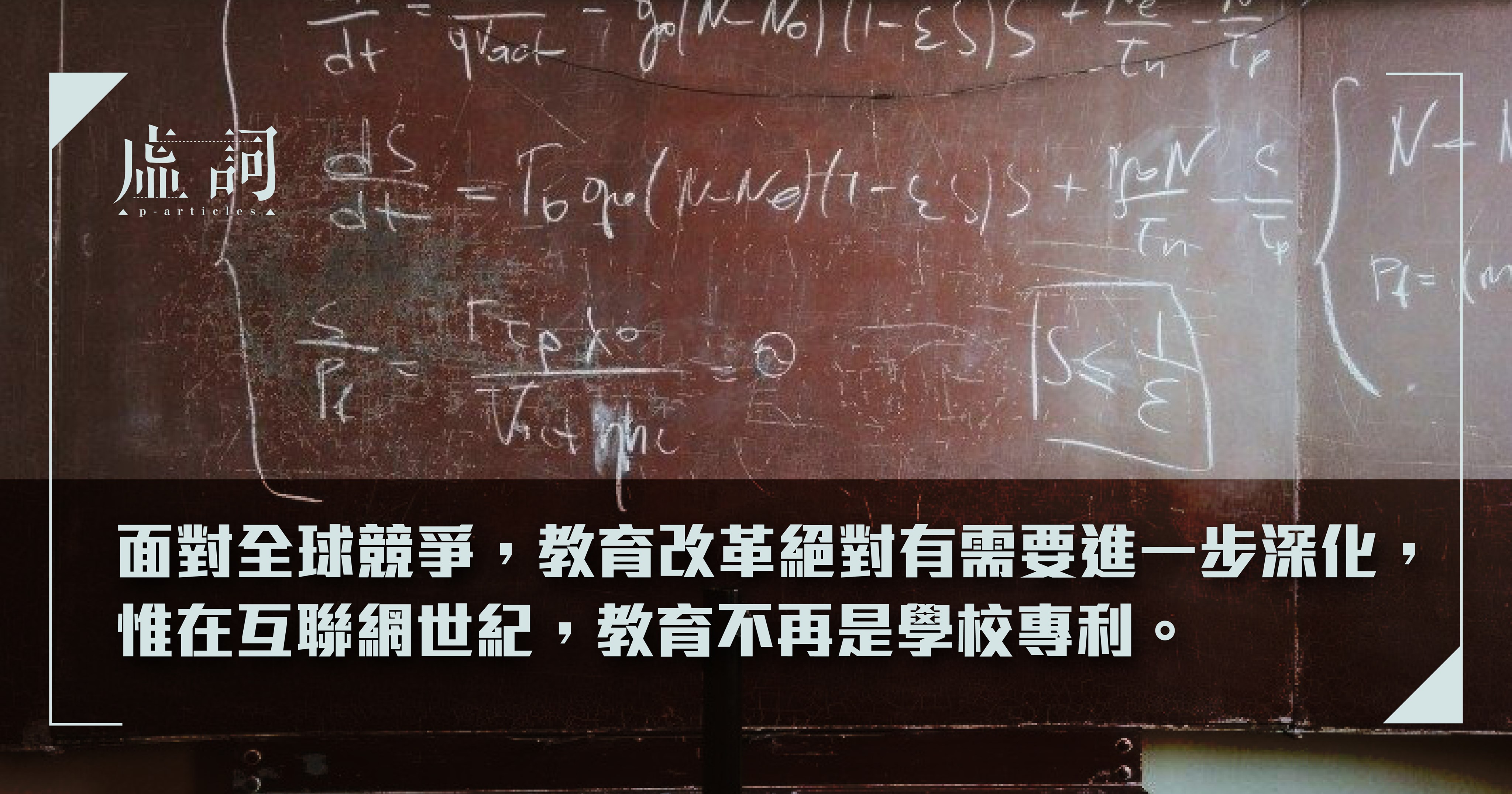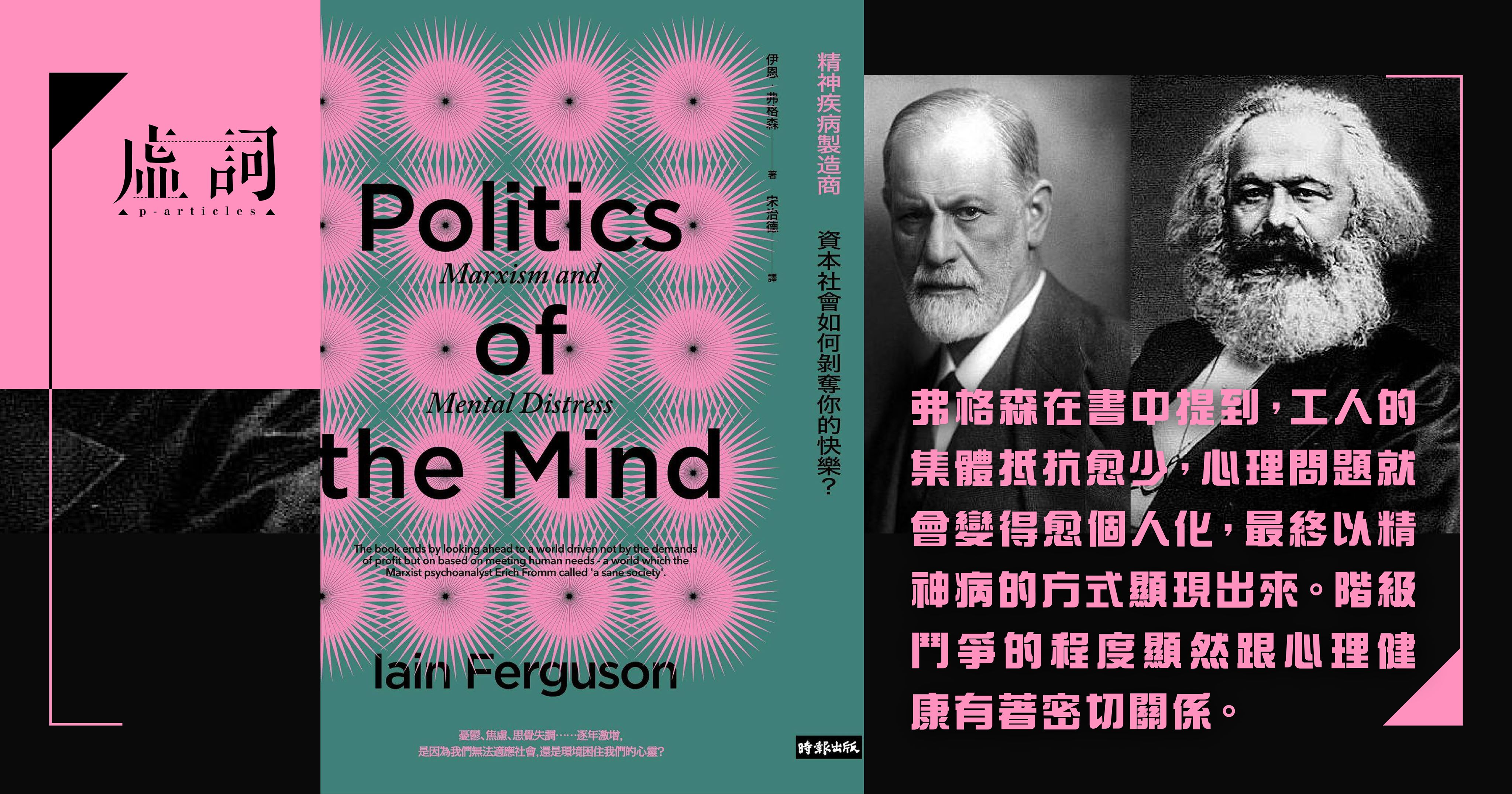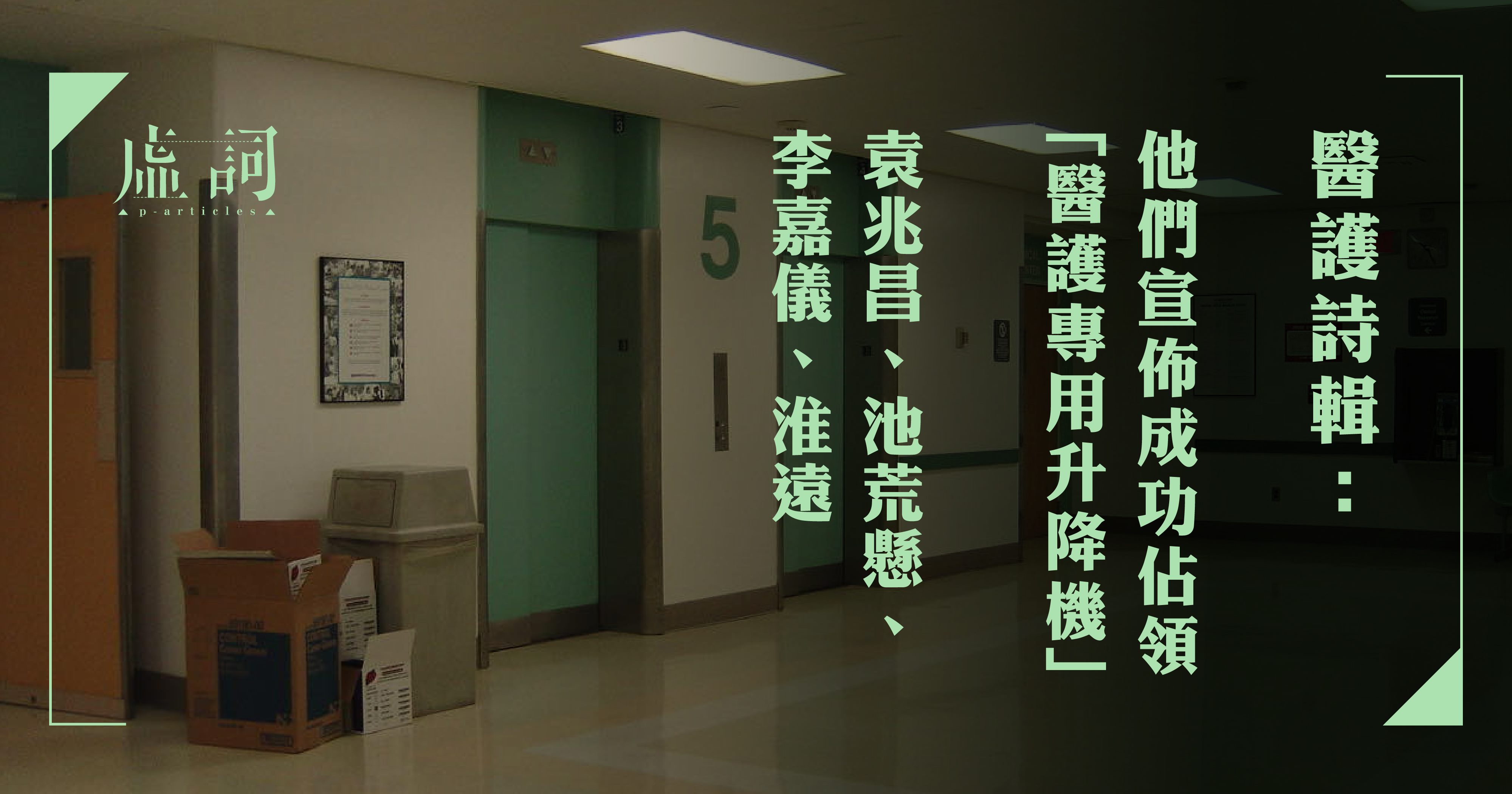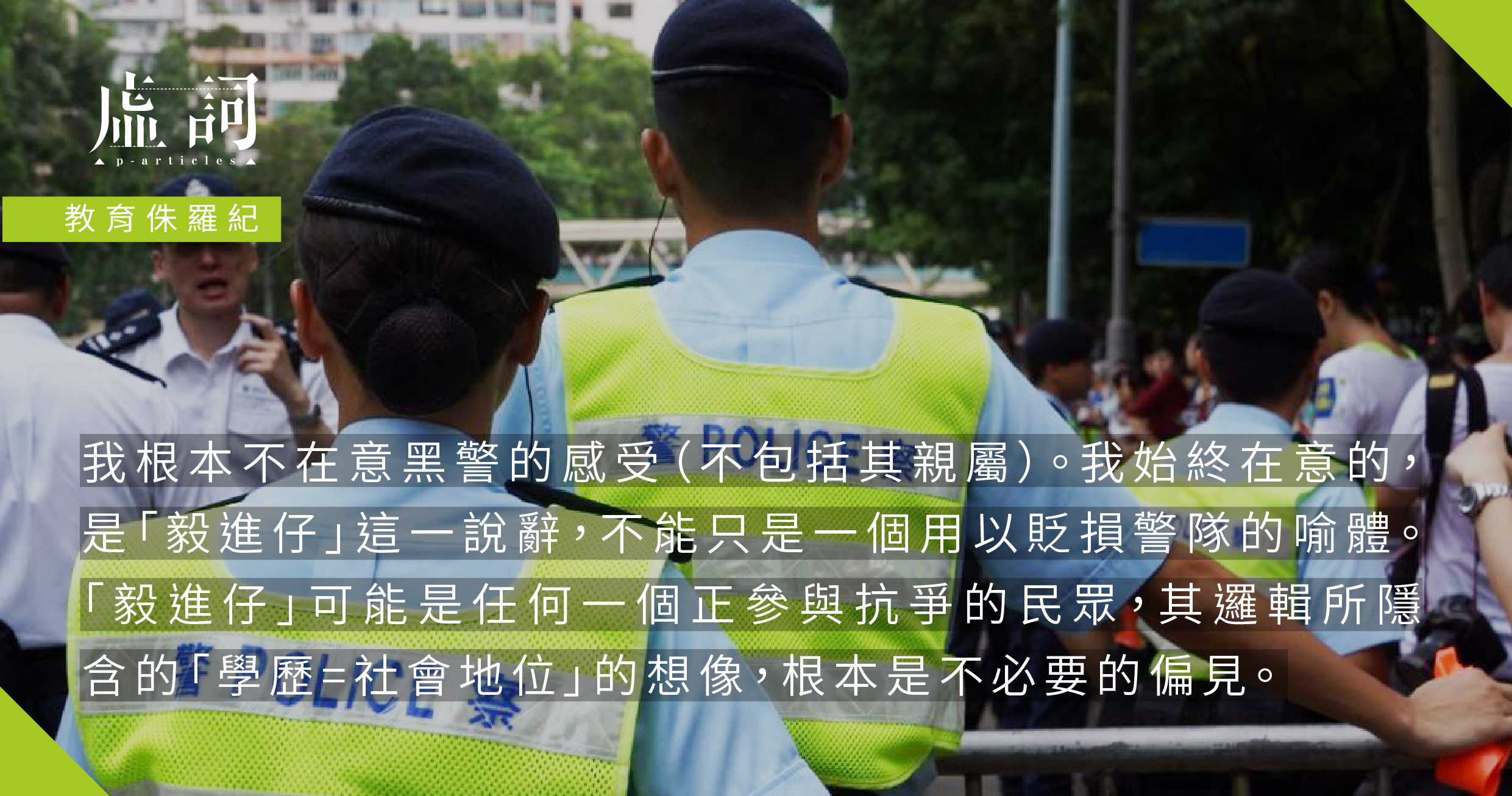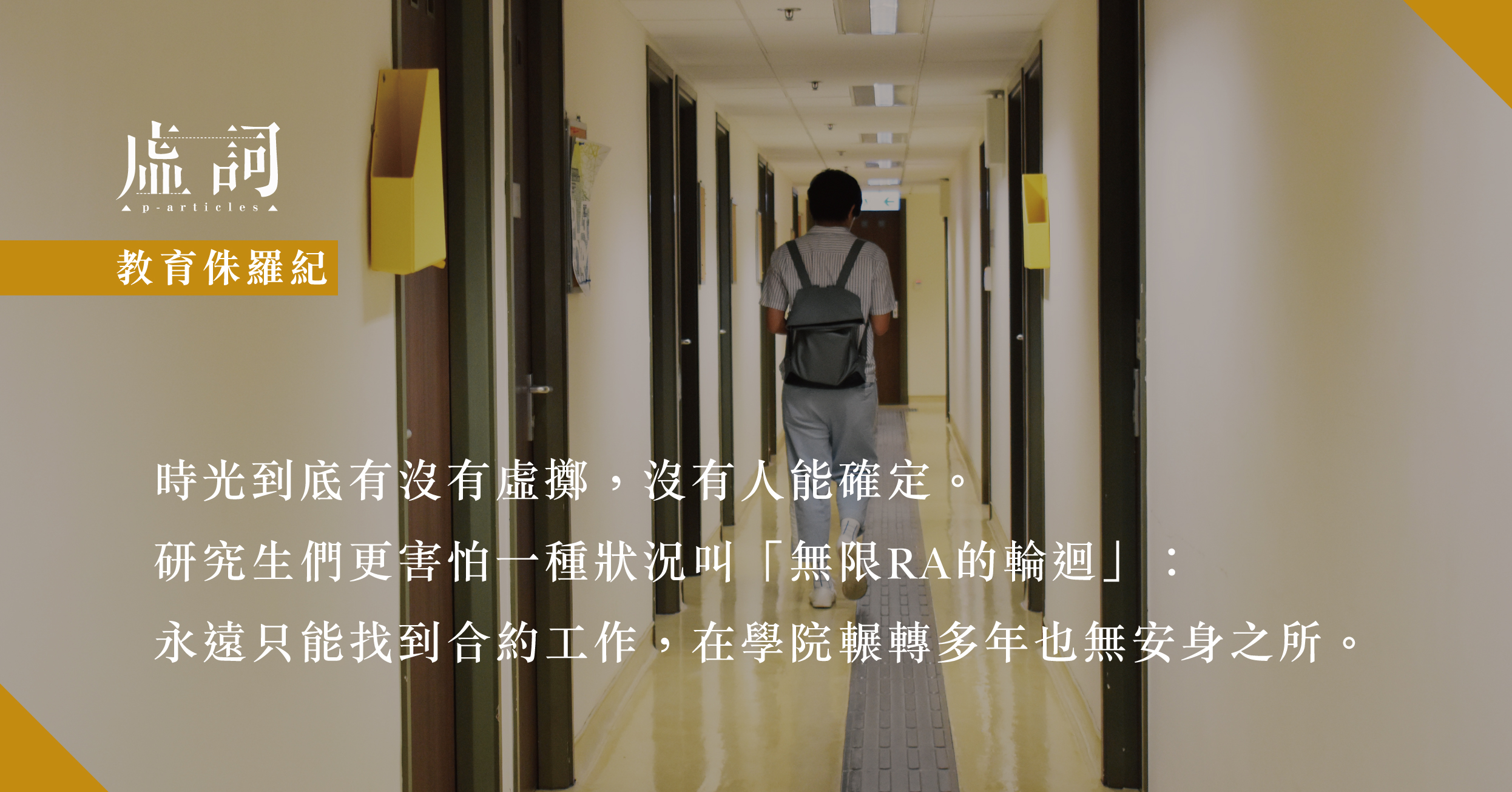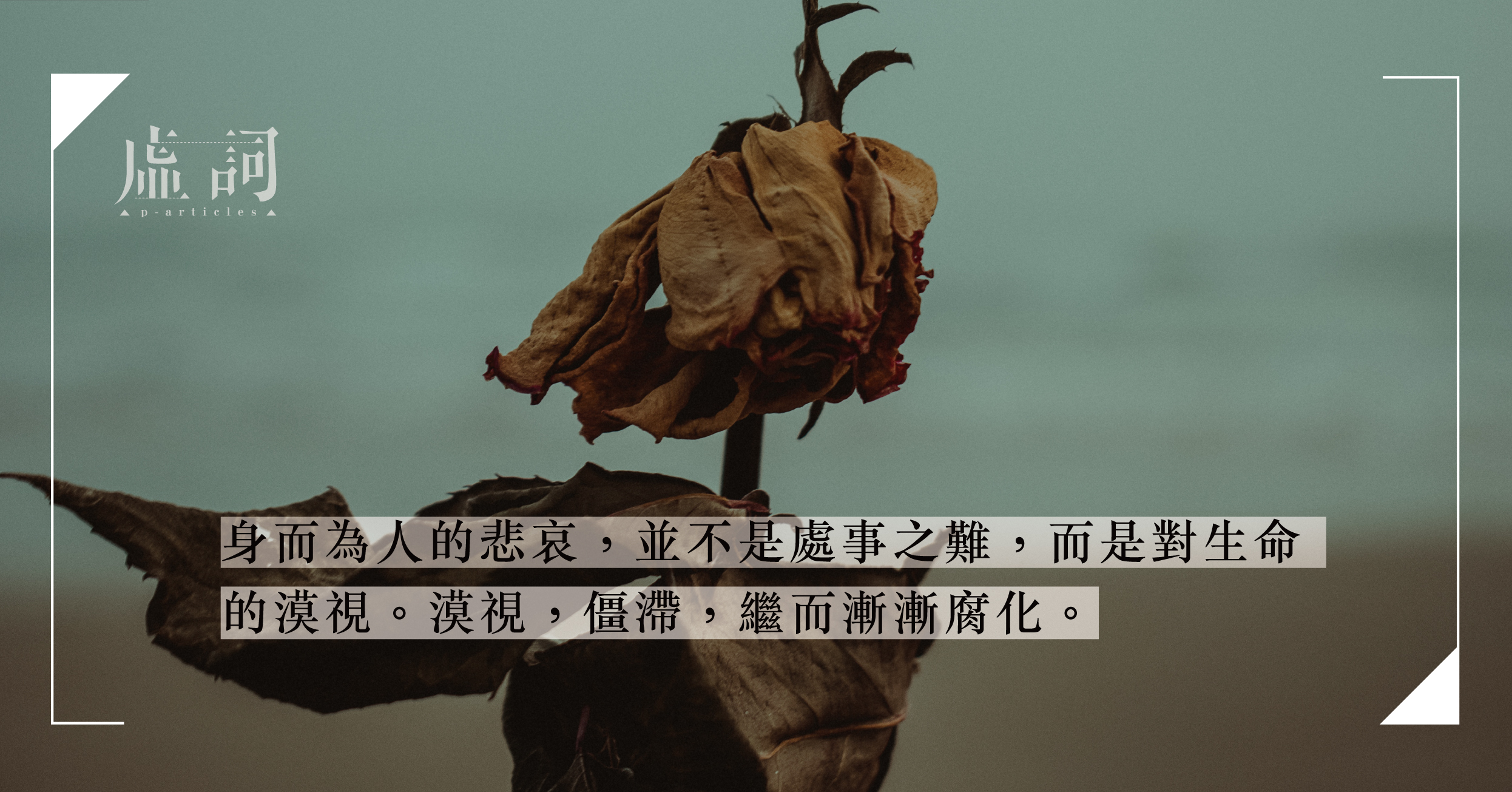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制度"

嗅嗅聞聞余光中
小說 | by 潘逸賢 | 2026-01-30
潘逸賢傳來短篇小說,書寫學生諾斯文學課堂上拒絕傳統閱讀報告形式,以玻璃密封罐捕捉雨天空氣,詮釋余光中散文〈聽聽那冷雨〉中薄荷、土腥、蚯蚓與蝸牛的生命氣息,卻遭到老師與同學的嘲諷。當這份「閱讀報告」在教室碎裂,課堂突然化為長滿植物的荒野,師生埋首泥中,諾斯則褪去人形,蛻變為一個純粹感知的鼻子。

敵意建築讓休息成為苦行 法藝術家以《The Fakir’s Rest》 批判公共空間的公平性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5-11-14
走在街上,我們或多或少都會注意到那些「一看便知坐得不舒服」的椅子,或在天橋底下的空間設置了石柱與尖刺。這些設計並非偶然,而是被稱為「敵意建築」(Hostile Architecture)的城市規劃手段。它們透過改造公共空間,意圖阻止特定活動、限制某些行為,或排斥特定群體。2003年,法國藝術家Stéphane Argillet與Gilles Paté拍攝的六分鐘實驗短片《The Fakir’s Rest》(苦行者的休憩),讓觀眾反思這種由設計所衍生的冷漠與制度性疏離。

葉姐
小說 | by 楊彩杰 | 2025-11-03
楊彩杰傳來小說,書寫葉姐作為海麗商場的清潔工,其工作是清除「人來人往」的痕跡。她對抗污穢自有一套秩序,如同她對烹飪的熱情。當外判商「順民」以轉換合約為名,騙走工友們的遣散費時,一場抗爭隨之展開。在記者會上,葉姐聽不懂組織者的「新自由主義」,也無法認同工友代表的「賣慘」。面對鏡頭,她選擇以勞動者的專業與尊嚴發聲,討回血汗錢。然而,三個月後,同樣的自願離職信再次降臨,制度的壓迫循環不息。

英國國家美術館拒政治化解讀畫作 近年藝術品解說有政治立場 你又點睇?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5-06-05
英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早前完成展品重整,沒有跟隨其他博物館的行為,拒絕在畫作解說中加入奴隸制度、殖民主義等歷史議題的字眼,強調這是為提升公眾的藝術欣賞體驗。館長Sir Gabriele Finaldi表示:「這是對館藏、畫家以及偉大歐洲傳統的一次慶祝。某程度上,這種做法略顯老派。」他強調,觀賞藝術應是一種審美體驗,雖然也具備教育與社會意義,但不應以政治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