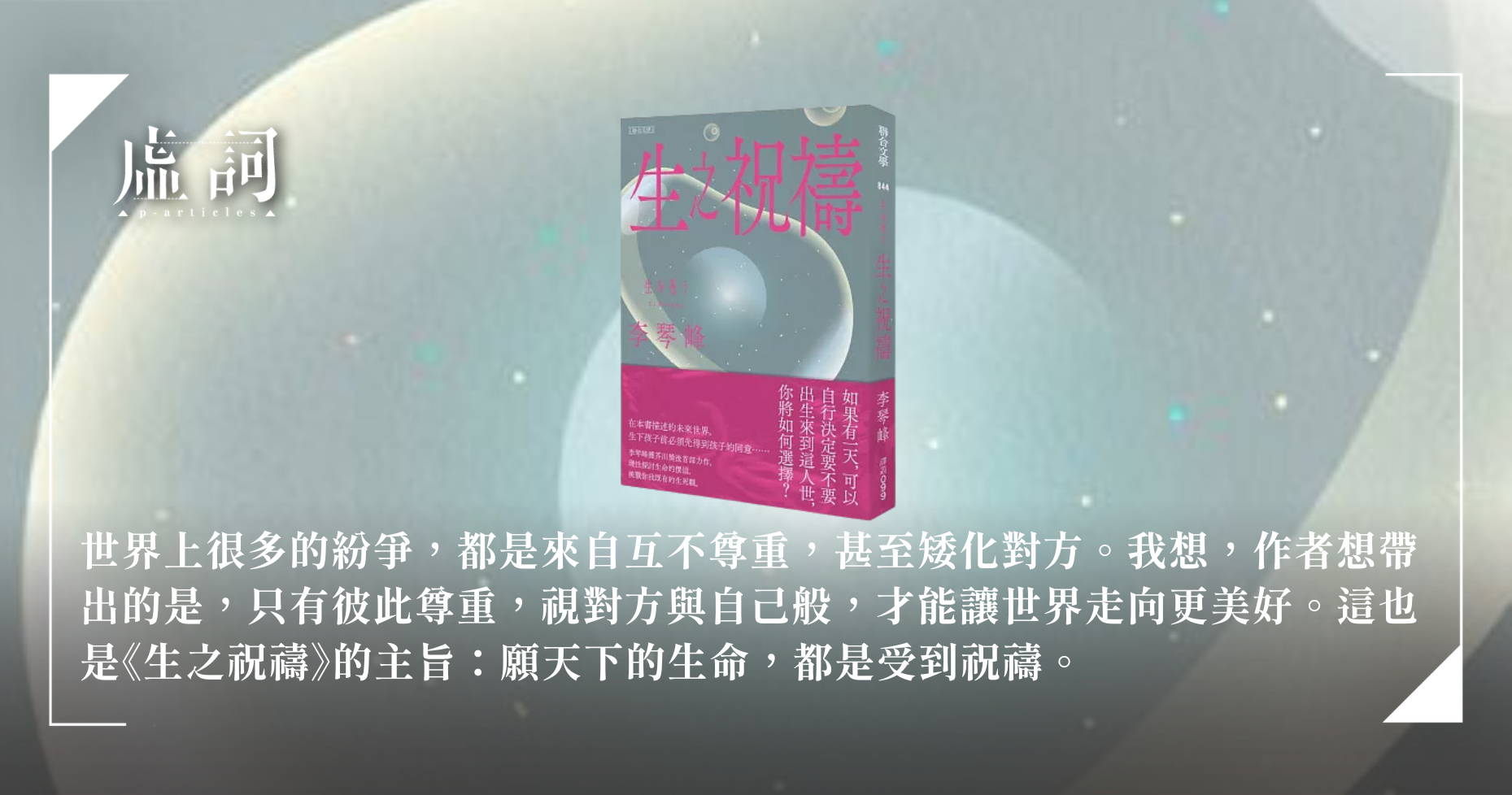彼此的尊重——從《生之祝禱》看生命的平等
書評 | by 亞德里安 | 2024-08-26
「我真希望自己沒有生下來」——李琴峰,芥川獎頒獎典禮演說
每當聽到朋友誕下新生兒,總會替她感到高興,一方面母子平安,另一方面是孩子來到世上,期盼他/她有美好的人生。不過未必每一個胎兒能順利誕下,可能是先天病證,也可能是意外懷孕。現時提出終止懷孕的決定,都是來自母親與醫生。然而,如果有一天,母腹中的胎兒能決定自己是否誕生於世時,這又是一個怎樣狀態李琴峰的《生之祝禱》,正好作為一種啟示。
李琴峰自2021年,憑《彼岸花盛開之島》得到日本文學界最高榮譽之一芥川獎後,她的作品開始受華文世界關注。然而,因為她必為自己的作品親自翻譯,所以這本華文翻譯作品《生之祝禱》比日文版遲了近3年才能面世。
《生之祝禱》這書名,已表達這小說的主題是有關「生」。故事的時代背景,人類已經可以自由決定什麼時候死亡,安樂死再不需要到某些國家進行。每個國家,包括日本,已有法例定明合法。與此同時,科學家也研發出一系列檢測,並將這檢測結果「告知」胎兒,讓他/她作最後決定。當胎兒接收這些資訊後並決定誕生,孕婦才可以誕下胎兒,政府並會發出「合意出生公正證書」;然而如果胎兒拒絕,孕婦需要立即安排「出生取消手術」,即墮胎。這制度為「合意出生制度」。
主角彩華是一位在這「合意出生制度」下誕生的女子,而與她一同組織家庭的同性太太佳織,則是在還未有這制度下出生。彩華與佳織因著醫學科技發展而懷有她們的孩子,正當她們期待孩子來臨,很久沒有跟彩華聯絡的姐姐彩芽突然出現,並跟彩華講出她因這「合意出生制度」而沒法誕下兒子的傷痛,更指向這是政府的陰謀,以控制人口、血統、智商等,著彩華不要去醫院接受最後檢查。因為彩華在這制度下誕生,深信這制度是尊重胎兒意願,而不理會姐姐勸告。然而當她在最後檢查時,得悉肚中胎兒拒絕出世而無法接受這結果。就在個人意願與胎兒決定的天人交戰下,她要從中為自己及胎兒作最後抉擇。
以生、死兩道作題材的小說,在中外很普遍。如堀辰雄的《風起》,看著所愛的人步向死亡的無力感;野坂昭和的《螢火蟲之墓》,渴望生存卻無法阻止死亡臨近。而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更是作者透過死前的控訴,對生之渴望。而日本漫畫中,也有這樣的題材,如《死亡預告》,它描述國家為了令國民重新認識生命的意義,設定1000分之一人中,會被植入藥物,這藥物會在18-24歲這階段發作而死。在藥物發作前24小時,這位年青人會收到「逝紙」通知他們將要面對死亡。
至於作者,她並非第一次書寫生死議題。首部作品《獨舞》,也包含「死亡」:主角因為某些原因離開台灣移居日本,改名換姓,以此契機「了結」前半生。這次她書寫「誕生」,是緣於她對於出生一直存著懷疑。她在中學期間面對的種種困難,讓她覺得自己不應該出世(頁239)。所以作者一直存有一種想法,如果胎兒能夠決定自己是否願意出生,那往後日子會否活得更好?所以小說有這樣的設定——醫生會為每對父母(不論是異性還是同性)作各項評估,項目除了一些現在產檢已有的如性別、先天疾病外,還有一些如胎兒智商、容貌評價;胎兒雙親的社會地位、生活習慣、價值觀,甚至外部環境,即生存難易度指數,也能化成數字,綜合得出胎兒的生存難易度,及胎兒同意出生機率。
胎兒是否視為人,一直沒有定案。從物理角度來說,人是始於出生,終於死亡。胎兒並未離開母胎,所以不能算為人。既不視為人,所以胎兒是沒有人權。現在所有的「權利」只是靠法律保障。按照香港法例,如果一位母親要停止懷孕,需要在24周前進行,否則會被視為殺胎,需要負刑責。除非有兩位醫生「真誠達成意見,認為為了挽救孕婦的性命,必須終止該妊娠」。即便如此,也不會視他/她為「人」。何況,決定去留,也是由母親及醫生決定,胎兒只是接受現實。然而,在小說裡的胎兒,已得到與人同等的權利,即生(誕生)死(不誕生)權。
既然胎兒的人權是小說的重心,作者除了著墨於制度設定外,也著墨這制度如何影響人生。彩華的伴侶及她的姐姐因為在沒「合意出生制度」下誕生的嬰孩,而她們的人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彩芽的父母對彩芽溺愛,源自於對她的愧疚,所以每當彩芽與彩華發生衝突,父母都會站在彩芽那邊,使得彩華一直都不喜歡姐姐。另一方面,姐姐因為沒在「合意出生制度」下誕生而感到自卑。而彩華的伴侶佳織,則因為父親反對同性戀,使她恨惡自己為何生於世上(這跟作者的經歷十分相似)。
我們的社會總以數字作指標,大至社會性如國內生產總值(GDP)、出口數字、失業率;小至個人如血壓、心跳、膽固醇,甚至生死交界線的維生指數。透過數字,我們可以知道如何應對。至於決定如何應對,則需要知識作基礎。然而,胎兒是否能理解經過一系列檢查而得出來的數字的意義?他/她是否有足夠的知識,以決定自己是否誕生於世?這樣的制度,是否有漏洞,甚至過於兒戲?
故此,小說中對「合意出生制度」深信無誤的彩華,聽到姐姐彩芽對這制度作出質疑時,她是無法理解,直到她面對著跟姐姐同樣情況之時,才知悉制度的問題。而三位母親在最後檢查的感受,正好成了一個對照:母親「生產」的權利,是否被胎兒決定誕生的權利所蓋過?除了上文所述胎兒是否可以憑一個數字決定誕生與否外,當胎兒決定拒絕誕生,母親有沒有其他事可以做?答案是沒有。母親無法得悉胎兒為何作這決定,更枉論母親遊說胎兒改變這想法。母親畢竟是與胎兒最親密的人,十月懷胎,每天感受著胎兒的跳動、踢肚。直到胎兒快到預產期才得悉他/她拒絕誕生這事實,這是活生生地、冷冰冰地將母親與胎兒的情感徹底刪除。一刻的決定,無情地將十個月的辛勞抹去。小說中,姐姐彩芽是這樣形容「取消懷孕」:
「『取消』說得輕巧,那其實就是墮胎。當我躺在冰冷的手術台上時,我看到自己鼓脹的腹部,像是一座小小的山丘,我那珍貴的寶物就沉睡在那座山丘裡。一個醫生走來,把連接在我手臂上的針筒按了下去,世界就沉到了黑暗之中。等我下次睜開眼時,那座山丘已經不見了,就像鼓脹的氣球,轉瞬間便砰的一聲,消失得無影無蹤。明明在我閉上眼睛以前,他還在我的眼前,從我的體內賦予我的身心靈巨大的飽足感,現在卻突然消失了,留在我體內的只有無盡的空虛。彩華,妳能相信嗎?從閉上眼睛到睜開眼,就在字面意義的一瞬之間,陽翔就連理解自身疾病的機會,都永永遠遠地失去了。」(頁130、131)
字裡行間彷似控訴制度,但作者卻描寫姐姐在彩華的眼中是「披著柔軟的暖光」(頁131)。有趣的事,暖光、陽光,總是在暴風雨前出現。它們本給予一種愉悅、明朗、一切將會是美好的前景,好比彩華與佳織一起去做最後一次檢查時的情景:「陽光從窗戶照了進來,投射在木質地板上⋯⋯那景象有種神聖感,彷彿在預告著新生命即將從天上降臨人世。」(頁148)。然而這樣美好的時光,跟及後她們得悉胎兒拒絕誕生這晴天霹靂的消息,成了反差。
李琴峰的作品總有涉及性別/父權議題,不論是《獨舞》、《星月夜》或者《北極星灑落之夜》,主角們大都是同性戀人士。至於得獎作品《彼岸花盛開之島》,它所討論的是「非父權」。而《生之祝禱》雖是一個婚姻平權的時代,即便社會接受同性婚姻,但父權仍是充斥著。小說中的父親,不論彩華的前上司、同事的丈夫,在胎兒檢測事情上,都是缺席。而前姐夫雖在取消懷孕一事上受打擊,但之後卻不斷催促彩芽再次懷孕,而忽略彩芽失去胎兒的傷痛。作者一如以往且毫不留情地批判這些父權思想,懷孕的事上的確與他們沒關係,不論肉體上還是心靈上,都是一片空白。但他們的不理解、冷漠,甚至將責任推到女性身上,在作者眼中是無法原諒。
這小說既然是探討如果胎兒有決定誕生權利,那他/她的人生會否過得好這議題,那作者自己有定論嗎?她在後記已經清楚表達,她不會,也無法回答這問題,她只想拋出議題讓讀者思考。如果將胎兒視為「人」,他/她的抉擇權自然是要保護。但,胎兒的人生是否順境,是否可以透過那些數字表達出來,仍是一個問號。如果從「贏在起跑線」的角度切入,那些同意誕生的嬰孩,因著他們抱著對未來是美好的正面想法而積極生活。但是這也不代表往後是一帆風順,沒有挫折,沒有痛楚。何況,當他們誕下來,他們會否後悔他們的決定?有可能,所以他們可能選擇安樂死。至於那些未有「合意出生制度」下誕生的人,其實也未必一定過著悲慘人生,好像佳織,雖然她在年青時期受盡痛苦,但之後與所愛組織家庭,可謂苦盡甘來。正因為人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有平靜也有風浪,才能從中找到其生命的意義。
作者雖說她沒有答案,但從小說結尾可以窺視她的想法。彩華經過傷痛五階段——即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後,她最後接受胎兒的決定,取消懷孕。佳織雖然開首反對彩華違背胎兒決定,但她明白彩華對胎兒的愛,而表達支持彩華誕下胎兒的決定,願意一同撫養,更不介意面對懲罰。只是彩華覺得,尊重胎兒的決定才是最重要。彩華很清楚表達她的願望,我也相信這是作者的期盼。那就是為胎兒「獻上的不是詛咒,而是祝禱」(頁233)。
世界上很多的紛爭,都是來自互不尊重,甚至矮化對方。我想,作者想帶出的是,只有彼此尊重,視對方與自己般,才能讓世界走向更美好。這也是《生之祝禱》的主旨:願天下的生命,都是受到祝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