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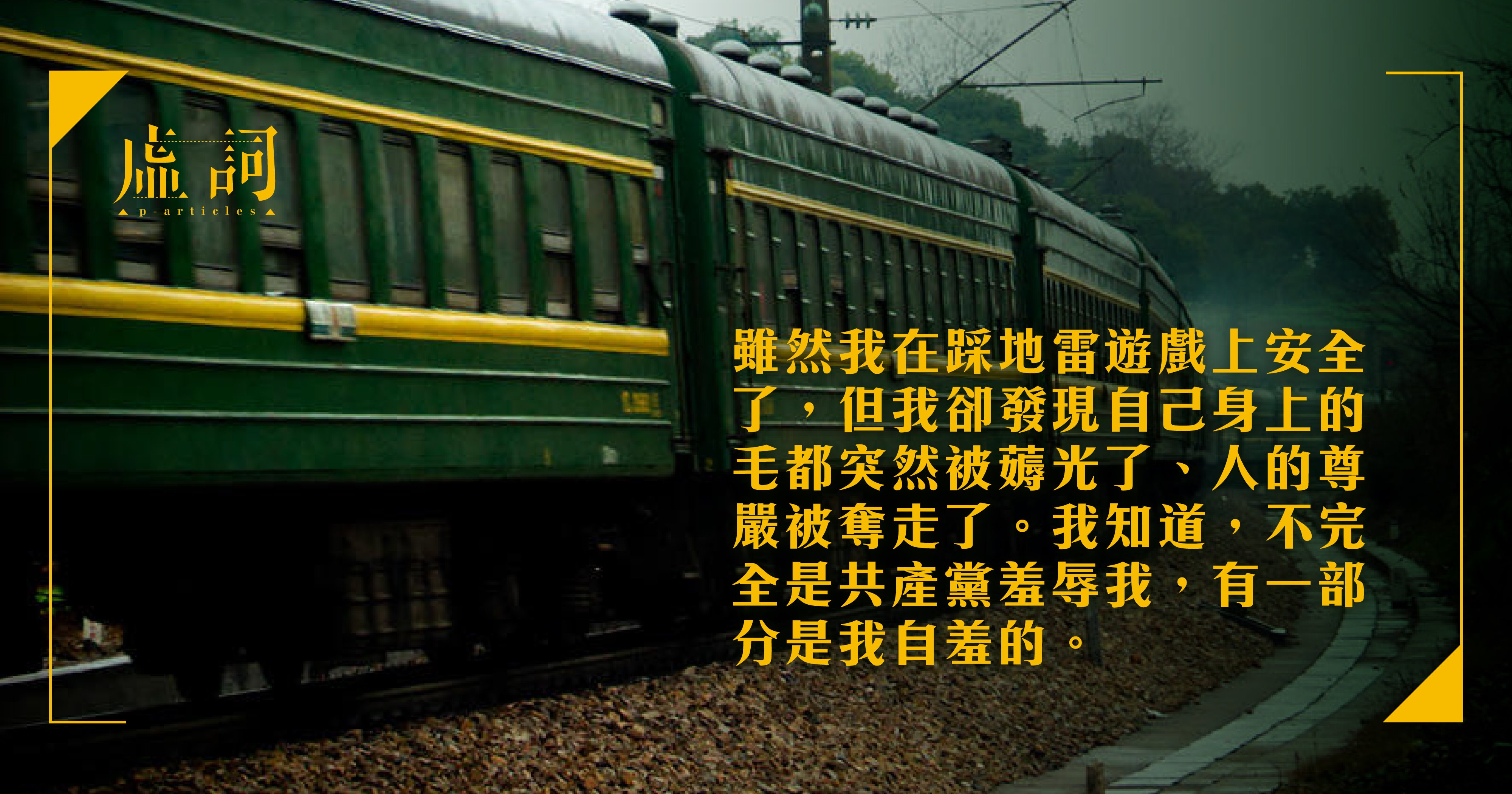
82032959_625064591633081_3124920416754204672_n.jpg
中國火車由十個墨綠色的鐵匣子串起來組成的,外型老套。鐵匣子早已發銹,霉出銅色的斑。我買了硬臥車票,登上了其中一架中國火車。
這邊的空氣污染很嚴重,但即使在室内也是烏煙瘴氣。車廂裡洋溢著一陣臭味,是令我誤以為有小狗住的臭味。小餐桌上還留有上一手乘客的長髮,還有幾個看似是衣服掉下來的灰毛球,我心裡難過,覺得衛生很差。
一個分格共有六張床,活像香港的籠屋。對面床的姨姨首先撩我講話,問我要去哪裡,就這樣打開話題。
明明是冬天,但車廂卻悶熱得很,我只脫剩一件短袖T恤,他們應該沒開冷氣,就算有開也是開得很小,這一切都是多麼的使人窒息。
洗手間也是臭得沒人話,雖然在鏡前掛了一個檸檬、一個橙癖味,但它們也似乎被臭到臉容扭曲了,皺皮皮的擠成一團,更莫講可以散發果香了。我入洗手間時都要閉氣,忍不住了,只好用口呼吸,雖然我知道用鼻或用口吸的毒臭也沒分別。
我不願睡,便坐在硬床上,盯著窗外慢慢飛起的鄉村景色發呆。偶爾,對面床的姨姨睡飽了,就會爬起身,興高采烈地講她自己的經歷——來自農村,長大後到廣州一間造牛仔褲的工廠打工,成了管理層......
我肚子餓時,就光顧他們火車上的熱飯。我明知道髒、明知道味道不好,但我都光顧他們。
揭開飯蓋時,蒼蠅也來湊熱鬧,但我卻有點失望。我從沒見過五毫子大小的雲耳......從沒見過......我用木筷子夾起它,仔細地檢查了很久,到底它是被切細成這樣還是它本來就是這麼細小。而鹹蛋吃起來口感很像軟柔的發泡膠,我覺得自己在嘴嚼著一種名叫謊言的食物,可是,相比起其他東西,鹹蛋已是比較真實。
我都沒有一頓飯是吃得安心的。唯一較好過的,是吃肉時吃到很小塊的骨頭,我好高興,有骨頭即是那肉是真的,不是麵粉或合成物。
我和對面床的姨姨聊著聊著,她忽然就問起我:「你從哪裡來?」雖然早知道會問到這,我卻還是下意識地警惕起來,裝作沒聽懂說:「嗯。」她追問我:「不是哪,我問你是哪裡的人哪?」
逃避不了。我尷尬地笑說:「我是香港人。」
談到香港,我像行走在地雷上,一不小心就會把自己炸死掉。
她主動挑起我最不想談的東西,問我:「你們為甚麼會這樣子?」......真的很有衝動回答說:「追求民主和自由啊」但我不敢。就算她是個開通的人,始終隔牆有耳。
然而,要我罵示威者,我倒又做不到。於是我尷尬地答了一句:「不知道。」姨姨大概也不是聰明的人,聽不出這三個字背後的無奈,就開始了馬拉松式的評論——罵我們不文明、不應該反對國家。
他們不曉得甚麼是極權,儘管他們身在其中。而我,明明是渴望自由的人,卻不敢講、不敢認、噤若寒蟬......我感到徹底的失望。
雖然我在踩地雷遊戲上安全了,但我卻發現自己身上的毛都突然被薅光了、人的尊嚴被奪走了。我知道,不完全是共產黨羞辱我,有一部分是我自羞的。
從深圳到貴州,要搭廿幾個小時,加上天氣乾燥,自帶的食水被喝光了。我很不情願地走到車卡盡頭的熱水機,它充滿半透明的、仿佛存在又仿佛不存在的污漬。
但我的雙眼見不到,見不到。雙手便隨即擰開樽蓋,急急地讓滾燙燙的熱水溜走我的水樽裡,濃霧隨著圓柱體的邊緣冒起。我回到自己的硬床上,盯著這樽水。
我深深體會地,身處這裡,是一種「不得不相信」的感覺。你現在要喝他們的水了,你只能告訴自己這是「正常的水」。你怎能一邊說這水有問題、這水喝了肚子痛但又一邊張口喝它呢?所以就只能相信啊,不然還能怎樣。
姨姨提到自己年輕時也到處旅行,她說:「我還去過北京,看過天安門。」
這教我直冒汗了。真是動魄驚心呢!她怎能把「天安門」三個字說得那麼從容?她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啊?對不起,講起天安門,我只想到八九民運!我猛地喚自己鎮定點、鎮定點,最後回應了一句廢話:「那不就挺好」。
原來人啞的時候,不是真的啞了,而是會說廢話。
入黑之後,火車就關燈了,只剩一些暗暗的光在腳踝位置,旅客們都睡著了。突然有電筒的光在照來照去,還照到我的臉,我驚醒起來,内心深處是一層恐懼。那電筒的光讓我想起在理工大學的泳池外,也試過被人照田雞,並使我一見到這些電筒的光就生怕自己做錯甚麼被發現似的。
但我明明甚麼都沒做錯。
原來是車廂職員提醒啊姨準備下火車了,要換票。
我盡最後的友善和禮貌,特意在睡夢中爬起身,陪啊姨最後聊幾句。她也是好心的人,叮囑我路上小心,還教我不要那麼誠實——「不要說你一個人來旅行,說去探男朋友,或者親戚。千萬不要說你來自香港。」
我笑問一句:「那我該說我來自哪裡呢?」看似問她,其實我是問自己。
「隨便一個省就可以了,重慶啊、湖北啊、廣州啊......」我知道她的意思。棄掉原來不潔的身份,重新做人,改過自新......這正是新疆教育營的套路,想不到這思想在廣大民間也實踐起來。
姨姨下車了,只剩我繼續我的火車旅程。我呆滯地盯著車廂,只見附近這裡大部分人都睡了,氣氛格外死寂。我覺得自己是一頭在木欄裡的蠢豬,有水可喝、有渣滓可吃、有床可睡......我是這樣被豢養著。
我無知地張望四周,突然覺得自己讀過很多書,仍懵懂不知事,在巨爪之下一切是那麼茫然。
我拿起手機,見到朋友問我「有無俾人斬手斬腳呀?」、「個肝仲喺唔喺度呀?」、「俾人賣去山區做老婆未呀?」在我們的想像中,中國就是那麼恐怖。我默默地回了一句:「平安」,之後就刪掉對話紀錄。
一個人在中國平安與否,與治安無太大關係,反而是政治、思想方面。而平安活著的秘訣也很簡單,就是在它動手之前,你首先自剃毛髮、成為一個乾淨的人,學會自侮。
見吧,我刪掉對話紀錄,我做到了。
火車駛在農村旁邊,那裡燈火不多,望出窗外已無任何風景可言。我百無聊賴,也迷迷糊糊地睡去。
這趟火車是慘情的、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