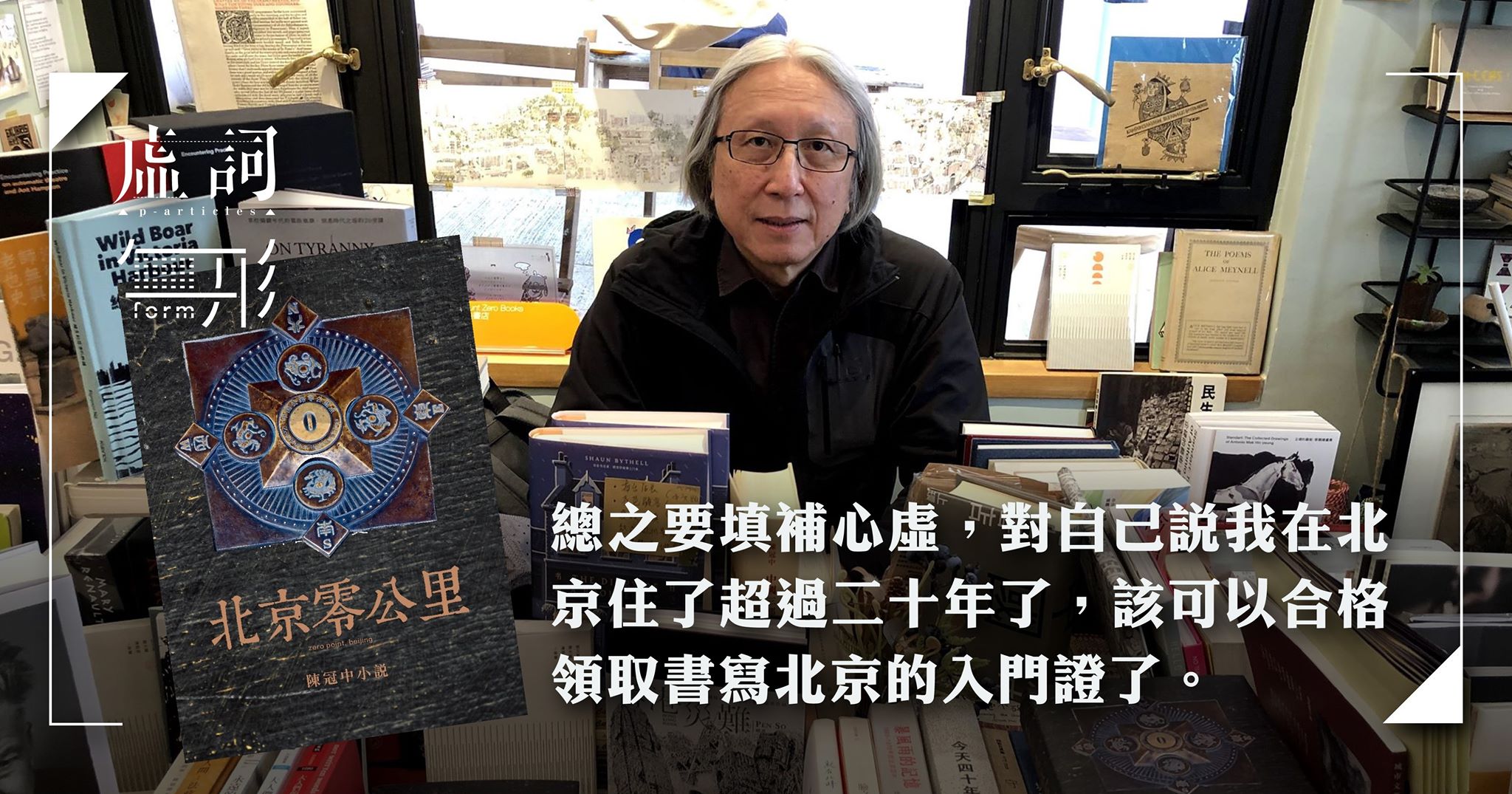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讀L"

初始的詩——讀Louise Glück〈退隱的光〉
其他 | by 任弘毅 | 2023-12-07
任弘毅未及拜讀葛綠珂之詩,葛綠珂便因癌症逝世。近日他借閱《野鳶尾》,被廖偉棠「詠物的內涵是詠神」的評論一言驚醒,當他再讀〈退隱的光〉時,發現葛綠珂演繹著文學的神話,甚至將自己活成了神話。這令他聯想到臧隸的〈詩已將世界分為兩半〉,當中無窮遞歸的數列若要套用在詩歌上,葛綠珂或會說:詩就是那通項公式,那不斷被傳頌,甚至指向自身的神話。

【無形・讀L】偏心女同志小說書單
書評 | by 林三維 | 2020-07-09
以女同志、性別流動為主體的小說,盡量呈現不同的女同志面貌,既有純文學、愛情、也有犯罪、懸疑,脫下標籤、類型後,大抵都是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