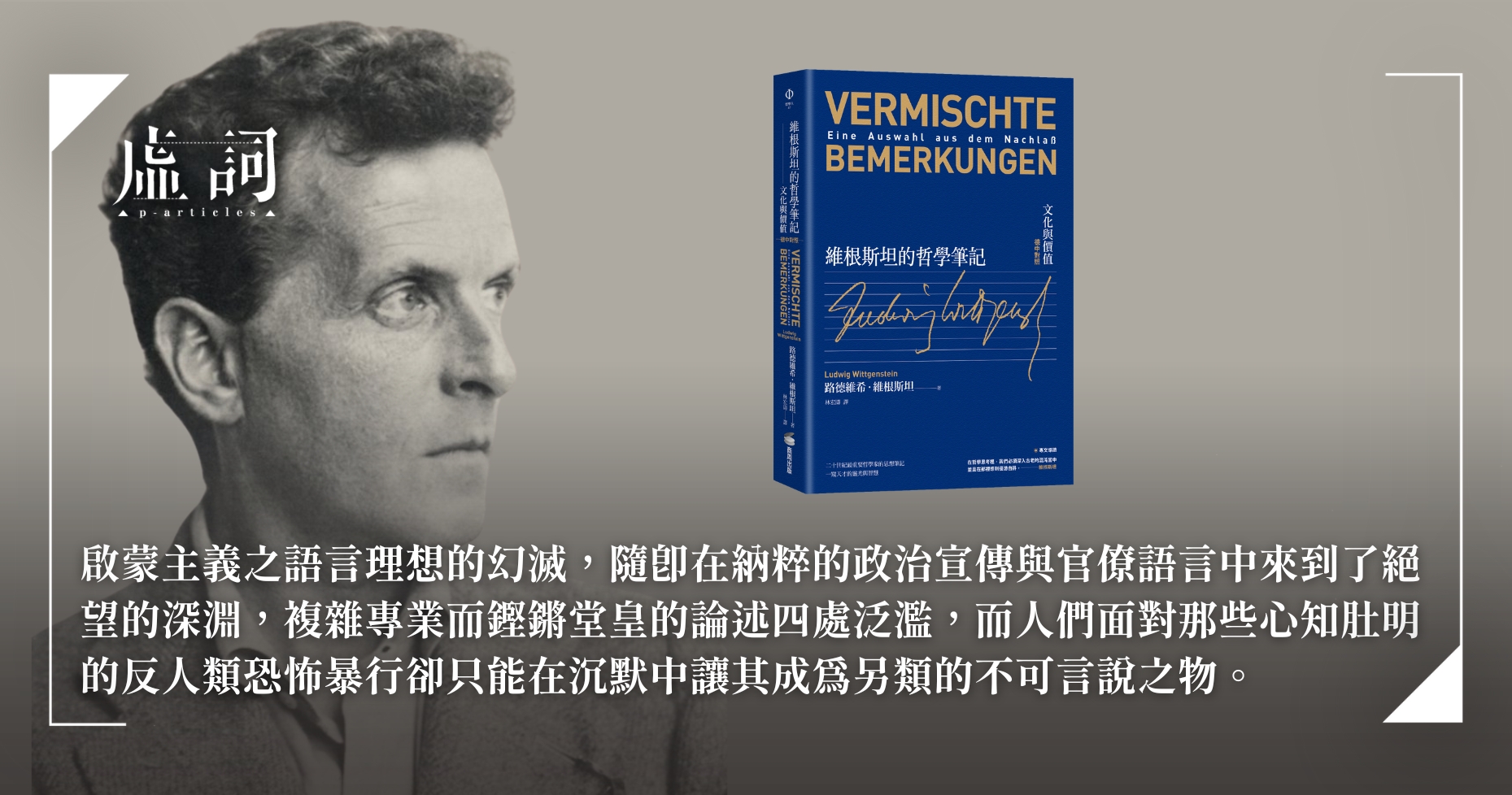《維根斯坦的哲學筆記》導讀——寫給離散在世界角落之人的筆記
書序 | by 黃哲翰 | 2025-01-13
「不能表述的事物(我覺得是一種奧祕而不可言喻的事物)或許就是我可以表述的事物所擁有的意義的背景。 」
維根斯坦一生的哲學旨趣在於探問作為真理之工具的語言與真理之間的關係。對維根斯坦而言,真理是整全而語言是片段的,儘管我們不得不藉助語言,但真理本身卻是不可被言說的。因而哲學就是一種對不可言說者進行言說(更確切而言是:避免進行言說)的嘗試,它注定是要來回修改、結結巴巴的(正如維根斯坦本人有口吃)。
這種來回結巴的思想特徵,恰恰表現在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與《哲學研究》這前後兩部代表著作的顛倒反覆上。為了面對那不可言說的、整全的真理,維根斯坦所做出的言說先後為邏輯實證論與現象學(這兩個幾乎互斥的思潮)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而這又成為學界長期以來討論的課題:維根斯坦前後期的思想究竟是一種轉折、還是一種延續?
不過,在這種學院哲學史式的探討之外,一般人或許更好奇的是:對於這位一生抑鬱、反覆決定進入又離開哲學界的天才哲學家而言,那不可言說的真理到底是什麼?而他如此執著於語言、執著於不可言說者的理由究竟是什麼?
上述問題在《邏輯哲學論》與《哲學研究》中都無法得到解答。然而,這部由維根斯坦劍橋大學教席的後繼者喬治.亨里克.馮.萊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所編纂之《維根斯坦的哲學筆記》,或許可以讓我們找到不少線索。在這部筆記集中,維根斯坦透過其零碎而私密的語言,方才向我們透露了他所面對的、所要處理的「世界」具體是什麼—那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歐洲文明處境:古典音樂與藝術的衰落、不斷進步卻同時也自我作繭般不斷複雜化的科學、大眾社會的出現與庸俗化、法西斯與社會主義席捲歐陸,乃至於始終糾纏著他的生活世界的反猶太狂潮。
事實上,正是猶太人的身份讓維根斯坦從上述歐洲文明的處境出發,走到了《邏輯哲學論》與《哲學研究》中的語言批判,以及對不可言說之真理的沉思。十九世紀歐洲各地的猶太社群曾力行同化運動,欲透過接受高等教育與努力精通主流社群的語言(例如德語、法語)融入當地並藉此抬升地位。為此,猶太人大力擁抱啟蒙傳統的理想,樂觀地相信語言的效力是普世的、科學的,而所有人都能藉助語言來溝通與共存。
此種啟蒙的語言理念隨即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遭遇了嚴重的挫敗,迎接猶太人追求同化之夢想的反而是愈加白熱化的反猶主義。同時,歐洲各地在快速工業化的背景下出現的階級、文化、政治衝突與狂熱的民族主義,也順勢將猶太社群當作替罪羔羊。尤其是蔑視啟蒙普世主義的民族狂熱者,更是把擁抱啟蒙理想的猶太社群視為社會毒瘤—維根斯坦成長的故鄉維也納,就正是十九世紀末反猶主義的重鎮(它也弔詭地同時是納粹反猶與猶太錫安主義的起源地)。
「我們和語言作戰。我們陷入和語言的戰爭中。」
作為「世紀末」(Fin de siècle)世代的文化人,維根斯坦所經歷的是一場語言被政治狂熱所腐化的災難:偏見與極端意識型態披上了科學與邏輯的外衣,讓言說論述在理性的假象下頓失客觀的依歸;而身為猶太人,維根斯坦更是處處能感受到主流大眾訴諸文明教養之概念論述的另一面:那實際從事歧視與排斥的言說行動。啟蒙主義之語言理想的幻滅,隨即在納粹的政治宣傳與官僚語言中來到了絕望的深淵,複雜專業而鏗鏘堂皇的論述四處泛濫,而人們面對那些心知肚明的反人類恐怖暴行卻只能在沉默中讓其成為另類的不可言說之物。
但維根斯坦並非鄂蘭(Hannah Arendt),他並沒有徑自去分析這場語言災難的起源,而是憂鬱地與他的世界隔離,忐忑地去洞察西方文明的境況。於是在他的筆記中,我們宛如讀到一個正在躊躇作詩的維根斯坦,他談布拉姆斯和孟德爾頌的音樂、談佛洛依德對夢的解析、談神性與善、談《福音書》、談悲劇、談科學發明、談哲學與語言—透過私密而隱晦的方式,他用自身的生命經驗與哲學思索,將上述文明境況的面向彼此連結、譜成斷簡般的詩曲。正如他寫道:
「『整個痛苦的世界都在這些文字裡。』……語詞就像橡實一樣,從它裡面可以長出一株橡樹。」
我們或許永遠都無法理解維根斯坦的這些筆記私語,因為對他而言,語言就是一個人的生活世界所譜寫出的詩曲(正如他的自我形容:「我的原創性是一種屬於土壤的原創性,而不是屬於種子的。」)。從某方面來說,維根斯坦的文字(或許也包含《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只是寫給一小圈子的人的……他們是我的文化圈,就像我的祖國的同胞。」
或許只有處於「世紀末」歇斯底里的歐洲文明、處於語言成為「世界毀滅的試驗場」的德語世界,只有身為猶太人的思索者、同時又是某種神性之善的探問者,才能理解維根斯坦這些筆記、乃至於其哲學言說背後的那不可言說者。
正如維根斯坦寫道,他的這些言說,「其實是寫給離散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