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別教出混蛋》:科學雞湯一碗四百八
書評 | by 曾友俞 | 2024-08-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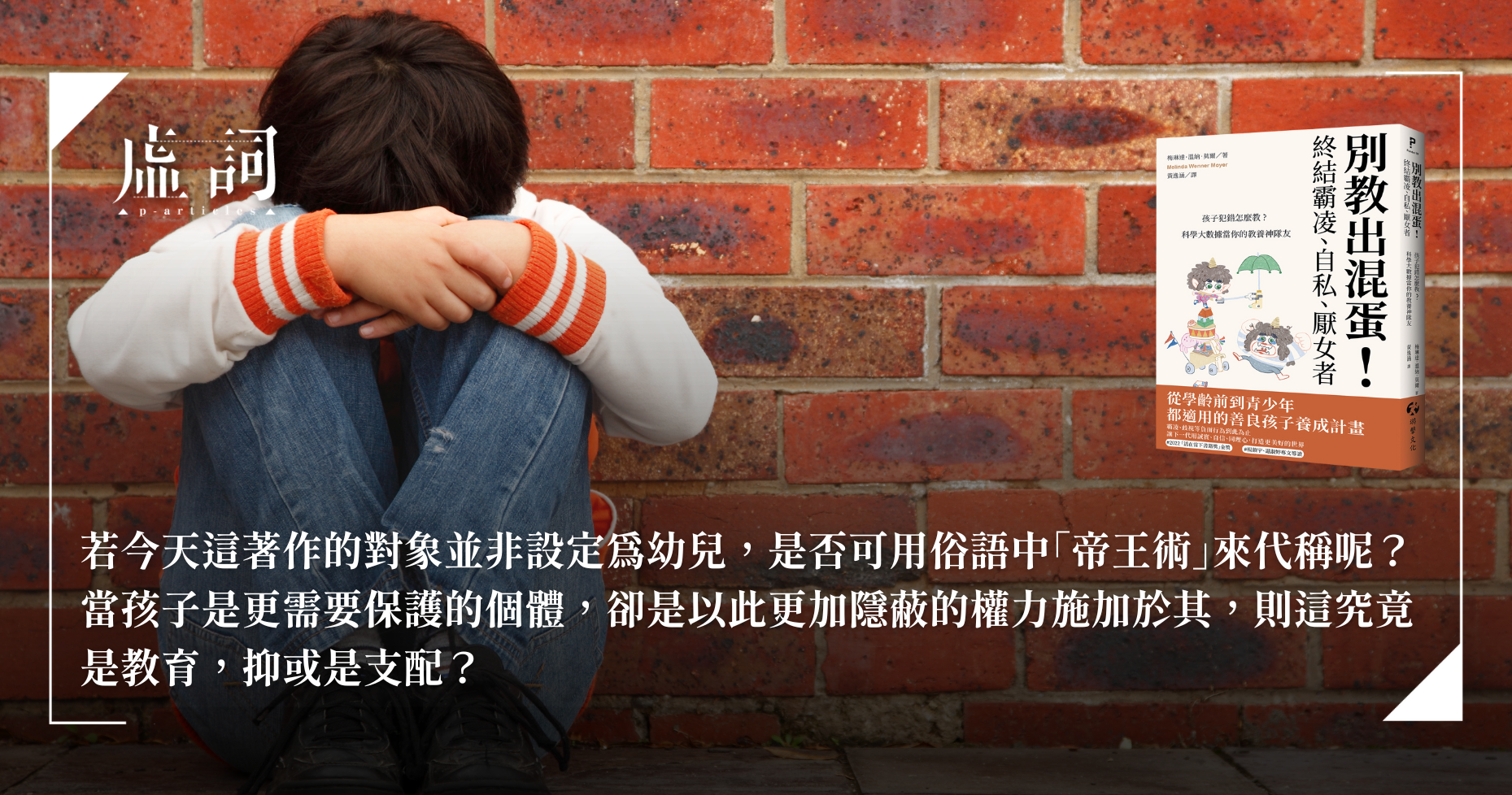
虛詞無形FB - 2024-08-01T152108.366.png
無論是任何工作,都要有相關的知識背景與技能,應徵時要投履歷證明自己的能力,而自行創業若沒有相關的準備,往往也有志者事竟不成。我們往往稱呼父母教養孩子為「父職」、「母職」,然而這份工作完全不需要有任何背景與技能,唯一需要的只有生殖功能發育完全的人類進行生殖行為,那麼就能獲得這份工作。但有多少人能做好這份「工作」?又有誰能評判誰做得好?好或壞是根據什麼判定的?或許這些問題的答案莫衷一是,甚至昨是今非。
《別》這本書可以歸類在「工具書」的類別,主旨是以科學之名講述如何教養小孩。內容不能稱之為陳腔濫調,因為對於一些人再清楚不過的觀念,可能對於其他人卻是聞所未聞,因此書中有些概念的提出與強調,仍是有其價值。例如:
「沒有哪一種辦法絕對正確;重點是持續對話,才有機會創造改變。」(頁212)
「簡而言之,請與孩子聊聊你們彼此、他人、所有人的感受,將他們的行為和選擇連結到他人的感受;孩子在氣頭上的時候,即使你一心只想翻白眼,也要認可他們的感受;等孩子稍微冷靜,可以討論你們認為適當的情緒表達方式,並幫助孩子找出未來面對困境時可以運用的對策。」(頁47)
「時時提醒自己思考,孩子的行為是真的調皮叛逆,或者只是因為他還不具備你以為他已擁有的技能。」(頁239)
「我就眾多主題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建議,你的腦子或許現在還有些混亂,但如果要我將所有建議濃縮成一句話,那就是:發揮同理心,建立情感連結。」(頁335)
「一九九六年,有一項研究...比較接受處罰等威權管教的孩子,在父母『誘導』之下理解他人所受影響的孩子,表現得更大方慷慨、更有同理心。」(頁44)
「結果發現,比起警告他們不誠實有和壞處,教導誠實的好處反而比較能讓孩子有所收穫。」(頁124)
「...成就斐然與一事無成的關鍵就在於動機與努力,而非聰明才智。」(頁63)
「要教導孩子隱私權(還有積極同意〔consent〕與身體界線)的重要性還有一個好辦法,就是即使孩子還小,也要先徵求他們的同意,才能把他們的照片發佈到社群媒體上。這樣能讓他們知道,使用社群媒體時,應該要尊重他人和對方的隱私權,而且每個人應該都有權掌控個人肖像的分享狀況。」(頁293)
這其中包括溝通的重要、同理孩子、獎勵取代懲罰、成就在努力(後天)而非才能(先天)、隱私權與自主權(同意)。較無異議的或許是溝通、同理孩子、隱私權與自主權。溝通是民主得以存在的要素之一;對於孩子的同理則是重視其感受並尊重其作為主體;隱私與自主則是可見於諸多自媒體經營者以小孩作為行銷工具由此而生的剝削問題,以及對此項目的怠慢或將可能造成日後孩子成長時青春時期犯錯的可能。
然而,成就與否與才能是否無關?獎勵才是正道而懲罰是邪道?
「多項研究一致指出,和善慷慨的人(包括孩童)幸福感比較強烈。二零一九年,研究人員針對三十年份的資料進行分析,在控制了家庭經濟地位和孩童智商帶來的影響後,發現在幼兒園時期較為善良慷慨的男孩,成年後收入較高,且差異顯著。」(頁27)
「為世界帶來改變的大人物,通常在面臨挑戰時都會展現不屈不撓的任性,對於自己的目標則是懷有滿腔熱血,且心無旁騖。」(頁65)
「...我當然是人性本善派的。我認為,孩子只要獲得豐沛的愛、同理與引導(包括設下界線),通常長大之後也能具有愛心、同理心和出眾的才能。我們不必隨時為孩子傾盡所有,可是要提供充足的支持。科學研究也支持這樣的結論。各領域的研究都顯示,孩子只要獲得所需的幫助,本質上都是善良正向的(一般而言,所有人皆是如此)。」(頁336-337)
我們可以質疑,是否作者相信「人性本善」,進而才提出諸種論述?尤其,採納對此結論有利的研究、證據?換句話說,射箭才畫靶,那能不中的?
作者提出善良的男孩成年後收入較高,然而我們可以看到諸多的富豪(例如川普、馬斯克)是否能被「善良」所涵攝?而若人性本善與獎勵可取代處罰,此不正等同於認定法律是無效的?法律中人的圖像是性惡的(主要是刑法),否則根本無需制定法律,尤其我們更難以對於一個孩童斷定其性惡或善。所謂的善惡是倫理學上的概念,而善行與惡行是主體在自由意志下所為行為經一定標準(例如倫理、法律)判定的正負價結論,惟兒童(未成年人)仍不具有「主體」的資格(較合適者應為「準主體」的身分)、不具有完整的自由意志,也因此其所為方無所謂善惡可言(例如法律上的無行為能力、無責任能力)。
甚至,我們可以在孩子身上見到我們會稱之為「殘忍」的行為,例如拿放大鏡燒螞蟻、拔掉昆蟲的翅膀,甚至攻擊動物。但這無法稱之為「惡行」,因其仍不知其為惡,反過來說,扶老奶奶過馬路也無法稱之為「善行」,因其仍不知其為善。就連《蒼蠅王》著作都無法武斷地將孩子劃歸全是「乖孩子」。且,作者肯定了努力,似乎否定了具有本質性的才能概念,然而卻又相信著「人性」具有本質上的善與惡,那麼又是什麼可以做出如此歧異的判斷?更別說舉許多動漫為例,前期貌似著重於努力,然而最終主角之所以是主角的理由,還是血統(如同才能一般,先天的)。說到動漫,松本大洋的《乒乓》正是說明了人有才能之別,有時候一昧的努力終究只是徒勞,「認識自己」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在一種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幻想裡頭過了一生。
回到教養這個主軸,教育這件事貌似有著良善的外觀,然而本質上卻是權力(power)的施展。「教育的目的,是在把個人陶養成為社會的分子。」 (Emile Durkheim,《社會學方法論》,頁8)。而這所謂的社會化,也正是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分析監獄時所說的「規訓(dicipline)」過程(例如監獄、學校、工廠、軍隊,都是規訓的場域)。固然在書中提到諸多教養策略的段落,例如:
「…人們如果是出自個人選擇,做事會更有動力,並且覺得握有較多自主權;一旦感受到被強迫,就會很快失去興趣...」(頁50)
「規矩就是「艱難任務原則」(Hard Thing Rule):她的孩子必須找出有趣又需要刻意練習的事情來做,而且不能在一季或學年結束前半途而廢。同等重要的是,這件事必須是她們親自挑選,不能是家長強迫。...達克沃斯在《恆毅力》一書中寫道:『終極目標是培養一種使命感,這是有趣又困難的事。』...達克沃斯還寫道:『如果我有一根魔杖,我要讓全世界所有的孩子都從事至少一種自己選擇的課外活動,而就讀高中的孩子,還必須堅持一項活動至少一年。』」(頁68-69)
「顯然,我們鼓勵孩子的方式真的很重要,而且我們的做法越不讓人覺得刻意操控,孩子就越能發揮創意、保有動力。只要我們不那麼積極地想控制孩子的行為,他們或許會比較晚才達到我們的要求,但卻更有機會培養出內在動機。...」(頁85)
不僅要影響孩子的決定,還要讓孩子認為那是自己的決定,因為這樣孩子才會覺得有較多自主權,才會繼續做下去,這無非是 Bachrach and Barartz 提出的「權力」概念,亦即並非屈從他人之意志,卻是使議程中自始就不存在特定的選項。試想,若今天這著作並非標榜著「育兒」、「教養」,也就是這些方式的對象並非設定為幼兒,是否可用俗語中「帝王術」來代稱呢?惟,當孩子是更需要保護的個體,卻是以此更加隱蔽的權力施加於其,則這究竟是教育(education),抑或是,支配(domination)?在「為了你好」之名下,可以正當化多少所謂的教養呢?(參閱拙著,《公民社會》,<善意謀殺>,頁124以下)
《別》中也有些部分不知所云,例如:
「並不是說恆毅力強的人就絕對不會半途而廢,或一定會甘於花費好幾年的時間投入你要求的事物。通常他們會選擇對於自己發自內心感興趣的事物努力付出,而在摸索興趣的過程中,可能會放棄其他事物。...如果你的孩子要求不再跳芭蕾,也不表示他就是缺乏恆毅力。...恆毅力會在孩子終於找到興趣時才展現出來...」(頁66-67)
「霸凌者看到其他孩子向他的目標示好,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引起反彈,也沒有達到預期中排擠對方的效果,有時就會罷休了。」(頁99)
「若要指引孩子在面臨霸凌時該如何應對,我認為核心觀念是別叫你的孩子反擊。...選擇反擊的受害者通常會失敗,畢竟霸凌者挑選目標的標準,通常就是因為對方個頭較小或是肢體能力較弱,而且研究顯示,不少人試圖反擊後,之後反而被霸凌得更慘。...如果你的孩子遭遇網路霸凌,請把證據截圖留存(也要確保孩子知道怎麼取證)。然後,建議孩子在所使用的社群媒體平台上封鎖並檢舉霸凌者。」(頁105-106)
「如果你家的寶貝跟我兒子一樣,會為了拖延上床時間而謊稱想上廁所,就告訴他睡前只能上一次廁所,他想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但如果濫用了這唯一的機會,最後就只能難受地憋著,甚至因憋不住而弄髒自己和床鋪,那也得承擔這個後果。」(頁126)
「如果孩子在你勸阻之後依然持續觀看色情內容,那麼你該做的或許是放手不管。」(頁329)
就作者所提出的恆毅力(然本文對此類概念不甚苟同,僅因不過為修辭而不具更多知識上的意義)是以孩子找到興趣會展現出來,然而放棄也不代表沒恆毅力,有恆毅力的人也不代表不會放棄。那麼究竟該如何判別這是不是孩子的興趣?有沒有所謂的恆毅力?再者,霸凌若是在看到被霸凌者有人向其示好,「有時」就會罷休了,那麼「有時以外」呢?如果示好的人也一同被霸凌呢?甚至,對於霸凌作者建議不要反抗,理由是被霸凌者通常弱小,但這似乎並沒有科學實證,甚至有時更會讓人驚訝的是被霸凌的反而是塊頭大於惡霸的孩子。更不用說,面對網路霸凌作者的建議是封鎖跟檢舉,面對孩子接觸色情內容最終解是放手。這些內容與其說是教養策略(具有實用性),更不如說只是彰顯一個第一世界中產階級對於教養的幻想而已。(內容的價值與作者對於自身身分與教養實踐的坦白無關)
或是有些部分前後矛盾,例如:
作者提到兒子不願分享,女兒樂意分享,「這兩個孩子出身同個家庭、擁有一對相同的父母,甚至有一半的基因相同,怎麼會這樣?老實說,有時我也搞不懂。」(頁36)、「我的女兒主動把萬聖節糖果分給我的時候,臉上總是洋溢著興奮,這點經常使我驚訝不已,卻也有其道理,因為慷慨付出確實是一件快樂的事。」(頁38)
「有一次,他甚至已經彎下腰,想去撿掉在地上的垃圾,卻突然停住並抬起頭問:『我撿起來的話,可以得到點數嗎?』」(頁82)、「我認為獎勵之所以奏效,其中有個道理就連反對派都不太明白:獎勵有助於好習慣的養成,而養成好習慣之後,有些事情就會變成下意識的行為,此時動機便不那麼重要了。我兒子就是這樣:我們一開始會利用點數來說服他洗自己的碗盤,但過了一陣子洗碗盤就成了習慣,不用別人提醒他也會自動去做。時至今日,即便不會獲得點數,他依然維持這樣的習慣。」(頁83)
「…學校處理霸凌的其中一種不當作法就是『調停』:讓霸凌者和受害者坐在一起,試圖化解衝突。」(頁107)、「(4)不要無視子女間的糾紛,也不要介入裁決,居中調停即可:協助孩子傾聽對方的意見、理解對方的觀點,然後構思解決辦法。」(頁269)
「所謂的霸凌,必須是蓄意且一再地騷擾或虐待,根據魏斯曼的解釋,是涉及「摧毀某人的自尊與固有價值」,根據他人感受到的固有特徵不斷發起攻擊(可能是過於安靜這種簡單的事情,也可能是源自對方族裔、信仰、性別認同或性傾向的特徵。)...」(頁91)、「如果你的孩子一再嘲弄別人,即使並未懷有惡意,但只要讓對方覺得無助或受傷,那就算是霸凌。」(頁98)
作者既稱付出是快樂的事,而女兒會分享所以她快樂,那麼為何兒子卻不願分享?當然,作者說了:「老實說,有時我也搞不懂。」那麼於後所斷言的「付出確實是一件快樂的事」又是所為何來?其次,作者在談論經由獎勵養成(或說規訓)孩子的好習慣,對於兒子撿垃圾仍追求獎勵然而洗碗卻不再追求並未提出解釋,僅草以養成習慣後變成下意識動機就不再重要(那麼這是否已被規訓至如同機械般的操演);調停在一方面(學校)是被批評的,在另一方面(家庭)卻是被鼓勵的;霸凌的定義先是以蓄意為必要,而後卻以縱無惡意亦仍屬之。這些矛盾多會出現在當特定段落作者需要論證特定的結論之時,也就是說,如同前先提及作者對於「人性本善」的預設立場,在其他地方作者也對於所謂權威式(authoritatvie)教養有所鼓勵(頁96-97),甚至在提到「在二零一四年一項大型研究中,...發現兩種方式均會各別影響到子女參與捐贈和志工服務的情形,表示口頭指導和親自示範都有效。」(頁56)時,卻只介紹以身作則(也就是預設此為推薦的項目)一般。
剩下的部分,作者有提到例如:
「孩子不見得會留意到你做的每一件好事,所以有時刻意明示也不錯。...研究顯示,孩子偏好幫助曾幫助過他們的人,但前提是他們得先理解到自己曾經受到幫助,而孩子不見得會意識到那些看似無形(卻無窮無盡)的事,是我們為了他們才做的。」(頁57)
「如果女兒在你說不該再吃糖果之後又偷吃,請說明違反規定會破壞家人之間的信任,你以後會很難再相信她。」(頁235)
如果用白話來說,這不正是情緒勒索?
作者有使用相當的篇幅討論在教養層面上的性別與種族等議題,然因此另涉身分政治領域,或會延伸過廣,於此僅略述本文對《別》書中關於此等議題之想法。作者提到:外觀有諸多特徵(髮色、瞳色、膚色、身高、體重)得分辨不同個體,然而人卻總以他或她來辨別(頁135);性別問題的根源為諸多場域(男女廁、男女校等)以性別為區分將性別作為重要社會類屬(social category)予以強調(頁135-136);不討論膚色的養育方式可能使得孩子種族偏見大於談論之(頁199);過於強調社會類屬會凸顯重要性導致刻板印象,不談會傳遞該議題重要且禁忌,「性別和種族正好就坐落在這個光譜的兩端:我們過度提及性別差異,卻又太少談論種族議題。」(頁212)
固然「溝通」的價值值得贊同(所以本文對摩根費里曼式無視種族歧視的作法不認同),但其他部分則有難以忽視的「偏見」。諸如外觀有諸多特徵得以分辨,但人既千萬譜,加以人總傾向於二元化的思維,最簡易的分類方式正是明顯的生理性別(sex),否則依照作者所列舉之各種其他特徵進行分類,人類是否仍有餘裕發展至如今文明?(甚至正是如今文明有如此餘裕方有機會使作者得發此議)而以「性別」作為區分個體也並沒有「錯」,若以「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作為平等原則的闡釋,那麼重要的並不是有無區別對待,而是有無「正當的區別對待」。例如男女因生理特徵不同分有廁所,於生理上的考量以及風險管控,都是正當的;惟若同工卻因性別不同酬,這才是不正當的。若性別與種族皆是外觀上可見的特徵,何以任何一者應被漠視?(於作者之立場,其認為美國社會漠視種族差異,作者則多有漠視性別差異的論述)
教育,一直是問題的問題,也是問題的解答。固然《別》以科學為名,但充斥著預設立場(偏見)、矛盾以及語意不明,至少在最基本的一致性(coherecy)上,就有失格之虞。更且,縱使善意理解作者所述有研究為基且為平易故,然行文卻未有引註,於諸多地方更僅泛以「有研究指出...」,但究竟是什麼研究也未指明(即便最後附上參考資料也無礙於此批評),尤其,預設立場將也將使得方法上有是否科學之議。但這或許都不太重要,因為有時候重要的不是科學與否,而是宣稱科學與否,「吸引力法則還是癌症心靈治療,都建立在一個宇宙是人的心靈所創造的不可靠的不科學假設之上,但是對於這些人來說「有研究指出」就已經很充分了,至於是甚麼研究、有沒有對反的研究,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結論是自己需要的,甚至『有研究指出』這句話、出現在紙張上的這句話,就成為了能附庸的另一個權威。」(拙著,《失控的正向思考》──不樂觀,就該死,連結:https://paratext.hk/?p=3948#google_vignette)
因此,有這麼一個作者這麼一本書寫著有這麼一個研究這麼說所以該這麼做,那最容易了,使人自願遵循於特定文本相較於文本內容的各種方法是否有效,不正是作者的教養策略實踐本身嗎?但是,這樣的情形不正是我們需要「教育」的理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