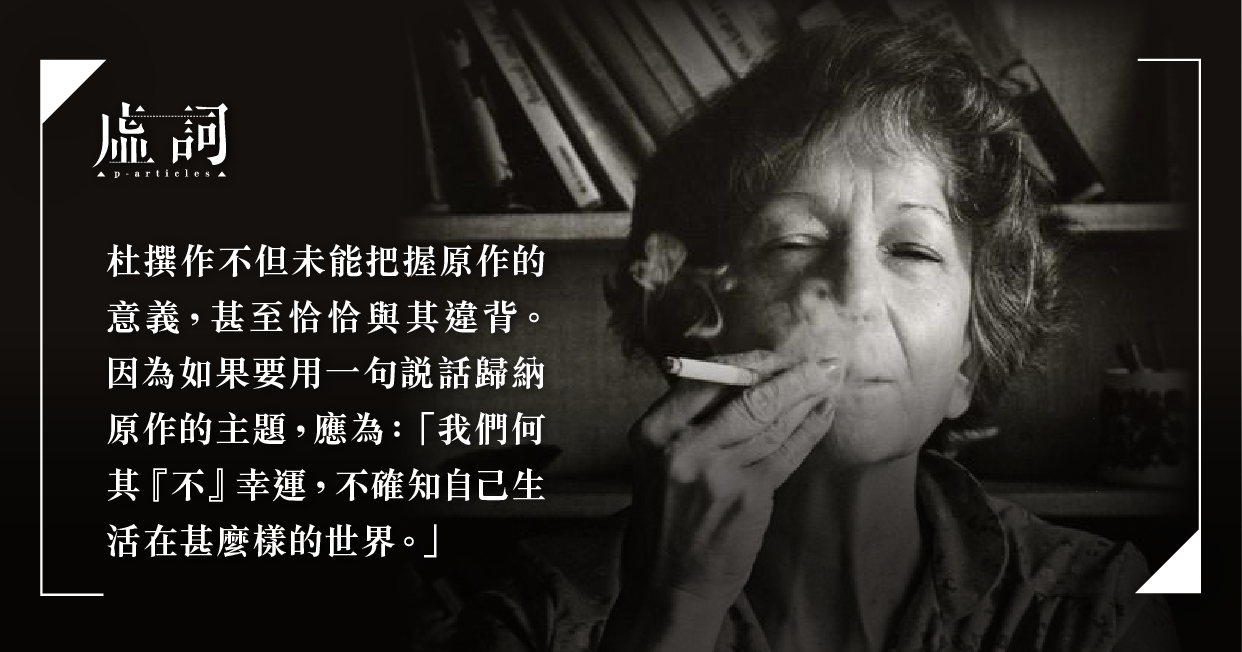看過原作甚具諷刺意味的詩句以後,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杜撰作不但未能把握原作的意義,甚至恰恰與其違背。因為如果要用一句說話歸納原作的主題,應為:「我們何其『不』幸運,不確知自己生活在甚麼樣的世界。」的確,辛波絲卡常以自然生態入文,也表現了對觀察萬物的熱情,但這種熱情,是基於她對知識的好奇心,近日出版的辛波絲卡傳記中文版《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裡面有提到辛波絲卡在她的讀書專欄「非必要閱讀」中,介紹最多的不是文學書籍,卻是各種各樣的科普書、指南,範疇包括但不限於:自然(譬如,關於蜻蜓或蝴蝶的書)、歷史、人類學等等,她甚至認為費曼的《費曼物理學講義》是她讀過最有趣的書籍之一。[註2] 像她這樣的一位讀者,怎麼可能會寫出「我何其幸運/因為我不是氣象學家/不用知道雲彩如何形成或氣流裡有甚麼成分」? (閱讀更多)
【悼米蘭昆德拉】笑與忘,輕與重——略談米蘭昆德拉的傳世辯證
故事與說理,固然屬於兩個層次,把明顯不同的層面置入角色的遭遇、他們之間的衝突、處境的變化發展等,與其說會帶來抽離的效果,鼓吹讀者進行相關主題的思考,時刻意識到敘事的意圖和局限,不如說是一種精心布置的風格。用得好的話,便宛如將邏各斯(logos)和迷思(myth)兩大人類文明的表達式,交叉運用,相互配合,宛如《莊子》所謂的兩行之道。而昆德拉在其創作黃金期(六十至八十年代),庶幾近之。 (閱讀更多)
【無形・辛波絲卡,種種可能】用詩奪回個人的完整性:談辛波絲卡的政治詩
其他 | by 林蔚昀 | 2023-07-11
我個人認為,說她很有意識地寫社會詩、政治詩(尤其是那種要熱血改變社會的議題詩),有點過頭。但是她的詩中確實有政治。那是不直接的政治詩,是「可是可不是」的政治詩,是讀者可以創造、互動、參與的政治詩。和〈與石頭交談〉裡面那顆冷冷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石頭相較,辛波絲卡的詩邀請人走進來,你可以在她詩中找到你想要的東西,你可以感覺,可以思考,甚至可以發笑。 (閱讀更多)
「自由舞2023」: 繁花與餘香
其他 | by 俞若玫 | 2023-07-13
喜見「自由舞2023」沒有淪為一個只為娛樂及旅遊服務的舞蹈節。策劃團隊在選取節目上顯出平衡功夫,既要考慮票房,又要培養及刺激觀眾口味,同時支援本地編舞家持續創作。可以說,一手安排優質的節目,另一手新增形體導賞,普及舞蹈知識和眼界,同時打開編舞視野。不過,在性別議題論述及討論方面,還可以再深入,女藝術家也不一定有很強的性別意識。希望來屆對「自由」的意義有更多元及豐富的呈現,在選取節目時,不妨多引入白人以外的作品,舞種也可以更豐富,如果以社會議題為焦點,期待有更深刻的論述及研究,讓繁花餘香四散。 (閱讀更多)
第十七屆「鮮浪潮」本地短片札記
剛過去的「第十七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十四部本地競賽短片中,何思蔚的《直到我看見彼岸》奪得「鮮浪潮大獎」與「最佳攝影」,今屆擔任映後談主持的曾肇弘,趁著賽果塵埃落定之際,總結看過本地競賽與非競賽短片的個人感想,並分享兩部與獎項無緣的遺珠。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