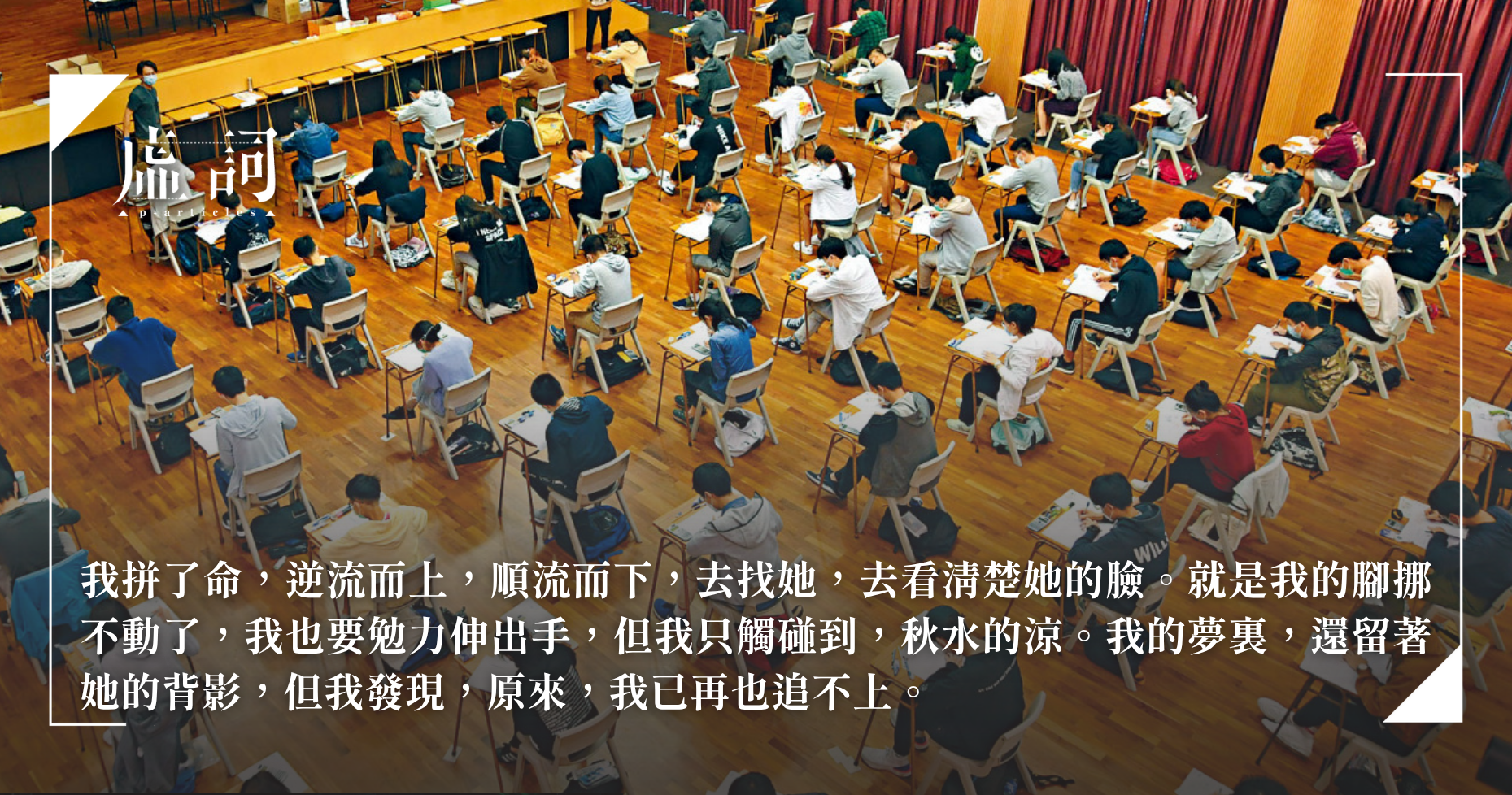離開拉斯維加斯
散文 | by ⿆卓穎 | 2025-07-12
⿆卓穎傳來散文,書寫自己過著刻板而漫長的工作日常,在中環上班的她更自覺處身於⽔族館,裹面的⼈在四通八達的⾏⼈天橋和偌⼤空間流來游去,卻始終游不到出去,令⿆卓穎回想起電影《離開拉斯維加斯》,Nicolas Cage 飾演⼀個酗酒的男⼈,溜進沒有時鐘的賭場,不分晝夜地沉淪在酒精之中。⿆卓穎認為這種墮落讓⼈不敢直視,但沒有表徵的⼼癮更為可怕,眼前的所有⼈以及自己,均對按部就班的⽣活上癮,眷戀⼀種病態的認同感和安全感。 (閱讀更多)
慢慢游
散文 | by 小煬 | 2025-07-11
小煬傳來散文,指自己總怕落在別人身後,更怕被時間扔下。不論中學、大學、讀博士還是工作,都奪力追趕社會的期待,只為離「上岸」更近一步。直至有次游泳時,身旁的教練建議他游得慢點,小煬放棄把動作做標準的執念後,反而游得更自在。那一刻,小煬頓悟自己被主流打造的生活圖景吸引和捆綁多年。 (閱讀更多)
蛇美文蛇美人
今年正值蛇年,令惟得想起吳煦斌的〈獵人〉的蛇,其攝人心魄的雙重本質——既令人著迷,又暗藏殺機。此蛇的意象不僅停留於自然,更延伸至藝術領域,特別是荷里活黑白電影中的蛇(蠍)美人形象,《殺夫報》的菲莉絲嬌媚外表掩蓋致命野心,又到《墮落天使》的史蒂拉至《舊恨新歡》的凱西等等,她們雖命運不同,卻同樣有蛇的冷酷與魅力。 (閱讀更多)
悶
散文 | by 俞宙 | 2025-07-04
俞宙傳來散文,他總是提醒自己別買太多人偶,要不然之後搬家真的很麻煩,但總是一而再再三地敗下陣來。他認為躺在盒子裡的人偶是最完美的,四肢以鐵絲細細綁縛,規矩地固定在瓦楞紙盒裡;頭髮壓得服服帖帖,盒子一側塑封著精緻的衣服和飾件。把娃娃取出來,就像解救一個被封印的沉睡精靈。替人偶梳妝打扮是一樁很神聖的儀式,也是俞宙生活中少數能掌握的安定。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