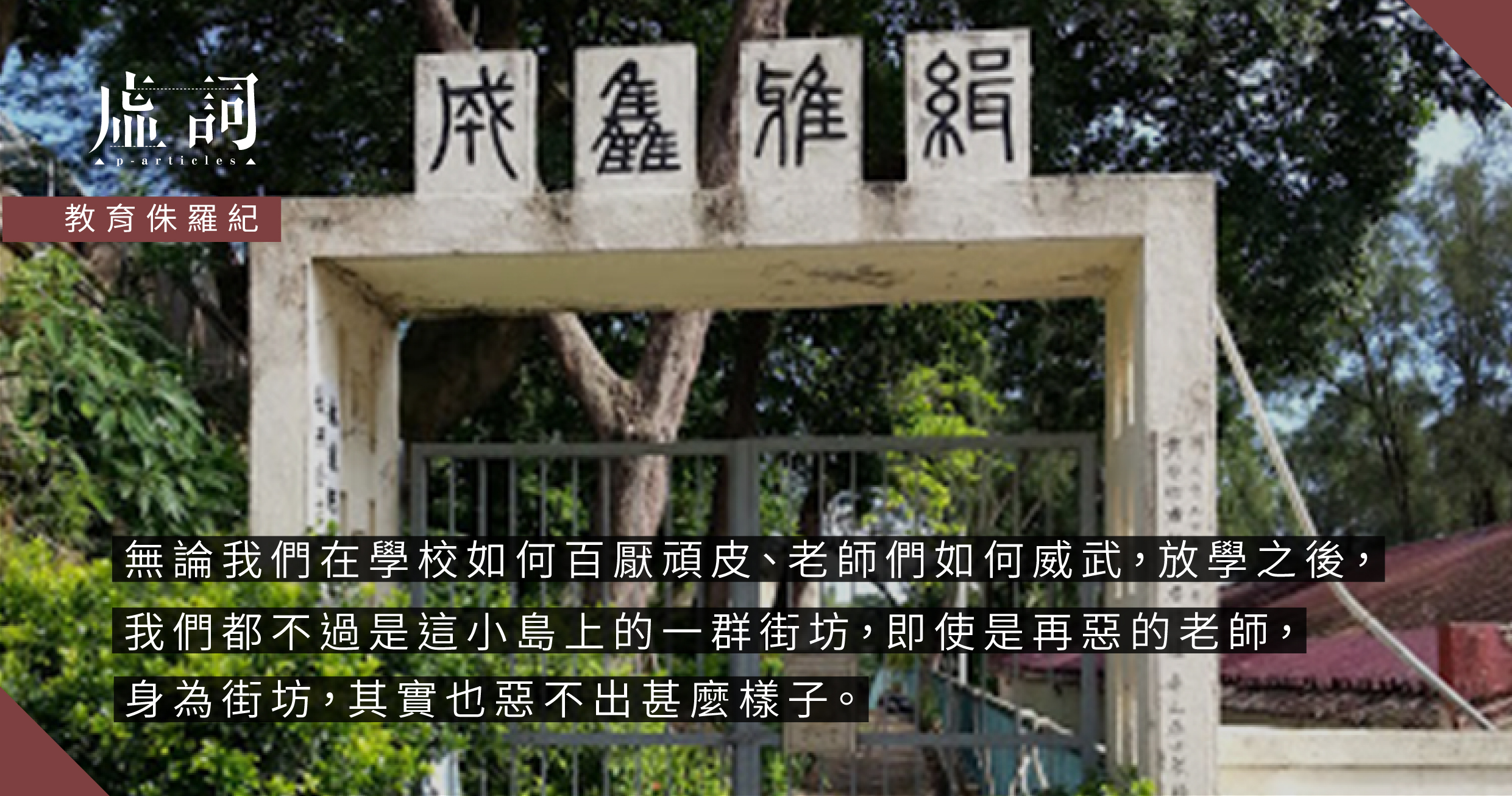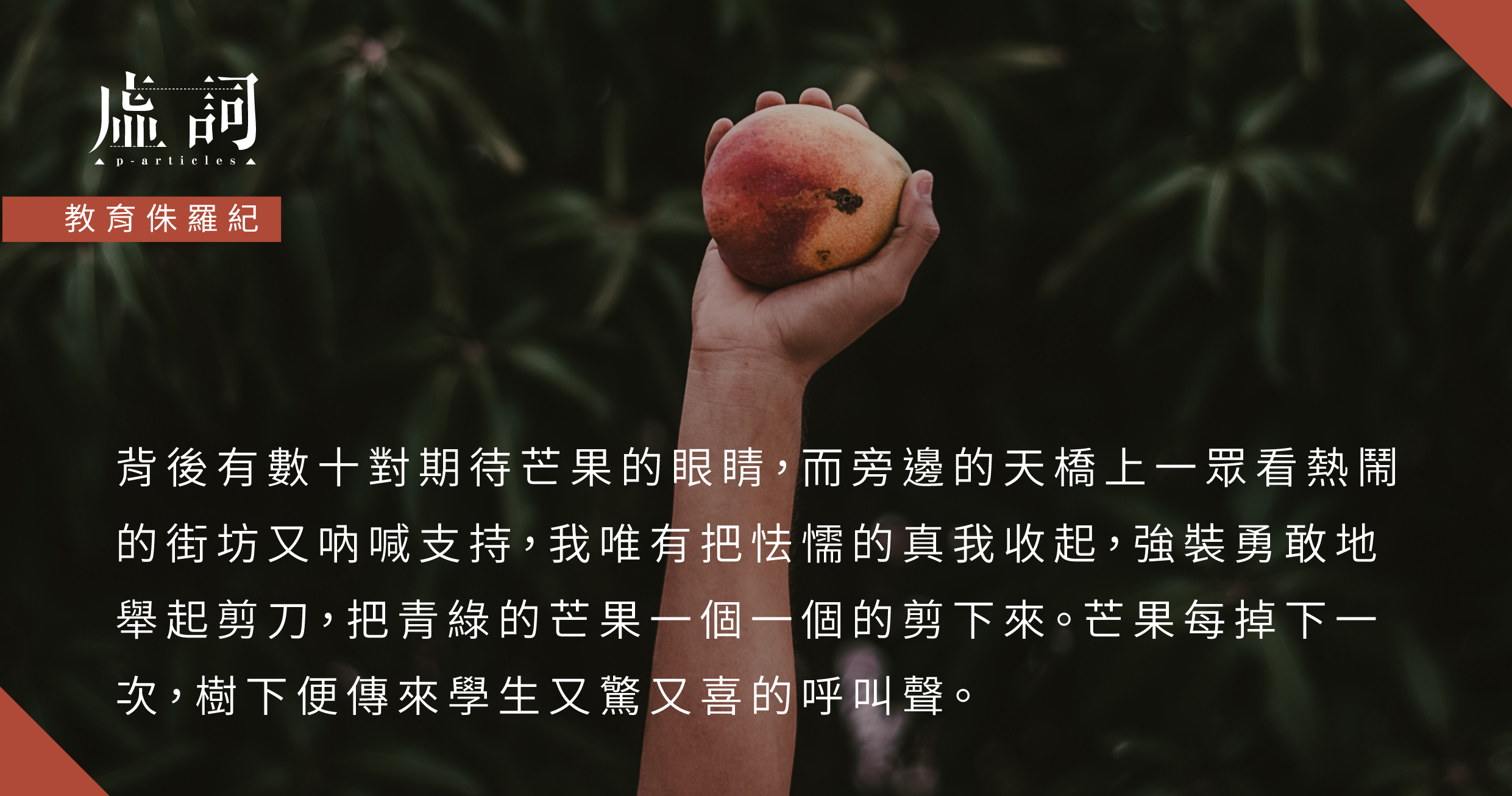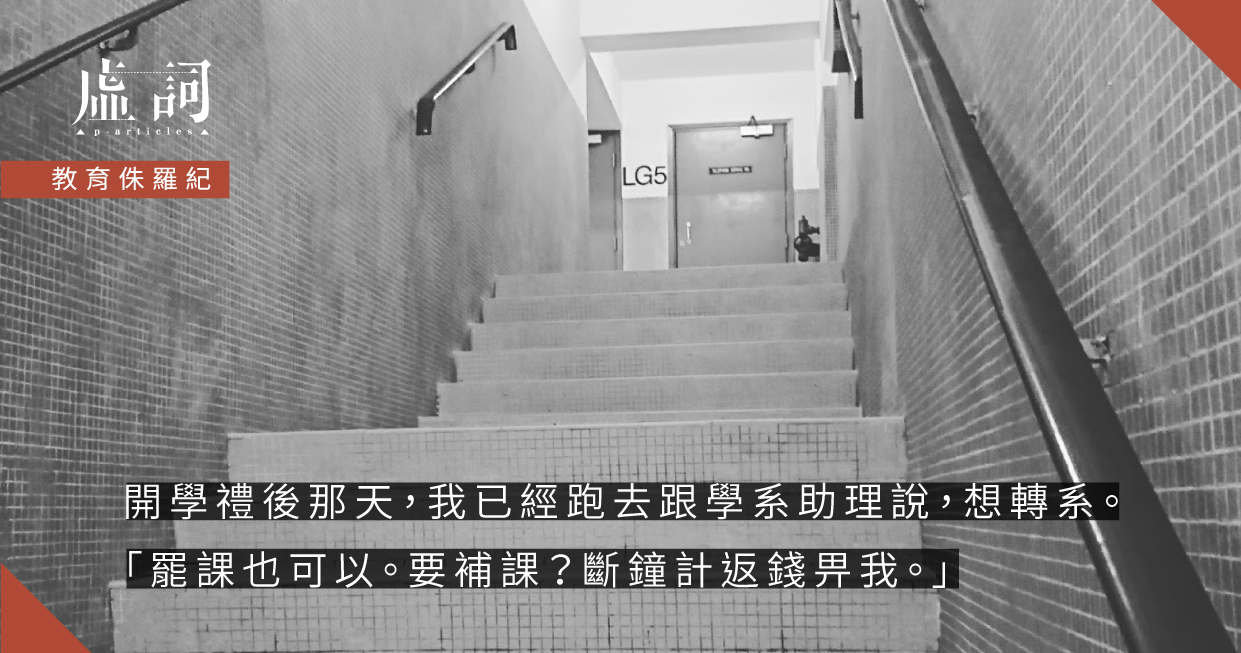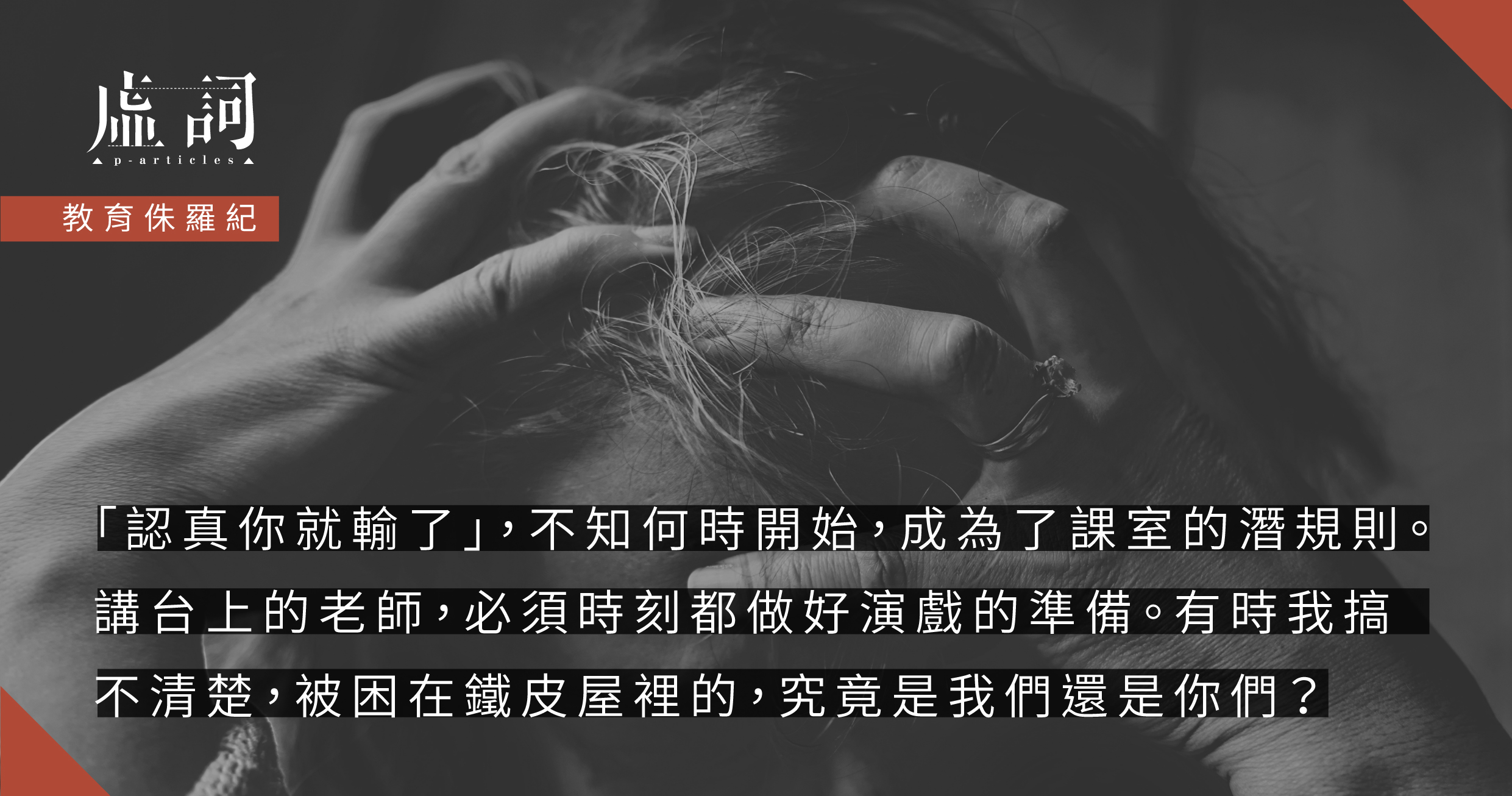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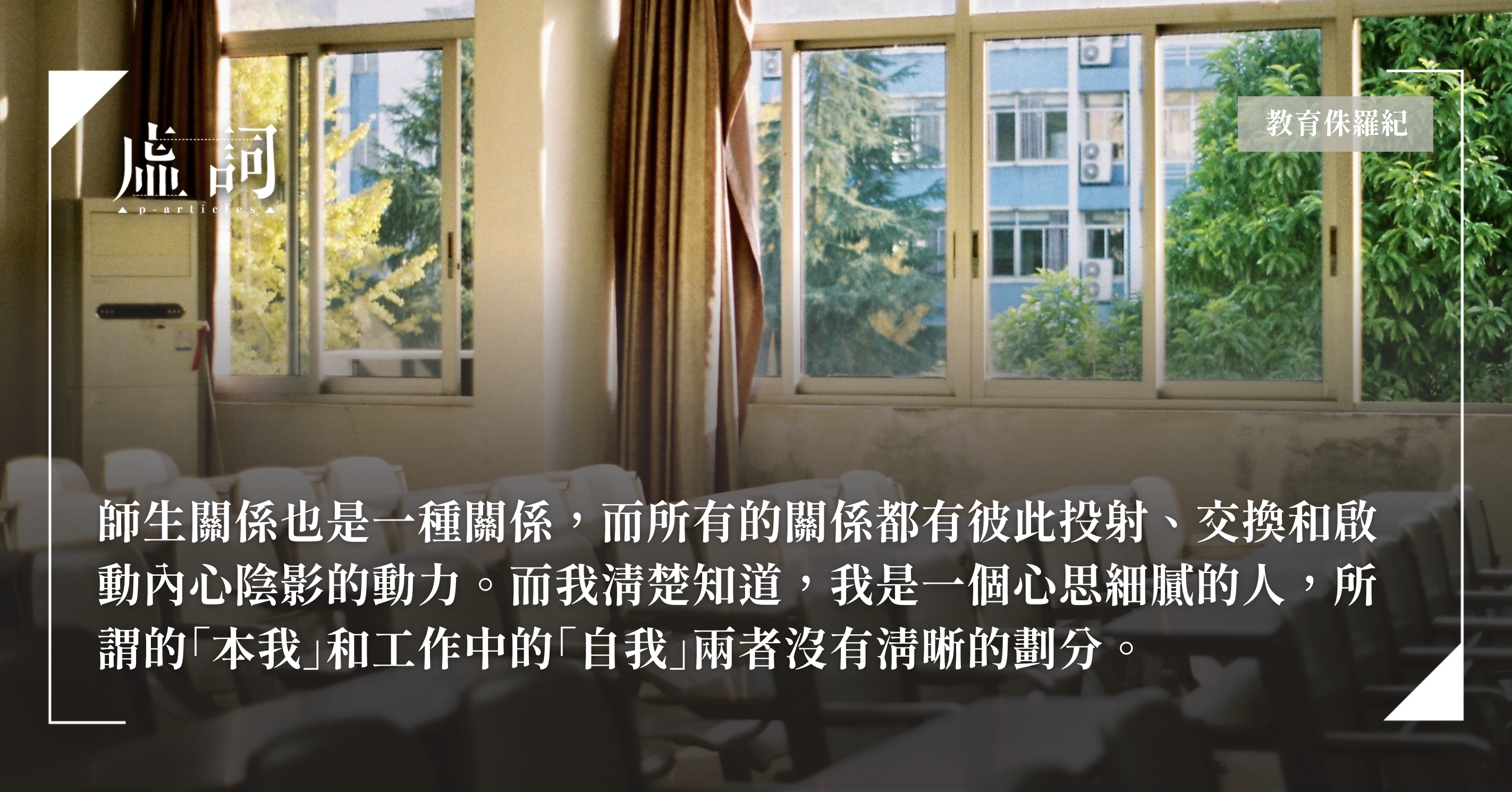
【教育侏羅紀】師生關係六問
教育侏羅紀 | by 小曹 | 2024-03-11
有一次,又再經歷挫敗後,我用了一程車的時間,在手機上打下了6條反躬自省的問題。我慢慢認知到,即使學生有她/他們要負的責任,我內心對此情此境所生起的反應,其實也透露出我自己的期望、想法、需要、投射和執取,以及一系列從我成長中習得和發展的對應方式(coping)。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完成總結 師生同營造幸福校園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3-07-02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並由香港輔導教師協會、香港理工大學專業 及持續教育學院、保良局、東華三院及15所本地中小學主辦,為期三年的「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接近尾聲,近日(29日)舉辦名為「創變力量‧幸福校園」的計劃總結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