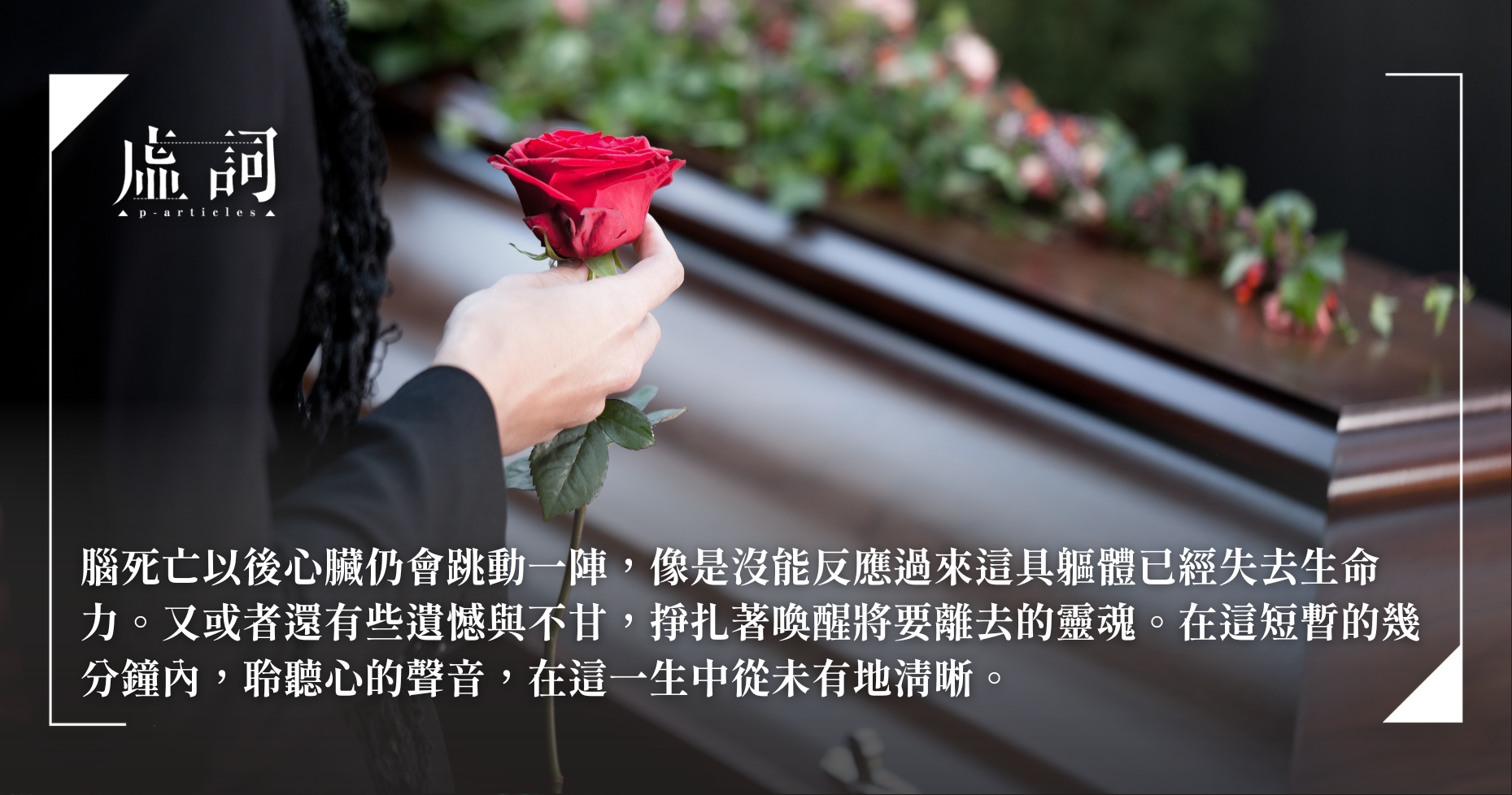我們都是信徒
小說 | by 勞國安 | 2025-06-06
勞國安傳來小說,以「信念」為主題,講述羅拉從唱片店失業後,轉職至投注站,繼而認識了黃伯。每個星期六黃伯都在同一時間現身投注站,風雨不改,每次花十元買六合彩,數十年來只堅持買同樣六合彩號碼,深信這組取自他與妻子生日組成的數字,終會為他帶來好運,贏得六合彩頭獎。 (閱讀更多)
看貓
雙雙傳來散文,指自己受到一本漫畫書《綺譚花物語》,其中一篇〈無可名狀之物〉的啟發,於是興致勃勃地踏上了尋找虎爺的旅程,期望看到可愛的東西後能走一週的好運。雙雙帶著對虎爺的期待從研究室出發,終抵達附近的普天宮,一窺「可愛」的虎爺。然而,這尊神明座下的「貓」,卻與漫畫中的圓滾滾形象有些許落差。 (閱讀更多)
等待莎莉
散文 | by 黎喜 | 2025-05-31
黎喜很喜歡無印良品,總覺得它很簡潔,當中無印良品的背景音樂深深吸引了黎喜的注意,一查之下發現那名為《Down by the Salley Gardens》的歌,並因此認識了莎莉。兩人在校園寫作課彼此鼓勵,分享音樂與人生觀,萌生微妙情愫。黎喜面對莎莉的心意選擇了沉默,成為朋友口中的「白痴仔」。 (閱讀更多)
琴間失格
小說 | by 潘逸賢 | 2025-05-30
潘逸賢傳來小說,講述朗朗自幼學琴,但長大後甚少彈奏擺放家中的鋼琴而佈滿灰塵。在一個大掃除的下午,朗朗憑藉肌肉記憶奏出一曲,卻無法掩蓋鋼琴被冷落的孤寂。晚上,鋼琴突逃然離家園,三腳踏板化作奔跑的動力,它穿越街道、飄浮天際,甚至飛向無聲的宇宙,卻在真空裡失去鳴奏的能力,感慨「生而為琴,我很抱歉」。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