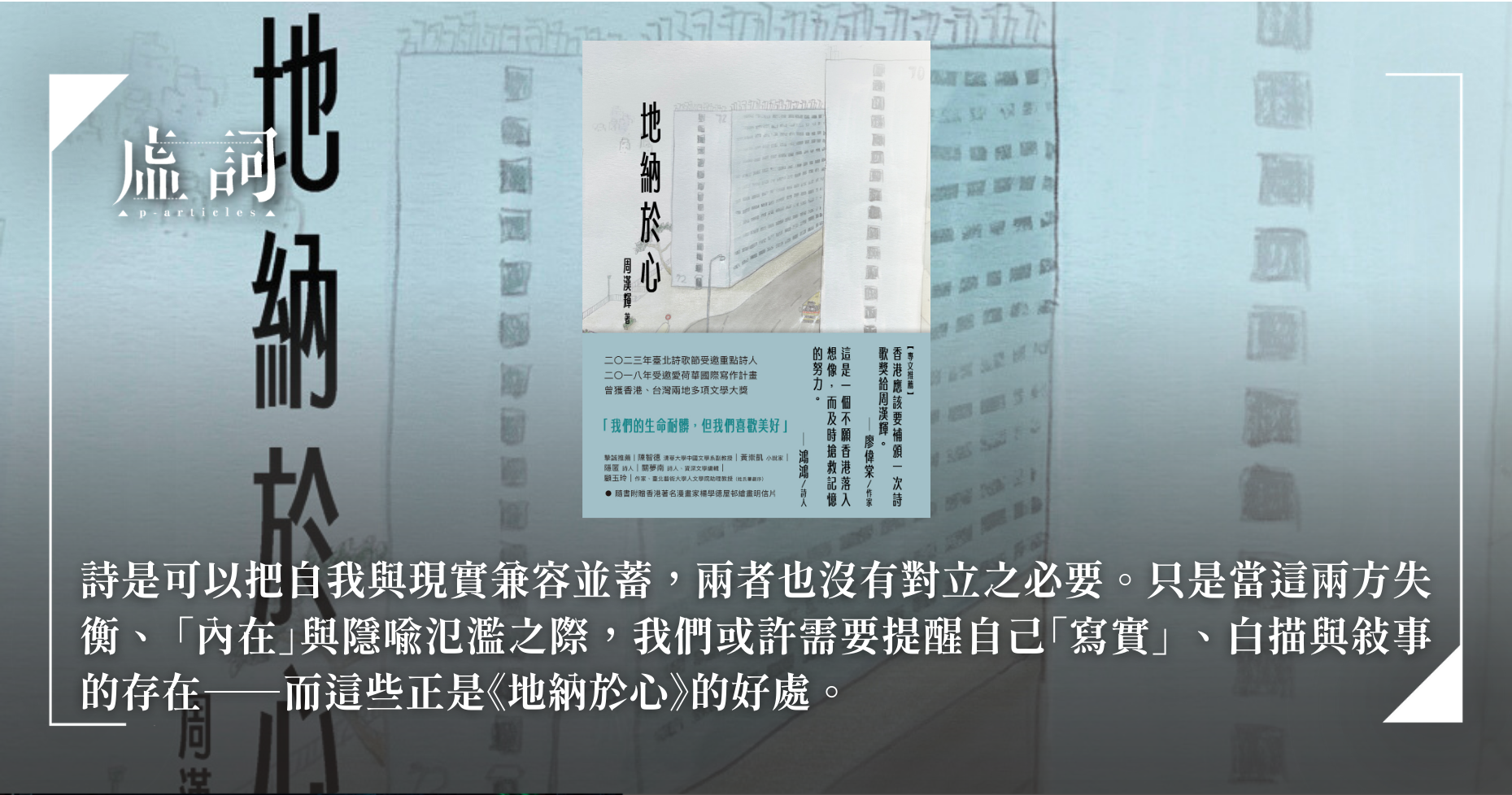蜘蛛網之舞——火中虐讀《撒旦探⼽》
書評 | by 蔡元豐 | 2025-12-30
蔡元豐傳來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評論,指出該書以十二章節模擬探戈舞步,透過「前六章」推進情節與「後六章」逆向重述,構建出如莫比烏斯環般原地踏步、永劫輪迴的敘事迷宮。故事描繪了騙子操控愚民的荒誕行徑,營造出充滿廢墟感與反烏托邦色彩的末日景象,藉此諷刺威權謊言及人性的盲目希望。蔡元豐認為觀乎全書,與其說是「隱喻」,不如讀作連結歷史與當下的「換喻」,是一部結構錯綜、猶如蛛網般的「複雜文學」。 (閱讀更多)
席捲全球的文化力,不是只憑政府大撒幣:讀《韓流憑什麼!》
書評 | by 許景雅 | 2025-12-29
針對席捲全球的韓流現象,許景雅指出《韓流憑什麼!》一書跳脫了過往僅歸因於政府「大撒幣」政策的簡化觀點,轉而從歷史與文化研究視角進行批判性審視。書中強調,韓流成功的關鍵在於民間互動、共創文化與數位平台的擴散;無論是偶像產業或網路連載,均體現了閱聽眾積極參與的動態過程。許景雅認為,該書不僅是歷史紀錄,更揭示出韓國如何歷經後殖民時期的自我探索,從而確立文化自信。韓國成功將「被展示的文化」轉化為具主體意識的「文化品牌」,並重新定義了屬於自身的美學價值與精神內涵。 (閱讀更多)
夜讀隨筆:水底詩社三人詩選《星的答案悄悄成形》
書評 | by 任弘毅 | 2025-12-09
任弘毅傳來水底詩社《星的答案悄悄成形》讀後隨筆,以此書作為學習「感受」的起點。他指出詩集中,翳陽直面疼痛以確認存有,一土以佛性解離轉化創傷,陳謨則在靈肉衝突中尋求詩的鬆綁。作為詩社成立初期的見證者之一,任弘毅稱三人不執著於技藝較量,反以強大的共情能力在喧囂中築起防線——這或許就是他們獨有的,在水底呼吸的能力。 (閱讀更多)
軟科幻的魅力與強悍:只有愛不夠,你必須恨——讀金草葉《派遣者》
書評 | by 郝妮爾 | 2025-11-24
郝妮爾讀畢韓國作家金草葉新作《派遣者》,認為其是她集過往靈光與意志於一身的重要長篇小說。《派遣者》雖以人類對抗外星「氾濫體」的末日戰爭為背景,實則探究著共生、身份與意識,人類何以為人的哲學命題。郝妮爾指出閱讀此書不僅需愛其強大包容,還須恨其挑戰人類個體性,皆因金草葉以小說提出只有愛不夠,人類要以恨記住自己,才能保有自我與回歸的力量。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