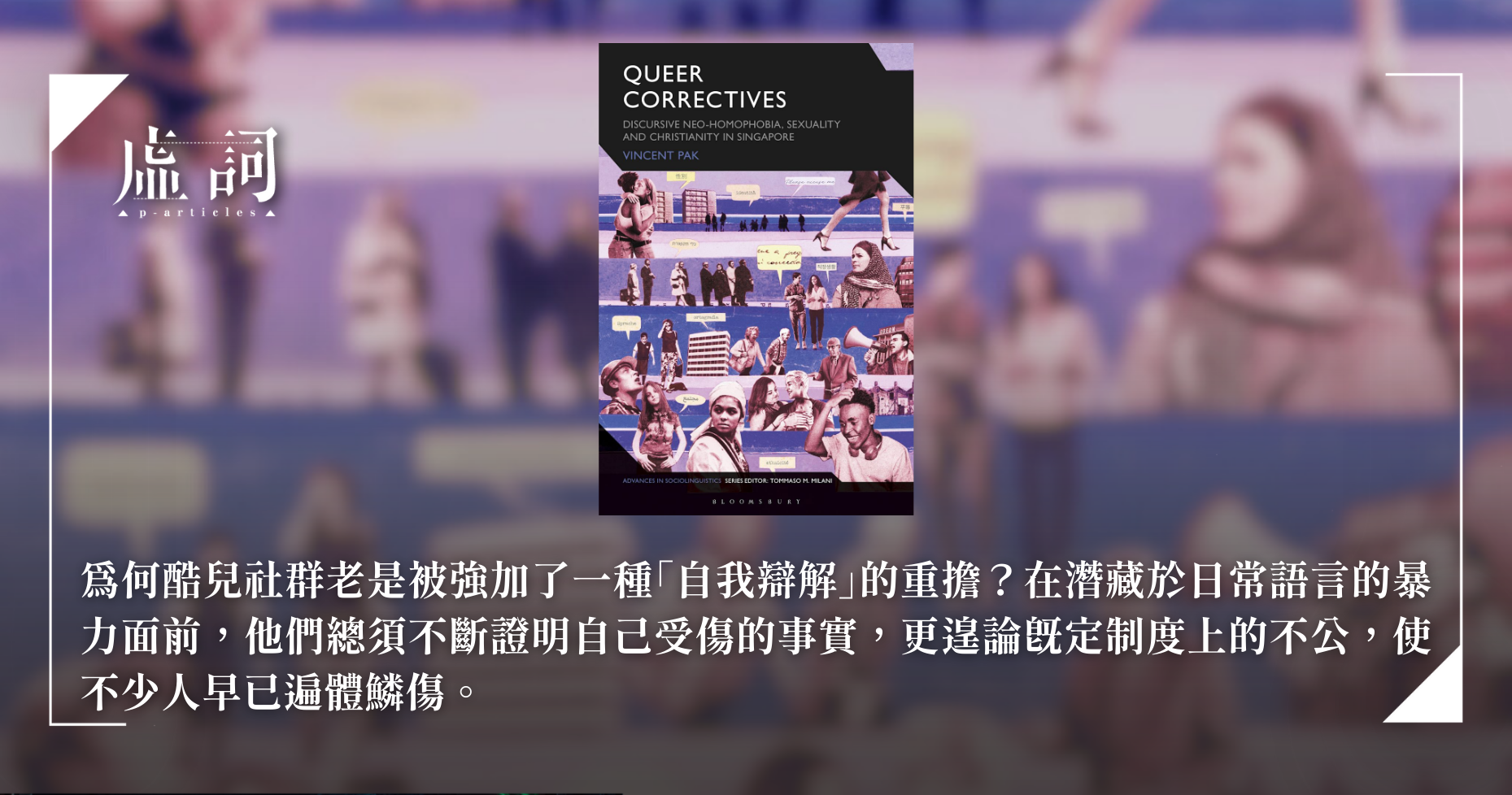語言的桎梏:拴住酷兒的直線——讀Vincent Pak《Queer Correctives》
語言是我們習以為常,甚至不以為然的載體,因此也是最難察覺隱含在敘述中的意識形態。
港大社會語言學學者Vincent Pak撰著的《Queer Correctives》,揭示了對酷兒社群的無形傷害是如何被細密地縫合於日常的話語之中。這裡的關鍵詞不僅是作為賓語的酷兒,更重要的是日常的話語。不論是關注LGBTQ+身份認同,或是熱忱於語言的讀者,不難對書中的洞察有所共鳴。
一開首,作者直接指出語言既能塑造,也能壓逼著酷兒身份。他採用的理論框架主要基於傅柯的文化理論,並結合社會語言學及酷兒理論的觀點,嚴謹而清晰地闡釋了語言如何被用來構建和維護社會的性別規範。
作者以新加坡的「新恐同」現象(neo-homophobia)為背景,剖析該現象如何化成被操弄的語言,繞過受者的審視,悄然蔓生下去。他以宗教色彩濃厚的機構TrueLove.Is為例(該機構曾被批評帶有「拗直治療」的意圖),揭露其如何以裹上愛、恩典與寬恕等糖衣般修辭,將同性慾望描繪成有待矯正、該被背棄的「罪」。
「線」與「家」的解構
有趣的是,作者提出了兩個饒有深度的比喻——「線」與「家」。
作者首先拆解了「線」的意象,將之理解成不偏斜、不歪曲的僵直規範,輔以幾何學和語義學的詮釋。隨後,這一比喻延伸至社會文化場域。「線」可被看成秩序、規訓或效率的符號;往往,酷兒的生活面貌卻被視為是偏離這些規範的存在。譬如相對於「直男/直女」,單從「攣(意指:同性戀)」或「掰彎(意指:把異性戀轉為同性戀)」這些用詞足以反映出偏離直線的意思。
貫穿全書的另一核心概念,就是「metanoia」(意指:悔改或轉念)。作者詳細分析了傅柯的多個文本,進一步將之推論成一種永無止境的轉化(perpetual conversion)。這個過程無關時間及空間,要求個體不斷質疑和背棄自身的同性慾望,走向一個異性戀規範的理想,從而為信仰內的酷兒預設出一條永無盡頭、直線狀的「救贖」路徑,令人筋疲力盡。
同樣地,作者再解構了「家」的意味。書中引述TrueLove.Is其中一個宗旨是「Share real life stories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come out and come home」。然而,家究竟在何方?對於酷兒社群來說,在那個溫暖安全的歸宿表象之下,實質卻是一個規範性和反酷兒的場所,甚或是排斥那些曾經(或仍然)被邊緣化的人的空間。
除了理性知識之外,作者身為新加坡的男同志,語境回到家鄉,亦是酷兒社群一員,使其視點紮根於眼前活生生的現實。他對見證故事、訪談等數據分析通透,近距離將隱匿在關懷表象下的壓抑和傷害呈現人前。有別於一般的學術書籍,此書的字裡行間貫徹了一種情理兼備的人性。
香港的語境:另一話語權之爭
雖然作者的分析聚焦於新加坡的語境,但將箇中論述放到香港亦無不可,同樣的「線」也捆住了這個城市。近期,《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引起了一陣廣泛討論與爭議,最終在71名立法會議員反對下,以大比數否決的結果告一段落。然而,那正是話語權爭奪的鮮明例子。該條例旨在為同性伴侶提供法律保障與認可,卻遭到保守派及宗教團體的強烈反對。
與新加坡的TrueLove.Is類似,香港如明光社等機構亦積極宣揚反同性戀論述。某些組織嫻熟地利用一套特定的語言,將同性戀描繪成不道德的行為,有損公眾權益和社會價值,並試圖硬生生將輿論扭轉成「逆向歧視」的罪名。與此同時,他們高舉愛與關懷的宗教修辭,掩蓋了排他的意識形態。所以,他們所愛的到底是誰?
更甚者,草案辯論期間,部分議員所發表的駭人言論,進一步證明了掌握主流話語權的權力者,如何以語言為工具來鞏固異性戀規範,以及邊緣化酷兒社群。毫無疑問,語言在權力結構中舉足輕重,奈何在這些角力之中,性別平權議題更易淪為炮灰。
珍惜我們的語言
對於維持社會規範而言,無論在新加坡,還是香港,類似的話語策略都被用來製造與延續對酷兒社群的傷害。《Queer Correctives》一書(或是這篇書評),不是要試圖去灌輸或強加某些主義的思想,而是將討論帶回人性本身。
作者在書的結尾處提出了一個詰問:為何酷兒社群老是被強加了一種「自我辯解」的重擔?在潛藏於日常語言的暴力面前,他們總須不斷證明自己受傷的事實,更遑論既定制度上的不公,使不少人早已遍體鱗傷。
這不僅是受害者身份的問題,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們習以為常的語言,竟能被如此刻意地扭曲成傷害的路徑。
正如提摩希·史奈德的《暴政》一書中提到,我們必須對語言保持敏感和警惕。誠然,我們未必掌握充足的學術理論,去批判或解構那些看似中立的論述,但至少不要輕視語言的威力。在一片灰色地帶之中,語言會被當作武器,但同時也是我們唯一的工具去暴露那些不見於人前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