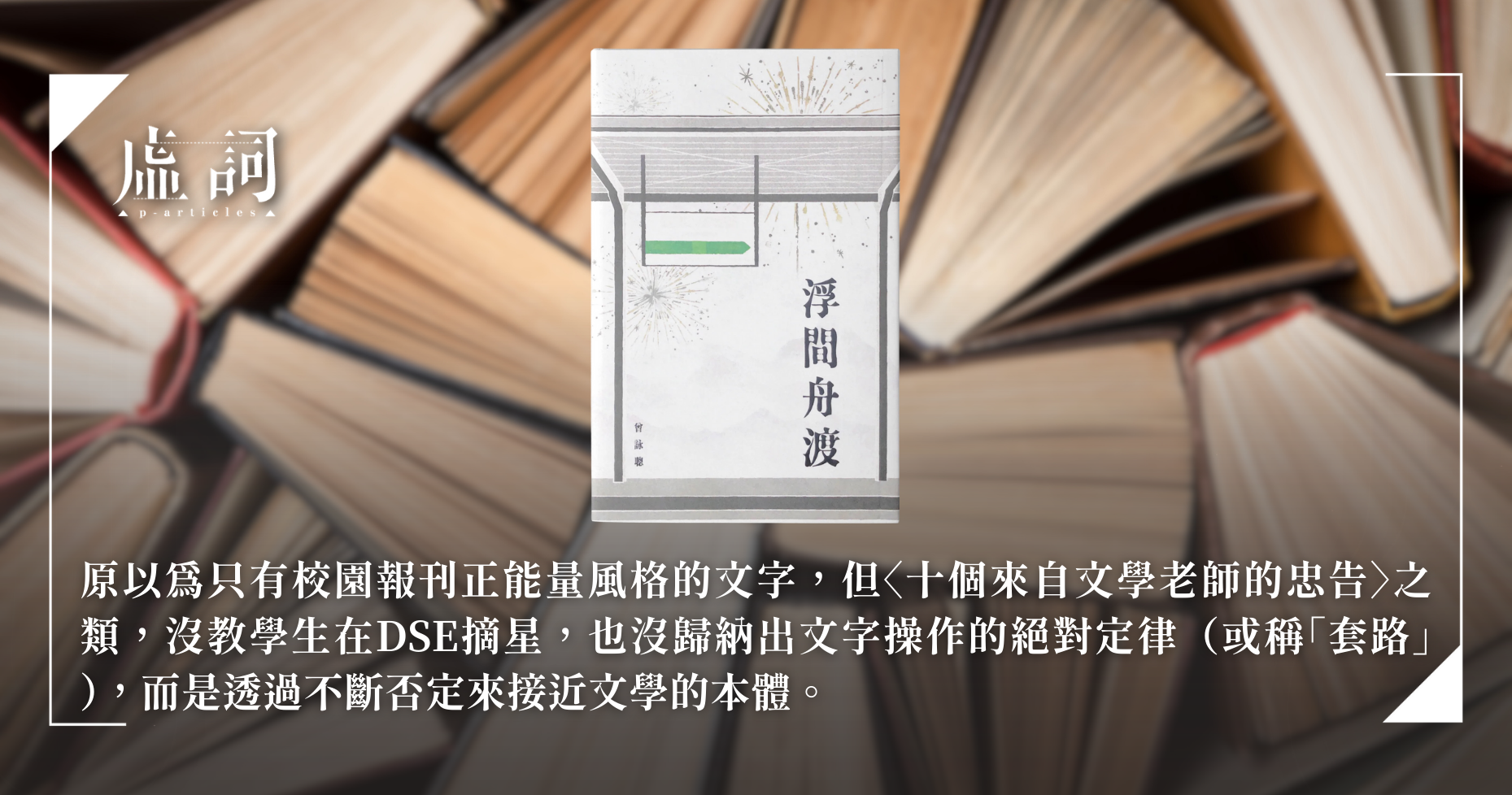【新書】曾詠聰《浮間舟渡》曾繁裕序——〈無限接近無限流動的清澄白河本體〉
那一瞬間
我希望我是他,這樣安安靜靜地工作,
像天堂一樣沒有干擾,讓黑夜無限延長。
我不斷閃過停下來跟他打招呼的念頭,
但我的靈魂說:「這是個奇蹟,
你闖不進去,因為你不是
也不可能是它的一部分。」
──黃燦然〈裁縫店〉
阿聰結婚的時候,給每位兄弟訂造西裝。於是,我在大華洋服半掩的門外,窺看穿涼鞋的老人獨自丈量剪接。牆上掛着不明的法國證書,時間在那寸光影停頓,但阿聰說與黃燦然的詩無關。
曾詠聰是詩人,但不刻意做有詩意的事情,因為他知道生活和文字是做給不同人看的。
難得他在接新娘時的「愛的宣言」非常濃情,但至「朝拍晚播」環節,宴客卻只見商業慣性操作與形式化的影音,常人難解的深刻,只作笑話剪去。
留下甚麼呢?他的散文集就是苦心縫合的衣裳。那麼安靜,那麼不用顧及喧鬧而膚淺的世界,那麼讓人耗費精神來品賞。
如果,這是評論,簡單一句「天橋巍峨,某些段落我沒有走過,那些決議築起天橋之城的官員,脫下西服又換上古裝,聽從誰的話串連六國遺下的城牆,不卑不亢,在時間裏立下一個更好流走的路徑」,我便可分析他如何延展意象(天橋→ 城→官員→城牆→時間的路徑),如何文白並置(把「天橋巍峨」、「不卑不亢」嵌進平易句子),又如何把主觀步移引向永恆視角。還有〈社區人與曼德拉〉那篇,可大言後設散文佈局之妙。然而,評論顯然不是閱讀《浮間舟渡》的路徑,也不是閱卷無數的文學科老師創作散文的目的,如他像北島《時間的玫瑰》般寫與詩人的交往,多於分析詩本身。「雜篇」部分,原以為只有校園報刊正能量風格的文字,但〈十個來自文學老師的忠告〉之類,沒教學生在DSE摘星,也沒歸納出文字操作的絕對定律(或稱「套路」),而是透過不斷否定來接近文學的本體。
「我站在這裏,又站在那裏,但我知道本體並不是我所能視的。」本集的第一篇第一段如是說。
康德為人的知識立下邊界,先於經驗或超出經驗的,我們永不能知。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不能知,不代表不能望,望而成詩成文,可藉無限內溯對抗無限隔斷。
幸福得多的碇真嗣在〈最後,我來到了灣仔西〉寫道:「我們不時出來交換回憶,因我們是回憶的本體」,回憶屬於過去,永遠無法同在,但文字的咒術使之揮不去。「我們幾個在薯粉店內催促訂單,店員衝口而出問:『你係邊個?』朋友回答說:『我係醬爆丸。』」〈天橋之城〉中那位順着語言的罅隙開玩笑的主體或許仍承載着薯粉店的回憶,但他與阿聰已永無法擦出當時聚合的花火。正如〈吟遊詩人的高光時刻〉止於分離和殘留的共有感受,無論如何執着,也只能像《追憶似水年華》般拉伸文字。
「浮間舟渡」,如阿聰解釋,既是日本地方名,又是「當下處境」和「不完美解答」的拼貼。學者曾言:「戀舊出於對當下不滿。」在苦沙彌的貓大寫距牠十數載的中學生活並引用許多經典動漫電影之外,似乎「戀日」也可讓牠逃離詩人共通的躁動。
沐羽曾引畢飛宇說:「日本不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對於當代世界而言,日本是一種形而上。」新宿、東本願寺、紀伊國屋書店、都電荒川線、東京灣……如李歐梵言張愛玲的香港是上海的「她者」,日本是踢過毽、興辦詩社、打過文史哲盃、在文學課得不到學生共鳴、與舊生聖誕聯歡、讓來賓扭新人閃卡的香港的他者,是抽象的、思辯的、象徵的、侘寂的、唯美的鏡,折射繁縟的原鄉焦慮。
或許「外篇」佔一半的E人並不知道,「Behind the scenes」的除了馬爾代夫小島不向遊客開放的部分外,還有他婚宴的晚上,一位女文友真如他命名上一本散文集的「千鳥足」,酒醉,因而步履搖晃,引人攙扶和記憶。或許,我們的本體都隨她搖晃,但各自攙扶和記憶的方式,都會繼續聚合,且共戒,且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