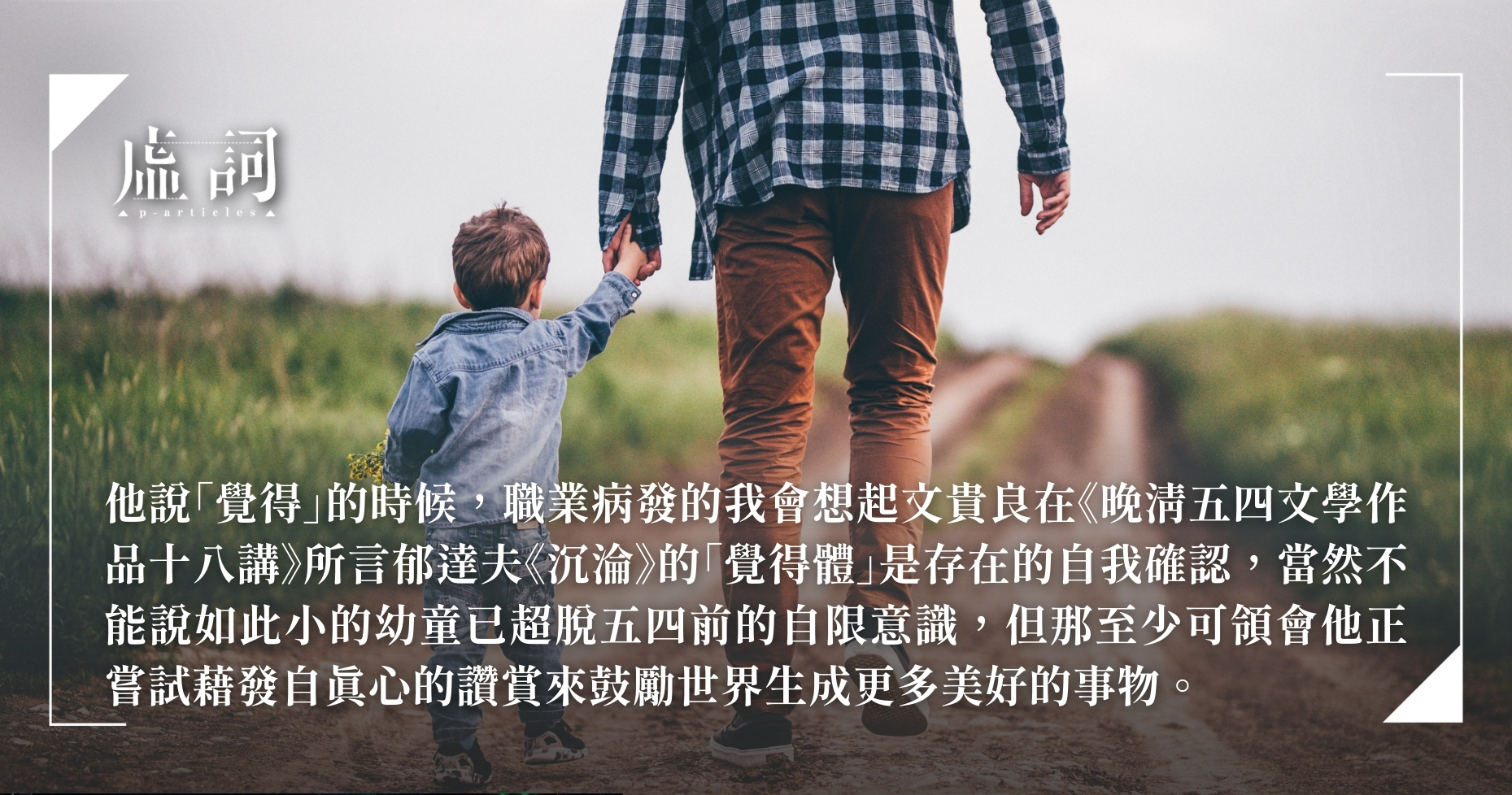獨力湊仔兩日談
中學選修經濟,學過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較優勢)的概念,意思是即使你做兩件事情都比別人好,也要選最有效益的一件來做,而非兩件都做。
菲傭姐姐快將回來,工作較彈性的我便做了兩天全職爸爸,先說結論,父母貼身教導兒女肯定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但無奈,返工比湊仔輕鬆,所以懦弱的我,比較之下,還是必須收回跟妻子說她工作、我靠她養的戲語。
第一天,像日常工作天般起床,吃早餐,然後打開手提電腦工作,因兩歲多的兒子可能忽然甦醒然後不可理喻地索要所有關注,所以需戰戰兢兢地趕快檢查郵箱、處理文書工作、寫一點文學。十時多,他醒來,呆呆滯滯的,替他換尿片、給大腿抹上潤膚膏、從額頭到脖子洗一圈,發覺他的下唇爆拆得現黑點,便問他要不要搽潤唇膏,「唔要,敦敦唔要搽潤唇膏。」給他照鏡後,我說:「你睇,唔搽就黑色一點點,唔靚仔,咁你要唔要搽?」掙扎一輪後,便把廁所的鏡櫃下找到的「Made in EU」、聲稱「organic」的潤唇膏刮去表面,再用洗好的手指點一些,往他的嘴唇輕擦。
接著,他popo了,雖然昨晚跟他講了關於父母送給Henry一個potty,讓他學習自行便便的故事,但他還是習慣不在有便意前先跟我們說。換了片,感覺多了一件可跟妻子炫耀的功績,接著便去廚房煮麵麵給他。我吃一點,他吃一點,然後請他換校服,他怎樣都不肯。「我唔鍾意返學。」他像極了從前懶惰而常被老師責備和討厭、同學側目和排擠的父親,所以父親很想很想迫他返學。
出於旅行一周過於興奮的後遺?出於身體不適?出於下午班難以調整的生理時鐘?出於幼稚園的黑暗面?在迫與不迫之間,父親跟他說:「爸爸媽媽返工揾錢錢好辛苦,希望敦敦可以返學啦。」然後先帶他往幼稚園旁的小公園去瀡滑梯,他好像有點生性,在尚餘十分鐘便開始上課時停下動作,讓我把運動外衣勉強套在他的厚衣物外,只是他希望保留小企鵝襪,作為老師的我便無奈把白襪塞回袋子,把白鞋直接穿上。
一點半至四點半,該是美好的工作時光,可惜時至三點,兒子的老師便致電給在Jolibee打字的家長,說他完全提不起勁,很攰的樣子,希望他早退。如此,功利的我便數算,這就虧了一百多元的學費。
敦敦的確很呆,在清晨六點的阿里山說我和妻子是「人渣父母」的時候,也沒這樣呆。出於承諾,看他從迴旋樓梯下來後,便帶他走訪了幾間藥房和連鎖藥妝店,但都找不到車車口罩,為了讓他好過一點,便去他認得的壽司郎吃烏冬。烏冬來的時候,他難得地快樂,露出牙齒跟我合照。隨後,他打翻了小碗的烏冬,但父親的心境非常平和,撿拾、清理、再餵他吃別的,叫他小心一點便好。
回程路很短,經過水果店,網上說蒸梨有益,雖然我近來回鄉的父親說很麻煩,「唔好搞」,但我還是買了四大個回去。購買後,稍算一下,一天下來,竟然隨隨便便就花了近二百元,若我是全職主夫的話,一個月的用度就六千元,還不計買餸錢和其他開銷,算是洗腳唔抹腳……
蒸梨其實很簡單,切頂,去芯,把肉刮碎,加入紅棗段和冰糖,蒸二十分鐘便可,連皮的效果更好,反而其中一個為了兒子方便而去皮,卻蒸得不夠透。
「敦敦覺得好好味。」他說「覺得」的時候,職業病發的我會想起文貴良在《晚清五四文學作品十八講》所言郁達夫《沉淪》的「覺得體」是存在的自我確認,當然不能說如此小的幼童已超脫五四前的自限意識,但那至少可領會他正嘗試藉發自真心的讚賞來鼓勵世界生成更多美好的事物。
翌日,兒子九點便起床,殺正工作得興起的父親一個措手不及,又是換片、換褲之類的操作。因為聽他有一兩聲咳,便打算給他吃一服妻子買的猴棗末,由於兩服價值三百幾,所以把它倒往水裡、混和、餵他的時候都小心謹慎。猴棗末其實無甚味道,但混上水就像雨後濕泥,我說這是朱古力,但他硬不肯試,而他想把杯子撥開的手總讓心臟離一離,「呢個猴棗好貴㗎,爸爸媽媽細個病嘅時候,都無得食呢個。」他又再次展現人性光輝,但只半秒,就是嘴唇輕淺接觸、吸了一點點後,便爆喊,不斷用手抓舌頭,只能放棄。
及後,打開雪櫃,靈機一觸,便把紙盒鈣思寶取出,那是兒子渴求的飲品,為了把效果加強,第一次撲過來的時候,正飲的我把他推開,說食粥後才讓他喝,他唯有說:「敦敦大個先飲得。」然後,在我為煲粥切菜的時候,他一直在廚房騷擾,推起洗衣機蓋、撥動大片的錫紙擋板、觸碰危險的煮食爐,幸好,有個小機會,他離開了,我便把暖水浸著的紙盒取出,剪掉盒邊遠離飲管口的一隻耳朵,然後把泥水倒進去。盒內的液體還有一半,我有點害怕兒子會喝不完,但在他再次發現鈣思寶,我說「唔好比媽咪知」之後,他便用力吸吮吸吮,搖勻幾次,他再吸吮吸吮便光了。或許是報應,他接著便不吃煮好的粥,說要吃麵麵,麵煮出來後,又一口都不嚐。
「爸爸煮嘢好辛苦,又要洗,又要切,又要煮,你點可以一啖都唔食?幾唔好食都要食啲,身體先會好。」兒子凝視著面前的麵麵,我不斷問他要不要吃,心裡默禱,他都說不,我又說晚上再蒸梨給他吃,他都不願意。對於這個從前的自己,真的要放棄了。但,冷戰過後,忽然,他竟然妥協,吃了幾口,那一刻,感覺彼此的關係進入新境界,那就是我不再做只會順從、把兒子當玩具的父親,而是相信他的理解和思考能力足以在嚴肅的情況下讓他分辨對錯。雖然最後麵麵剩下許多,但我還是稱讚他。
接著送他返學,他很願意穿衣穿鞋,也不用先到公園去。送到幼稚園,他因不捨得父親而大喊,老師自然地把他接去,努力哄氹。我說:「放學帶你去搭巴士。」然後,待他乖巧完成三小時課堂後,便跟他乘K12往大埔墟火車站。痛苦的是,回去的全程,他都像小樹熊一樣,說:「爸爸抱。」「爸爸隻手就斷喇。」他還是不斷地上上落落。
這次,我還原了從前貧窮的自己,只搭一程車,然後買十元一斤的西洋菜苗,跟他吃十三蚊四條的腸粉時並沒點別的,整天只花$27.5,但快樂沒有減少。
兒子已經累極,對沿途的遊樂設施不甚依戀,回家後便睡在我旁,我們同蓋一張被子,直至妻子回來。如此「窮富翁大作戰」式的體驗便告結束,當年紀錄片拍攝的那些富翁仰望到貧富間牢固的高牆,然後幸然回歸他們覺得理所當然的生活,如今,我更深刻地景仰的Catherine已飛回香港,在敦敦抱她的溫馨時刻過後,她說她的小兒子在離別時哭得非常大聲。
文章本來在上一段結束,但翌日,婆婆到來,敦敦對父母都不甚理睬,母親便說:「邊個返工揾錢啊?」原以為與兒子感情升溫的父親回應:「揾錢無用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