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所不X──讀杜家祁《我在/我不在》
書評 | by 洪慧 | 2019-0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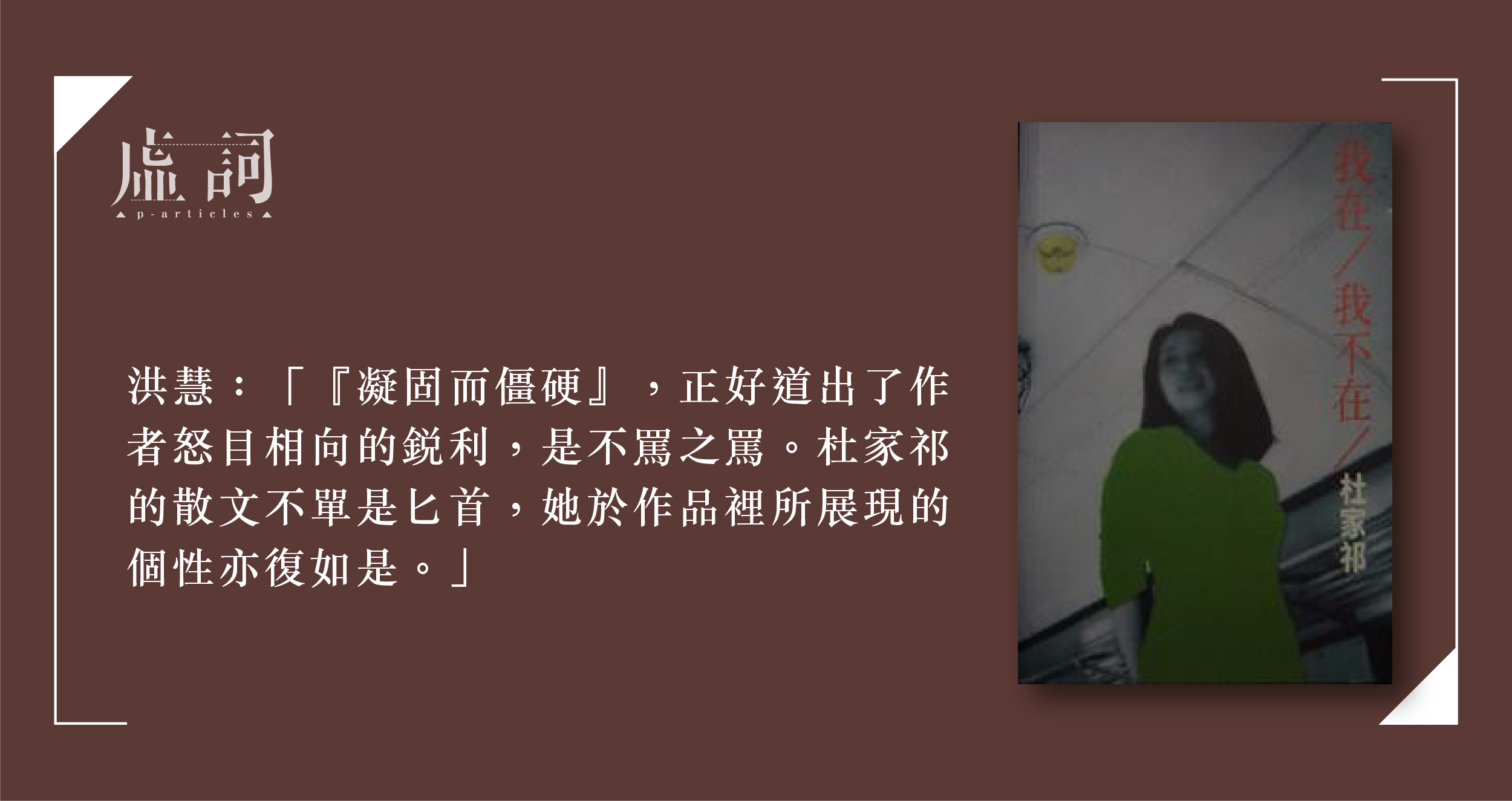
洪慧評杜家祁-09.jpg
《我在/我不在》是杜家祁迄今為止唯一一本散文集,於1999年出版。其詩〈女巫之歌〉,風格凌厲,孤高決絕,絕對是香港詩歌裡極為優秀的作品。杜家祁的散文亦非常出色,作品收於《香港後青年散文集合》。其散文同樣風格凌厲,對各種不公不平之事,時而橫眉鄙夷,時而怒目瞪視,極具個性,其文章亦時時透露出她對語言文字極為敏感巧妙的理解。《我在/我不在》,恰如《女巫之歌》,亦未見有評論詳加分析。當然,杜家祁可能是不太在乎的。
我喜歡看杜家祁罵人,迂迴之中,卻又直刺要害,她罵人時,眼神中總是帶有奇異的不屑與玩世不恭的表情。與書名同題的作品〈我在/我不在〉是極堪玩味的作品。文章寫的是九七回歸。題目本身就透露了強烈的政治評價。「我在」,就是作者作為香港人的一份子,當然是身處回歸這件歷史事件當中。「我不在」就是指作者雖然是香港人,但卻被中共政權和港英政權剝奪參與討論和決定自身前途的權利。因此散文開首一句便是:「我在歷史的現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我在香港中環的皇后廣場。」然而這個回歸儀式並不屬於杜家祁和所有香港人。作者在廣場駐足聆聽一個工會領袖的演說。此處人物描寫極好。
他說民主、自由、人權,如果我們不爭取的話,就不會有。像許多這類型的演講一樣,他數度問現場的觀眾:「你們說是不是?」
許多人在台下回應:「是。」
也有人大聲回:「不是。」
誰說「不是」?她坐在水池邊,和一大群洋男洋女在一塊,畫了一個不算清淡的妝,穿一件低胸緊身上衣,上半部乳房兩個半球呈現在衣服之外。我站在她旁邊,望下去可以看到一個相當旖旎的畫,可惜我並不覺得欣賞,當然那是因為我也是女性的原因。
這個性感的女子,對民主自由的態度就像只顧掙錢的中產階層,因著香港有了社會地位,經濟基礎。可能是祖父母輩在香港掙錢,辛苦積蓄,然後得以出外留海的香港青年,偏偏對民主自由嗤之以鼻。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當其他人投身運動,她尚且譏笑不屑,自以為超然物外。換一個角度說,作者寫這個女性也是非常細緻。性感女郎在所多有,隨處可見,一般人早就見怪不怪。作為男性讀者,此段文字如此客觀細緻地描寫赤露的乳房,還要穿插於嚴肅的政治演說之間,寫得如此反高潮,其技巧也是很值得欣賞。當然「旖旎」還「旖旎」,杜家祁下一刻就不留情面地「罵人」了。
在我為將來擔心的時候,在我聽演講聽得十分感動的時候,她的戲謔就像打了我一耳光。
一個洋漢子趨前用英文問她台上的人說些什麼,她用英文回答:「都是甚麼自由、民主那些廢話,你不會想知道的。」
我瞪著她,她向我擲來一個友善的微笑,她友善的笑容在她臉上漸漸凝固而僵硬。
我受不了這樣的尷尬場面,掉頭走了。
這段極精采,精采絕倫。讀者諸君如果是幸運的斯文人,也許一輩子都不會遇上這種事,就連口角衝突也未必敢回敬對方。值得欣賞的,不單是杜家祁在這裡的筆法,更是她不平則鳴的態度。書讀多了,有時我們反而會過於文明怯懦,漸漸不願與人有衝突,總要保持體面。縱使對方如何無理過份,知識份子有時會想,何必一般見識。假如看君曾對陌生人怒目相向,你就能體會目光瞪視的攻擊性。不單對陌生人出言駁斥需要勇氣,怒目圓睜同樣如是。「我瞪著她,她向我擲來一個友善的微笑,她友善的笑容在她臉上漸漸凝固而僵硬。」洋裝女子其實也自知失言。然而二人萍水相逢,曉之以大義,跟對方講民主自由,也只是徒勞。「凝固而僵硬」,正好道出了作者怒目相向的銳利,是不罵之罵。杜家祁的散文不單是匕首,她於作品裡所展現的個性亦復如是。
〈我在/我不在〉的重要性,更在作者於九七回歸前,以定居香港的知識份子這個身份,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
我一直留在這裡,十幾年了,沒有走,為了安居樂業。我相信香港是有史以來,中國人最好的一個社區,我卑微的願望只想這樣一生一世,我並不想見證什麼大時代,如果大時代表示動亂的話。
說香港是最好的華人社區,當然可以從各種方向進行嚴謹的討論。但這起碼足以反映了其時香港人的自我觀感。我們當然不能否認殖民地政府是以殖民宗主國利益為依歸的政府。但從「安居樂業」而言,九七之前的香港無論是經濟和社會環境都比中國內地超前。杜家祁這種說法其來有自。早在1938年,穆時英便在〈英帝國的前哨:香港〉說,在抗日戰爭裡,香港「變成了全國唯一的、最安全的現代都市」。杜家祁這種對香港的強烈肯定與自豪,可以對照薩空了的講法。薩空了曾於三十年代末短暫居留香港,並創辦《立報》。他甚至預言:「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屬於香港」。上述引文,當然亦有其卑微處。背後的思路,陳冠中亦有在《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有所發揮。「歷來很多移民都是為了逃避大陸的動亂而來到這個相對法治自由安定的殖民地,然後求發展。」每當內地社會動亂,香港人口便會隨之驟升,迎來一次又一次的機遇。〈我在/我不在〉可以說是同時深刻反影映了香港人這兩種心理面向。
論到罵人,最引人入勝的,還是〈問候你的母親〉。十多二十年言傳身教、躬行其道,對於問候其他人老母,自以為早已瞭然於胸,但這篇作品真可謂拓寬了我對語言的想像。
寫這篇文章時,意外地認識了一位從荷蘭來出生於南斯拉夫的女子。她會說南斯拉夫話。我問她波斯尼亞的事,她說很難說清楚,那裡面牽涉了政治、經濟、宗教、種族。小小的地區,便有三種宗教:回教、東正教、基督教。
我問她南拉夫的粗話,她說南斯拉夫的粗話可厲害呢!
「也會X別人的母親嗎?」我問。
「豈止,無所不X,別人的父親、兒子都X,連別人的神都X!」
操人家的母親,其實也是鬆懈平常。操人冚家,稍有新意,亦只是推而廣之,順理成章。連看不見,摸不著的「神」,這麼一個不存在的概念都能操,真是大開眼界。操別人的神,確實比操別人的母親更為侮辱。神代表了一個社會民族最神聖的象徵,所有道德禮俗都源於此。連對方的神也能肆意踐踏蹂躪,不單羞辱對方,更連帶羞辱對方所屬的整個社會民族,羞辱之處,無以復加。這個級別的粗話,可謂反映了當地的宗教衝突,可謂勢成水火,隨時要來個你死我活。
〈問候你的母親〉不單從語言,也從戰爭講。杜家祁援引女性主義學蘇珊.布朗米勒寫的《違反我們的意願》,配合伊朗侵略科威特、前南斯拉夫地區波斯米亞切放軍人的暴行,由是指出「男人視強暴為征服的必然伴隨物」。強暴不單是上級對士兵的獎勵,更是打勝仗的戰術,是種族清洗的行政命令。
杜家祁對這種狀況的總結可謂觸目驚心:
「這種意識的演進是這樣的:從「X你娘」進化到「X你,讓你成為我兒子的娘。」
事實上,對「操人家老母」的探討,在現代文學裡可謂博大精深,是一條隱而不宣的潮流。1925年,魯迅寫有〈論他媽的〉。魯迅從古籍經典探討「他媽的」之起源流變,由《左傳》到《世說新語》到《廣弘明集》,精彩絕倫。魯迅認為第一個發明「媽的」,應可納入天才之列。他更從文學翻譯切入,指出「你媽的」一詞,在日語只能譯為「你的媽是我的母狗」、德文譯作「我使用過你的媽」,只有中文「你媽的」簡潔有力,配稱之為「國罵」。再如比黃碧雲著有散文集《後殖民誌》,其中一篇名為〈我身,我說〉,則從女性身體的角度去討論。
「瑪莉說,操,你媽操的,你媽操的種族主義者。」
答案是:你都沒有陽具。你是女人。你怎麼操。這樣他們就可以說,佛洛依德是對的,你們都沒有陽具,你們妒忌。
那個操的國度,操的語言,從來不屬於我們。
黃碧雲自然又是另一種驚世駭俗。她從女性身體出發,指出粗言象徴男性制宰女性的社會權力,姿態激越挑釁。與杜家祁逐層指述的筆法又截然不同。對「操人家老母」的探討,每人各有側重,各自依循著他們所關懷的面向發展。魯迅關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黃碧雲關注的是女性身體。杜家祁關注的是語言與行動結合的大規模壓迫。當杜家祁除了以散文探討香港的歷史政治,亦兼及各種文學藝術如電影、小說、詩歌。她寫崑南、鄧阿藍、也斯,還有伍迪艾倫。看君自可各取所需。然而罵人的重要性,在於不平則鳴,看一個作家罵誰,怎樣罵,雖不免以管窺日,亦有略知其個性一二之功。1927年,梁實秋出版散文集《罵人的藝術》,其同題散文劈頭一句便是「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不罵人的人」。他列舉出十種罵人的策略,以為務必「出言典雅」,那又是另一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