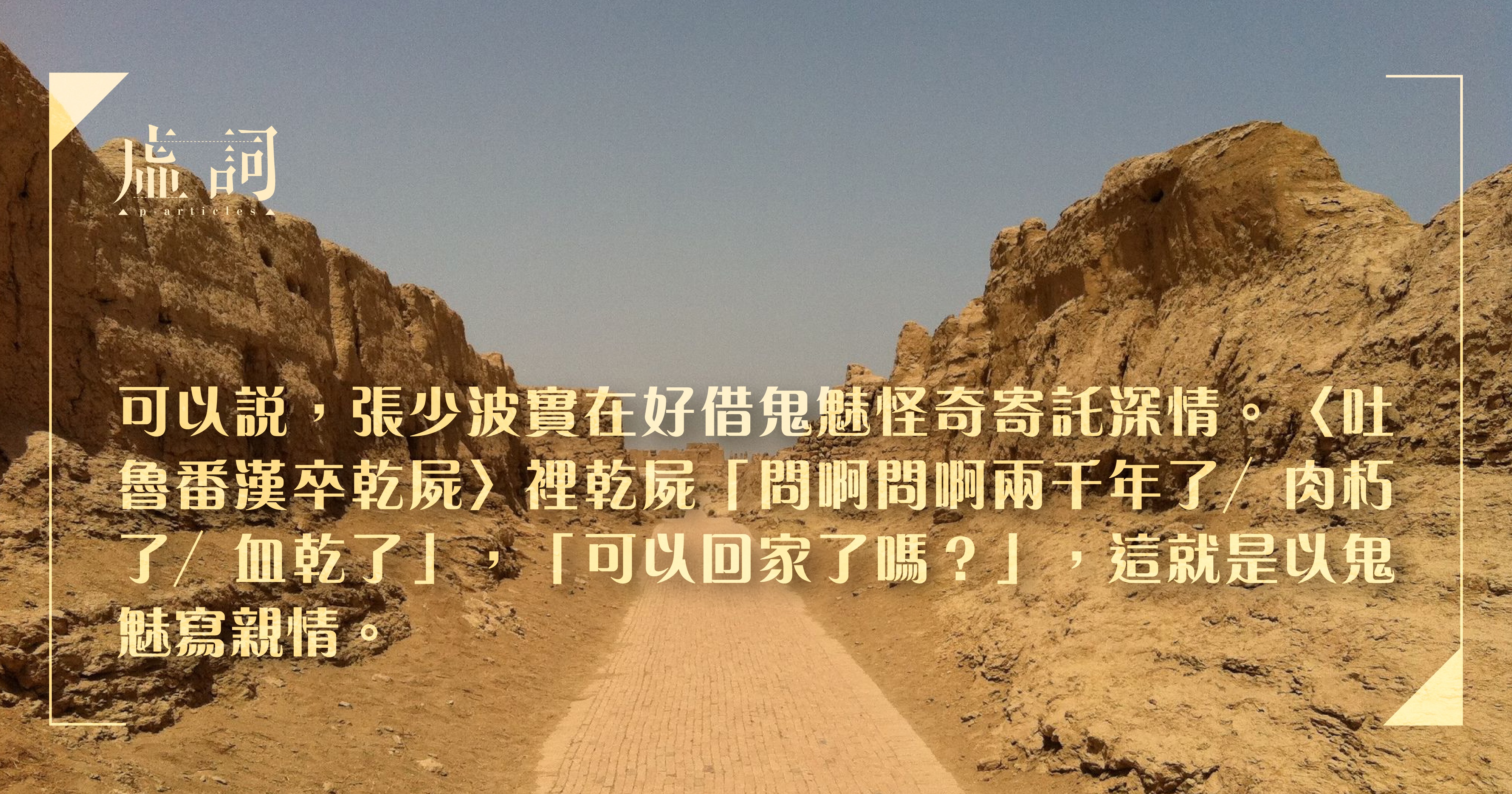鬼魅怪奇託深情———讀張少波《當隔世的繩斷了》
書評 | by 洪慧 | 2020-09-10
張少波是呼吸詩社成員。呼吸詩社於90年代曾出版《呼吸詩刊》及呼吸叢書,成員包括陳滅、杜家祁、小西等。相比起上述社員,張少波則是較少人認識。他著有一本不曾公開發售的詩集:《當隔世的繩斷了》。詩集只是以影印、手作方式釘裝。詩作質素雖有參差,但亦不乏個人風格突出的作品,值得讀者揣摩玩味。
張少波的詩不時會透出詭異氣氛,用字血腥,鬼魅森森。且看〈無題〉。
〈無題〉
就像一張新剝的人皮
晾在暗濕的地牢
誰,將我的尊嚴釘死在牆上
將我的頭顱四肢垂掛如腌菜
基督啊,我能聽見
你懸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一九九二初稿
一九九三.二.十五定稿
這首詩是詩集開卷之作。全詩所用的意象和比喻透出血腥暴力之意。作者將自己的尊嚴比喻為「新剝的人皮」,「人皮」與「暗濕的地牢」,恰如刑房、牢獄,構成詭異危險的畫面,帶著恐怖、死亡、罪惡的氣息。人皮從身體被剝離,即是說自己的尊嚴被人踐踏殆盡,而且被放逐到無人關心之處。「將我的頭顱四肢垂掛如腌菜」顯示出作者形同身死,四肢頭顱已如死屍般垂掛。「腌菜」一詞就是指他的屍首已經身死多時發出惡臭,如同低賤食物「腌菜」般無人理會。尊嚴被剝成人皮而身死,還不夠,還要「釘死在牆上」虐待、懲罰。「釘死」一詞,乃令作者引出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因此乃有最後兩句詩句:「基督啊,我能聽見/你懸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這首詩令人聯想起張景熊的詩作〈給討厭的傢伙們〉。這首詩同樣是其詩集《几上茶冷》的開卷之作。張景熊在詩裡並沒有解釋他為何討厭那些傢伙。他也沒有點明那些傢伙是誰。他是著力刻劃討厭的情感。而張少波在此詩亦是只刻劃尊嚴被踐踏的痛苦之感,他也沒有多費唇舌去交代是什麼人什麼事令他如此痛苦。〈無題〉與〈給討厭的傢伙們〉的處理是相通的。事實上,一些硬性的資料,背景起因,細緻敍述交代前因,有時反而會令詩作變得瑣碎,令詩作無法好好發揮其感染力。〈無題〉作為《當隔世的繩斷了》的開卷之作,可見作者對詩藝確是有一番認真的揣摩探索。
「人皮」這個意象值得進一步探究。古典小說《聊齋志異》有〈畫皮〉一篇,記有惡鬼畫人皮而偽裝美女。又有諺語「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至於香港詩中的「人皮」意象,在張少波之前的詩人,我暫時未有找到先例。可以這樣理解,張少波以「人皮」意象去發展這首詩作,即使不是香港新詩第一人,也是罕有的處理。起碼在張少波之前,其稀有和創新,在香港詩裡是有其價值的。又此詩並不止於「人皮」,而是由「人皮」、發展出「地牢」、「釘死」、「頭顱四肢」、「十字架」,構成一種酷刑、虐殺的環境。這是可以和處理牢獄、酷刑等詩對讀互見,戴望舒:〈獄中題壁〉、癌石:〈警察〉等皆是此中例子。
另一首值得留意的是〈遊北京大學被拒〉。詩歌雖短,亦隱然見其氣性。
〈遊北京大學被拒〉
步槍連風也扣住了
門裡的千荷不再搖曳,仰著臉
一莖蓮蓬舉著
如沉默的拳頭
一九九二年九月記
同樣,為什麼作者遊北京大學會被拒呢?詩中沒有詳細明言交待。但意象上的蛛絲馬跡可以讓我們找到一些提示。「步槍連風也扣住了」,「步槍」就是借代內地軍警。1992年9月的北京大學,當是發生了涉及政治問題的事件,因此軍警就將所有可疑的人扣查。既然連「風」也不放過,張少波這個香港來的外人自然也就被拒之門外了。「門裡的千荷」也就是北大學生,他們都噤若寒蟬,「不再搖曳」的荷花。「仰著臉」一句,極妙,顯示了扣查的命令由上而下壓落去,學生只能在低處「仰著臉」接受。然而千荷之中,亦有「一莖蓮蓬舉著/如沉默的拳頭」,此處就更為微妙。張少波將蓮蓬寫成「沉默的拳頭」,可以解作無聲的反抗,敢怒不敢言的無奈。但同一時間,在內地的高壓政治環境,這又可用近代中國獨有的政治語言修辭去解釋,「堅持維護黨中央的政策」。從這個角度去詮釋〈遊北京大學被拒〉,也就更能看出內地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複雜關係。人民既被逼害,同一時間又必須參與維護政權的穩定。這種精神分裂的狀態,值得當下香港人理解。全詩雖短,但「步槍」這個意象非常醒目,亦是與〈無題〉的酷刑、虐殺等意象相呼應。「步槍」之後的「千荷」、「蓮蓬」,則是古典文學常見的自然意象。可以說,這是一首嘗試結合古典與暴烈的抗爭詩作,在香港詩歌裡,往前可以與溫健騮作參照,往後則可以與廖偉棠作參照,可謂值得留意。
1997年,黃燦然編有《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他在序文中便指出,張少波多有「回望神州」之作。「張少波很多詩都是遊記,尤其是大陸遊記:對一個龐大而陌生的祖國的好奇,對生活其中的人民(他的陌生的同胞)的感觸,在某些情況下是懷著一種同情──也是少年人的家國情懷。」 黃燦然之說固然妥當,但這裡亦可以稍作補充。張少波也不是一味祖國山河壯闊。譬如〈遊北京大學被拒〉的政治取態已是很好的反証。再如〈吐魯番漢卒乾屍〉亦與一般庸俗左派香港詩人書寫祖國的角度大有不同。
〈吐魯番漢卒乾屍〉
這一矛刺得太深太急了
那麼多的話
要向父母妻子交托
都來不及了
都刺碎了
都碎成燙熱的沙,等候
每一陣東風走過
都幽幽地問
可以回家了嗎?
問啊問啊兩千年了
肉朽了
血乾了
眼睛望空了
唯獨扭曲的嘴巴
那痛苦,仍不曾合上
一九九三.七.三十一
此詩並不採取歌頌祖國山河之法,又或者以祖國山河的壯麗去批評香港的罪惡。他反而是寫中國歷史一個擺脫不了的惡夢:國力窮弱便向外族採取和親之法,當國力強盛便窮兵黷武,肆意開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因此也就有這個漢人唐軍死在吐魯番。乾屍這個題材,同樣在香港詩也是頗為稀見。張少波在〈無題〉寫過人皮和酷刑,如今就在〈吐魯番漢卒乾屍〉詠乾屍。在另一首詩如〈空宅蜘蛛〉說「會是誰淒淒唳的靈凝結/五百年不隨清風散去」,這是寫鬼魂。在《當隔世的繩斷了》則寫自己是一口古井,「等你垂下/接續好了的長繩」,用連著長繩的木筒取水,再續隔世情緣。可以說,張少波實在好借鬼魅怪奇寄託深情。〈吐魯番漢卒乾屍〉裡乾屍「問啊問啊兩千年了/肉朽了/血乾了」,「可以回家了嗎?」,這就是以鬼魅寫親情。以死屍寫親情,與香港詩人如關夢南以生活瑣碎寫親情,鍾國強以屋子寫情親,又是截然不同,另開幽徑。
《當隔世的繩斷了》不乏描寫愛情傷痛之作。情感固然強烈,但亦有粗糙之弊。比覺值得討論的是〈腹痛〉。
〈腹痛〉
腹痛如絞,哎
是否有一件陳年的事
在心室七瓣重重包紮內
仍燙如火,仍止不住
往下墜,往下墜
穿破這顆心
如岩漿注入柔腸
那千迴百結的古道
向最深最幽秘的記憶
炙去
一九九三
雖謂腹痛,緣起其實卻是心痛。因為「有一件陳年的事」,讓他心痛難當。簡單來說,就是情人心事。我們推斷這樁心事是情人心事,是因為「柔腸」二字。既是舊日情傷未癒,卻又無法捨割,於是便「重重包紮」在「心室七瓣」。然而這樁心實在太重太火燙,於是一直「往下墜」,由心而到柔腸。柔腸千迴百轉,小腸至大腸,最後的處所本應是肛門,排出體外,像排出糞便般忘記情傷。偏偏張少波的處理卻是「向最深最幽秘的記憶/炙去」,也就是逆流向上,反而流向負責管理記憶的腦部。姑且名之曰:越諗越上腦。這是此詩出人意表之處。循此可見,張少波的詩無論是寫政治、愛情甚至痛苦悔疚,抒情成份甚重而且偏向激越。概而言之,張少波這本結集雖然是大學畢業前後的作品,但當中個人風格已甚明顯,如有機會發展下去,當能更形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