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 RESULTS FOR "鄭點"

詩四首:〈秘密〉、〈四幕日常〉、 〈真空〉、〈無雲——記慈山寺行〉
詩歌 | by 嚴瀚欽、鄭點、鄭偉謙、任弘毅 | 2023-09-15
木箱子依舊在肩膀搖晃 你推車遊走的路線 有白色粉末飛揚 九龍城,過於潮濕的春天

《烈火青春》詩輯:永遠張望未來,今夜卻只有你
詩歌 | by 李顥謙、璇筠、鄭點 | 2023-04-28
譚家明執導的《烈火青春》,相隔41年最近再度於大銀幕上映,導演重新剪輯的4K修復版本,讓觀眾重溫戲中兩對男女的青春殘酷,愛慾橫流。李顥謙、璇筠、鄭點分別寫詩,組成《烈火青春》詩輯,烏鴉飛回尚未破滅的黑房,代替流離的觀眾,親吻曾經被禁的月色與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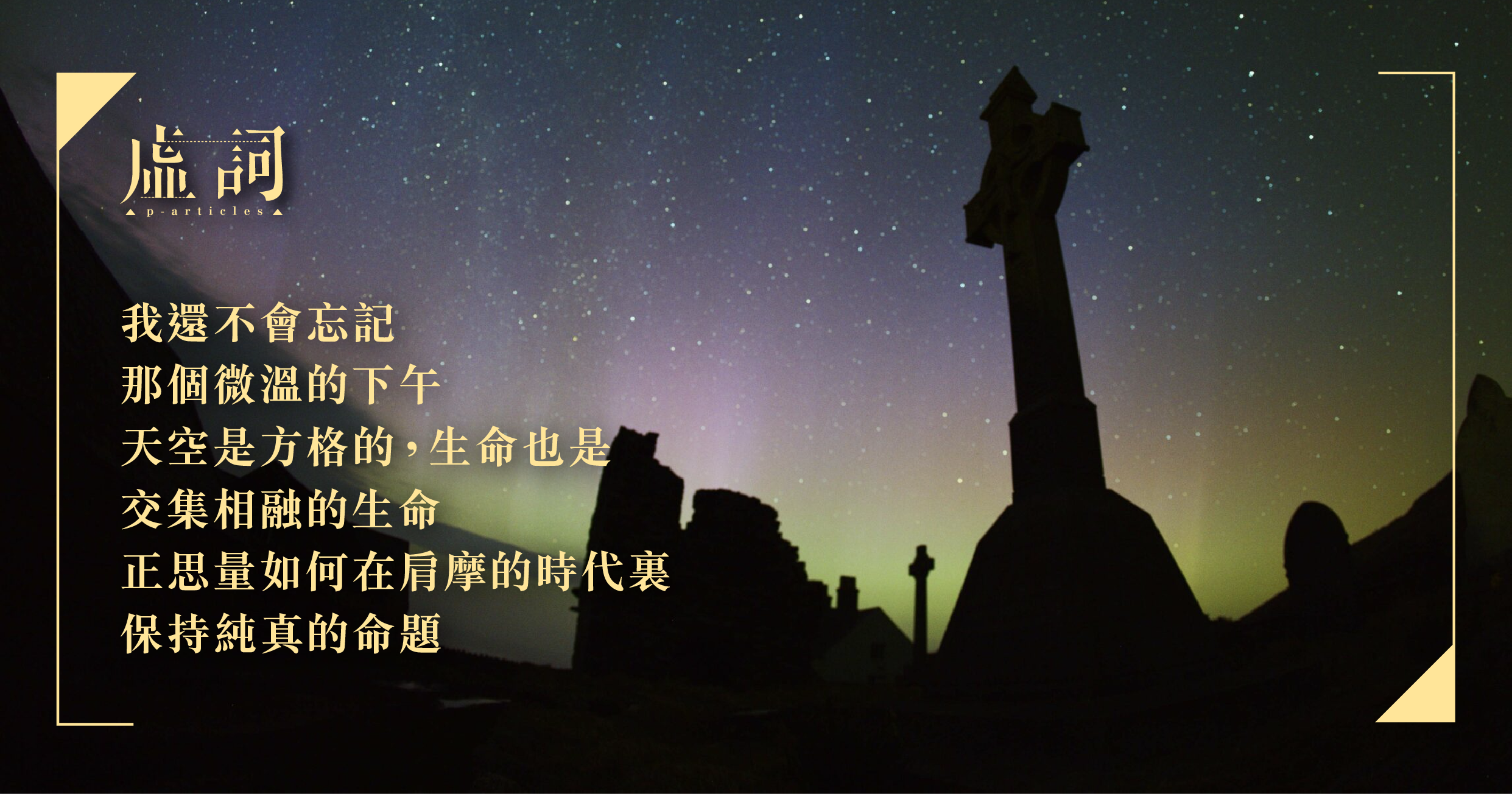
詩四首:徐竟勛 X 任弘毅 X 鄭點
詩歌 | by 徐竟勛、任弘毅、鄭點 | 2023-03-04
我還不會忘記 那個微溫的下午 天空是方格的,生命也是 交集相融的生命 正思量如何在肩摩的時代裏 保持純真的命題

角力
小說 | by 鄭點 | 2022-12-17
那天晚上有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他問我叫什麼名字,明天有沒有空去陪他喝一杯咖啡。他說話時直勾勾盯著我腿上的字,好像在想那是哪一個國家的語言。我說我叫Bershka,我沒有空和他喝咖啡,我明天要回西班牙了。我猜他已經有妻子,他的衣領散發著淡淡的洗衣粉味,襯衫上有一處小洞被細緻的針線遮住。黝黑的無名指上有一環白色的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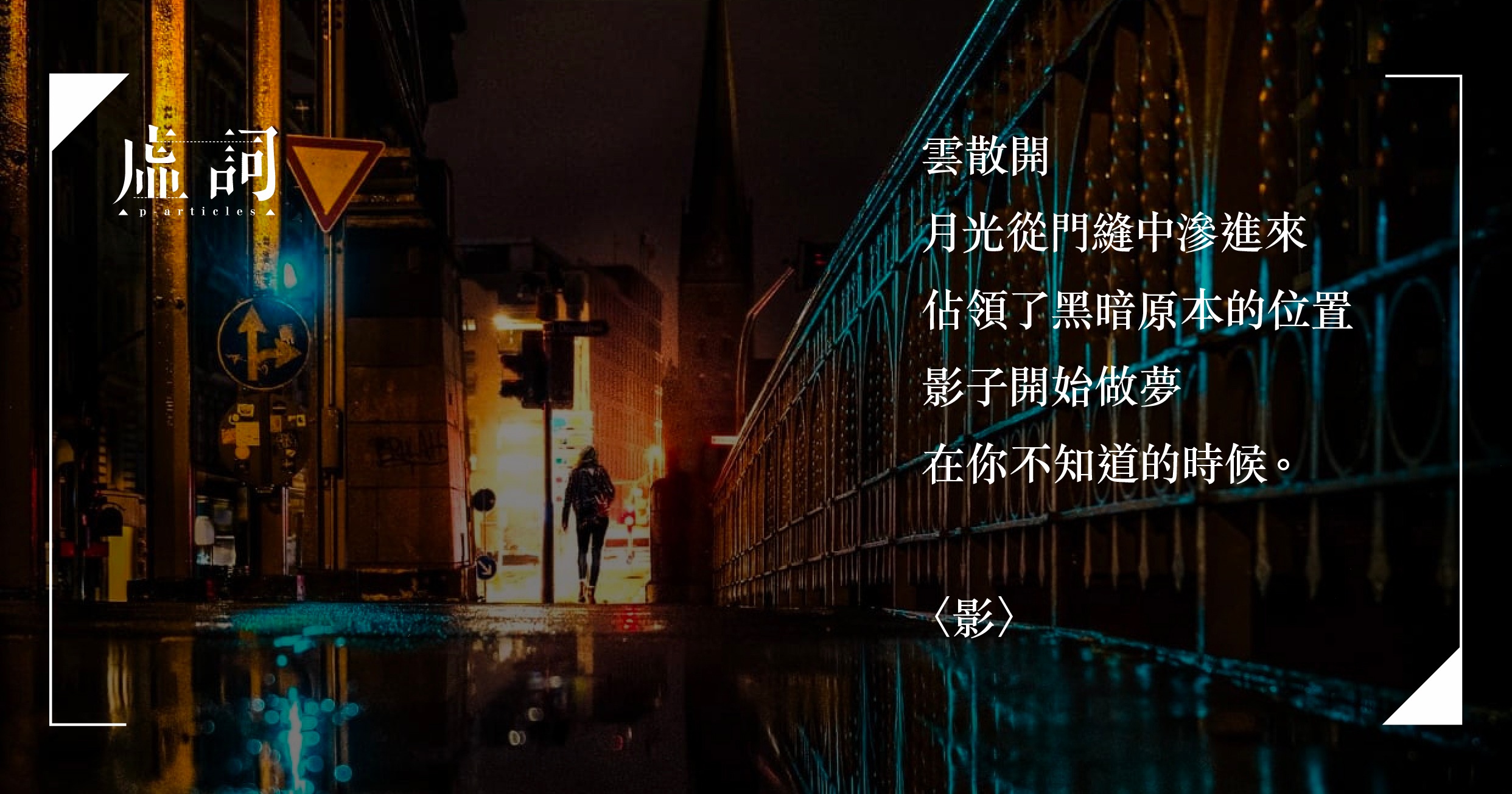
詩三首:鄭點 X 周丹楓 X 沁谷
詩歌 | by 鄭點、周丹楓、沁谷 | 2022-07-29
鄭點、周丹楓、沁谷分別傳來詩作〈啞縣〉、〈影〉與〈第一千八百二十六天〉。風吹散了幼嫩的髮絲,掠過襟翼的聲音滑進了耳道,下一個五年,你我會否仍然依舊?

侵略詩輯(三):血流激盪整夜,堅信還有下一個黎明
詩歌 | by 羅貴祥、彭礪青、鄭點 | 2022-03-10
烏克蘭局勢變化莫測,此刻難料下一個剎那,傷亡與囚禁,逃離的倉皇,羅貴祥、彭礪青、鄭點寫詩感懷。生命剩下唯善唯惡,終有一天,我們會抵達他們的海港,彼此問起健康和近況,穿越密集的砲火迎接明天。

「排隊」詩輯:打了針就可以自由吃喝
詩歌 | by 淮遠、鄭點、獱獺笑 | 2022-02-20
防疫升級再升級,排隊強檢成為當下香港的常態。偏偏正是天寒地凍冷雨交逼之際,為了「證實」自己健康之軀而令身體受害,其中的荒謬和非人性化,連一向權威的醫療體系都解釋不了。三位詩人淮遠、鄭點和獱獺笑各寫詩句,語帶哀憤,或是嘲諷,觀照今日各地各區的民間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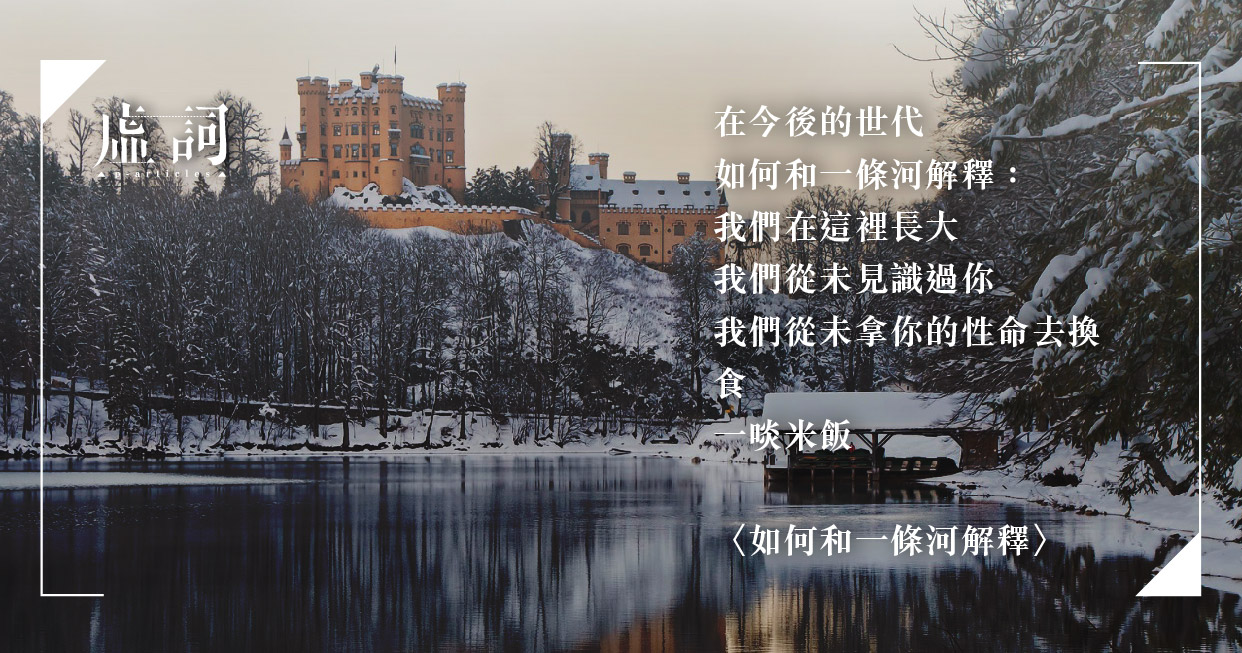
詩三首:鄭點 X 無皮蛇 X 李曼旎
詩歌 | by 鄭點、無皮蛇、李曼旎 | 2022-01-21
新的時代已來,走進誕辰,竊喜新世紀伊始。鄭點、無皮蛇、李曼旎以詩作迎接新的世界,沿著邊緣裁減,裁減出一個更具體的深淵。

詩三首:夕下 X 鄭點 X 驚雷
詩歌 | by 夕下、鄭點、驚雷 | 2025-04-15
夕下、鄭點、驚雷分別投來相當有個性的詩作,夕下的〈麻醉人生〉,既寫烈酒的醉中共舞,也寫濃縮咖啡的麻醉,一種「用清醒麻醉」的生活方式。驚雷在〈你可以殺了我在盧旺達的兒子〉寫的「殺」念,或許跟鄭點的〈擁抱拆毀的永定門〉寫國家的「拆」有異曲同工之感,「把向生的媚態,和死前的無奈,通通都跌得雞零狗碎」。

致阿富汗詩輯:讓我們在這恐怖的日子裡一起失眠
詩歌 | by 璇筠、呂永佳、熒惑、鄭點 | 2021-08-20
阿富汗局勢急轉直下,大量國民欲逃難出境,更有人在逃亡的軍機外墜下,場面恐怖,亦教人難過。璇筠、呂永佳、熒惑、鄭點以詩作回應,用文字去抵抗,在這恐怖的日子裡一起失眠,贈送這人間一小束白花。

詩三首:李嘉穎 X 鄭點 X 驚雷
專題小輯 | by 李嘉穎, 鄭點, 驚雷 | 2021-08-08
李嘉穎、鄭點和驚雷三位詩人,分別以〈邊緣〉、〈禁令下達之前〉和〈「」〉三首作品,寫下對今日香港社會的一些觀察。像〈邊緣〉一詩所寫,「風愈大,味道散了淡了/窗的巨/響驚起了床邊裝睡的她/『醒了嗎?』/迴避是她的姿態/沉默是她的答案」,與〈「」〉暗示的那些不能言說的「禁令」,似有某種呼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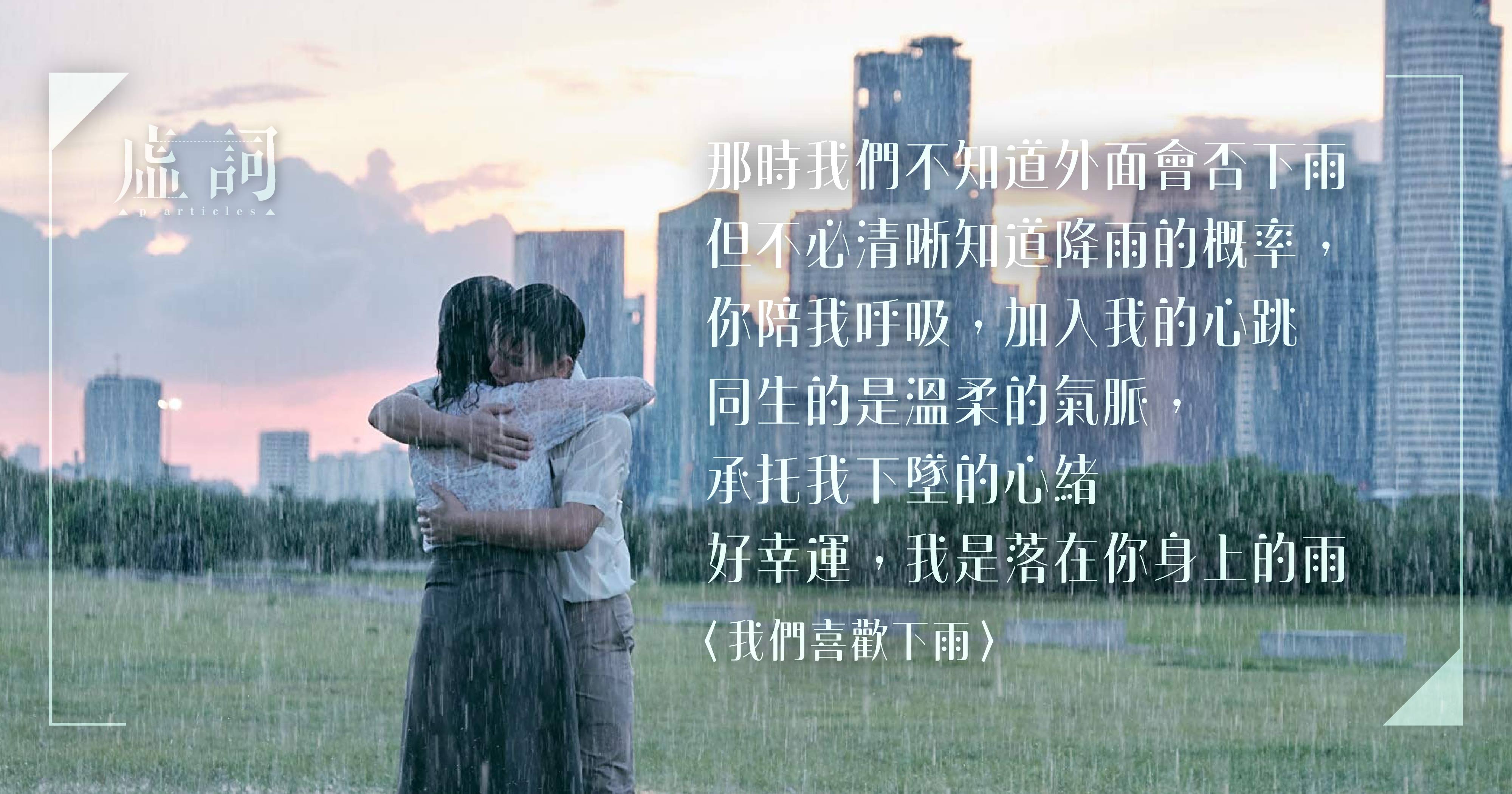
詩三首:鄭點 X 司徒子榆 X 李修慧
詩歌 | by 鄭點, 司徒子榆, 李修慧 | 2021-07-17
來自兩岸三地的詩人:鄭點、司徒子榆和李修慧,分別寫出了各自呼應當下社會氛圍的詩作。對禁令的恐懼,下雨的意象和隱喻,還有應該如何談純文學這些問題,都在詩句中尋覓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