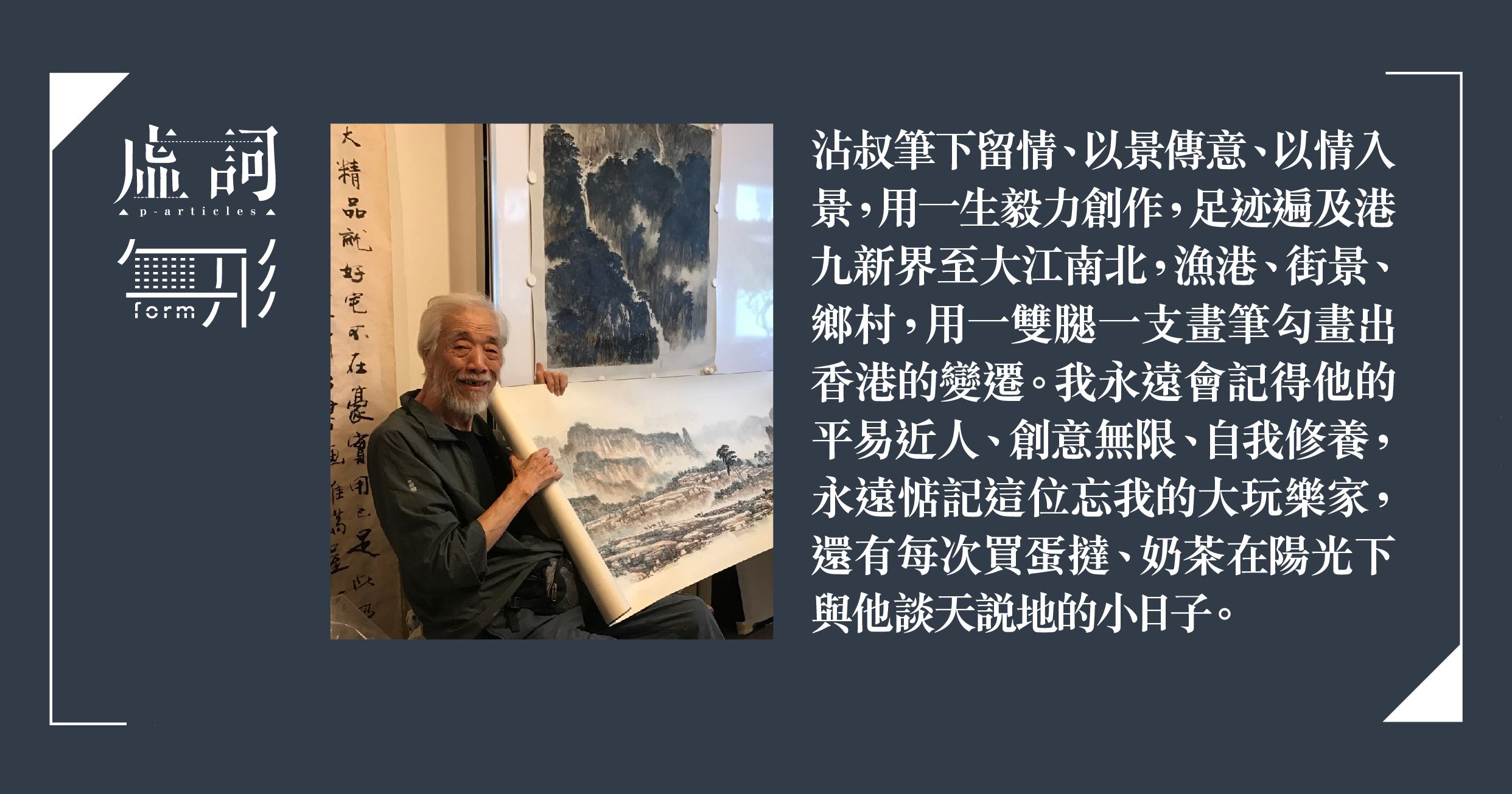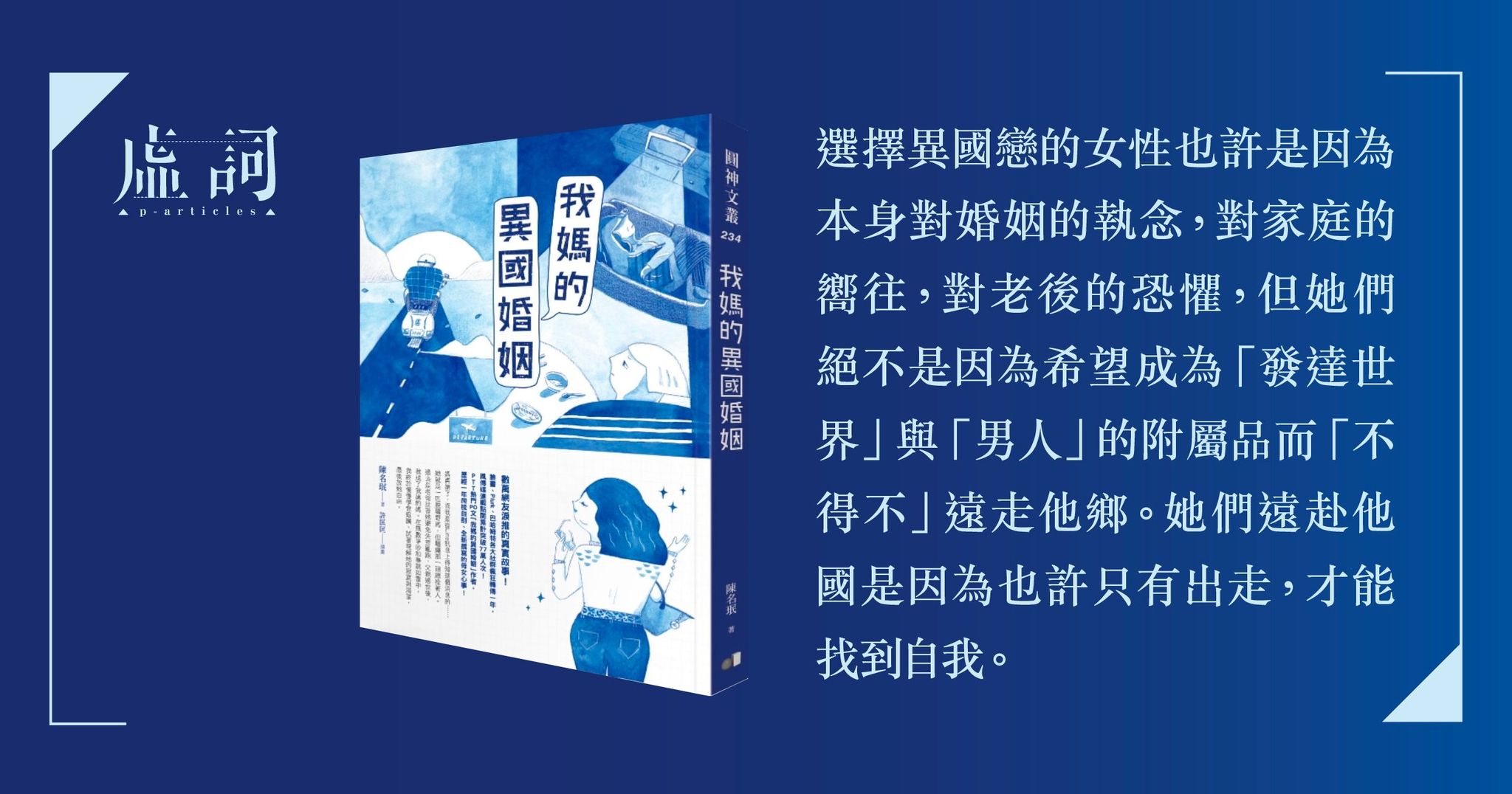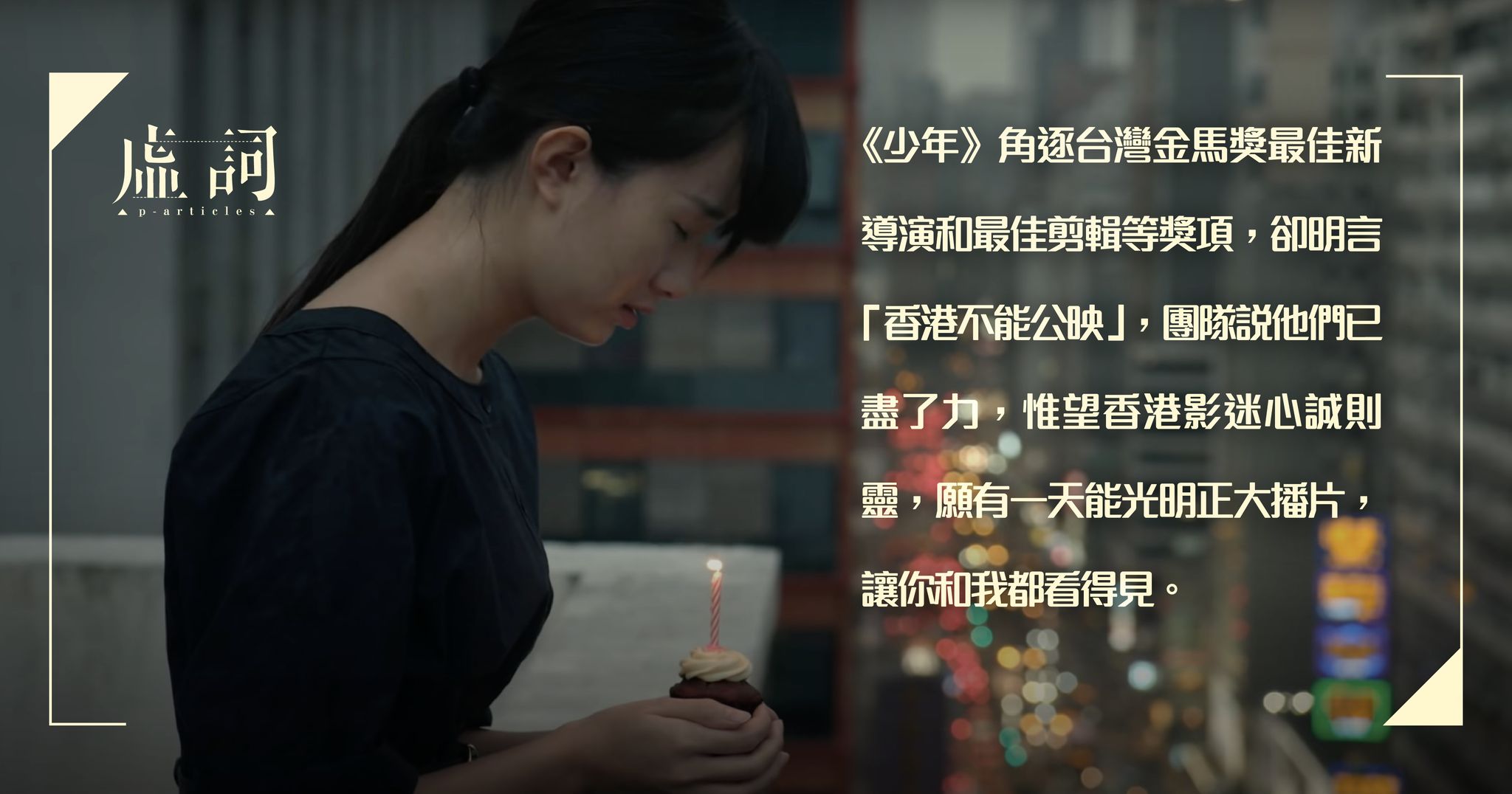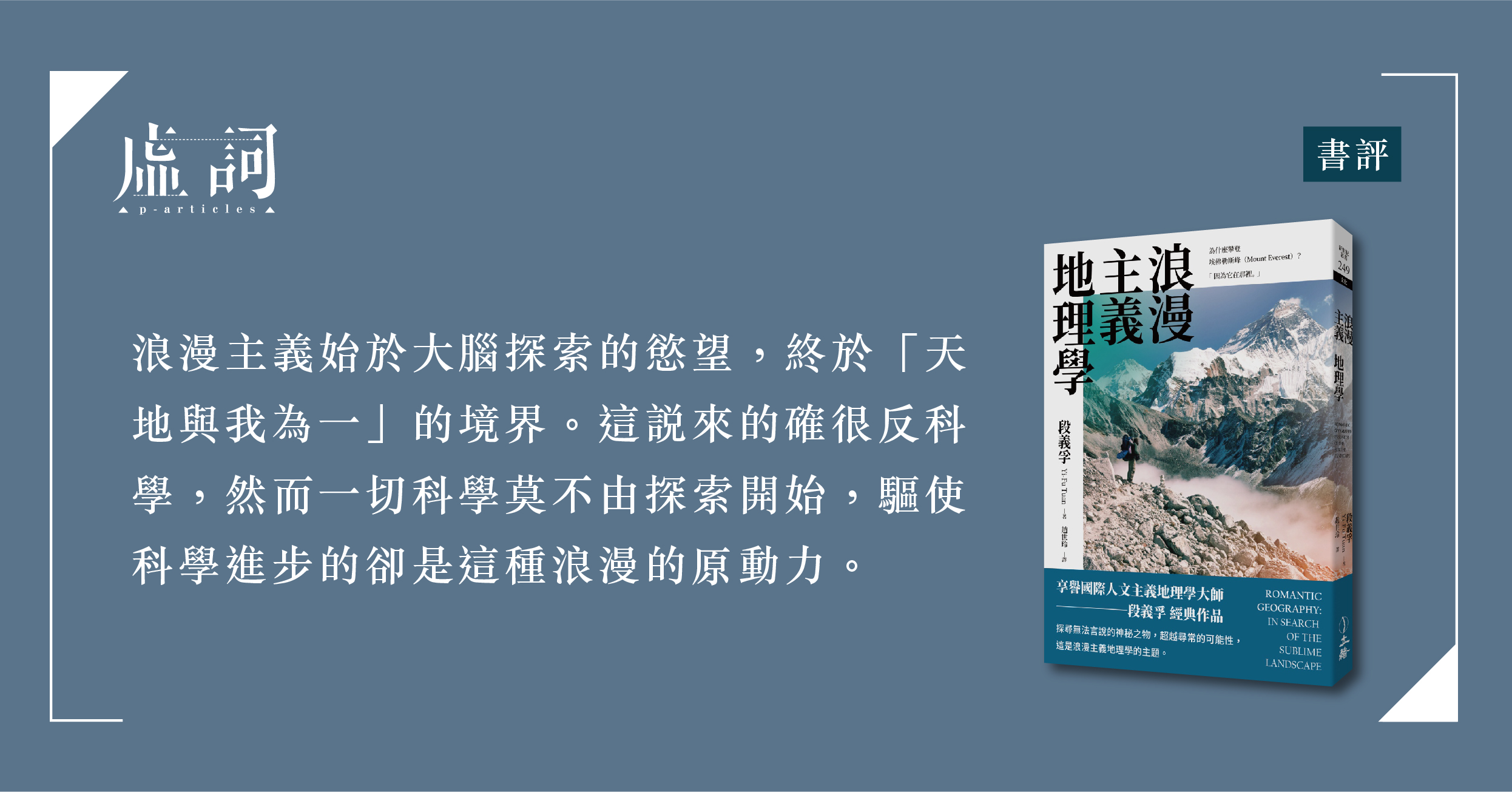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出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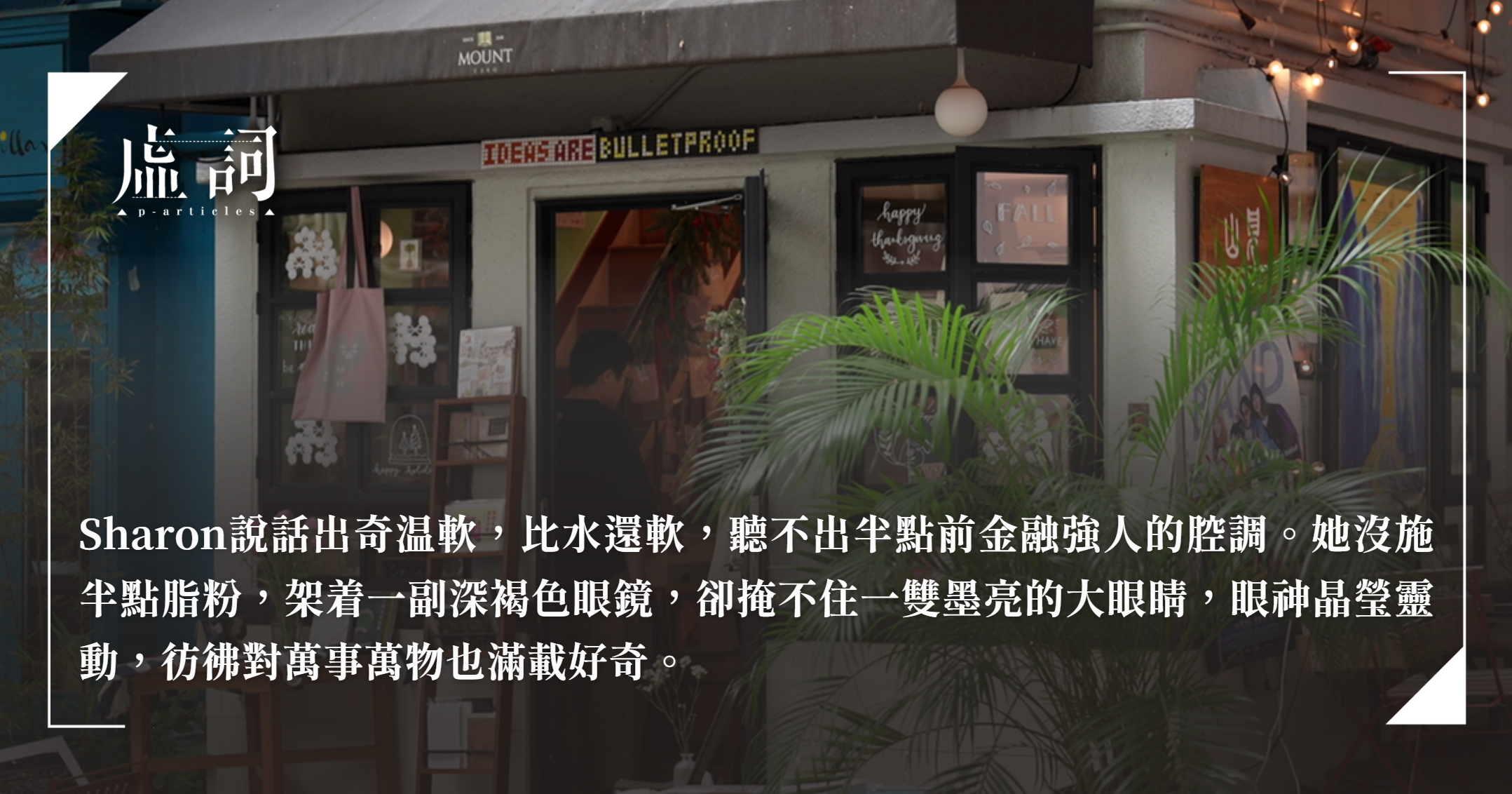
見山還是山
散文 | by 善喻 | 2024-05-22
善喻第一次到見山大概在2018年,當時它開始營運不久,來看書的人還不多,更顯清雅,後來見山成了名,他卻去得較少。為了讓自己的「賣不動的小書」找到好歸宿,他找到見山店主陳莘堯Sharon,「我當然不敢跟海明威比,對書本能找到一絲生機已心感滿足。」後來屋宇署發出清拆令,Sharon說:「你的書全賣出了,很喜歡你的筆觸,還有寫作嗎?」他向Sharon道別時,Sharon引他到門外小空地,望向閣樓說,已訂購了新的簷篷,合規格的。他心生好奇,「不是結業嗎,還是有新的計劃?」Sharon沒說,他也不便再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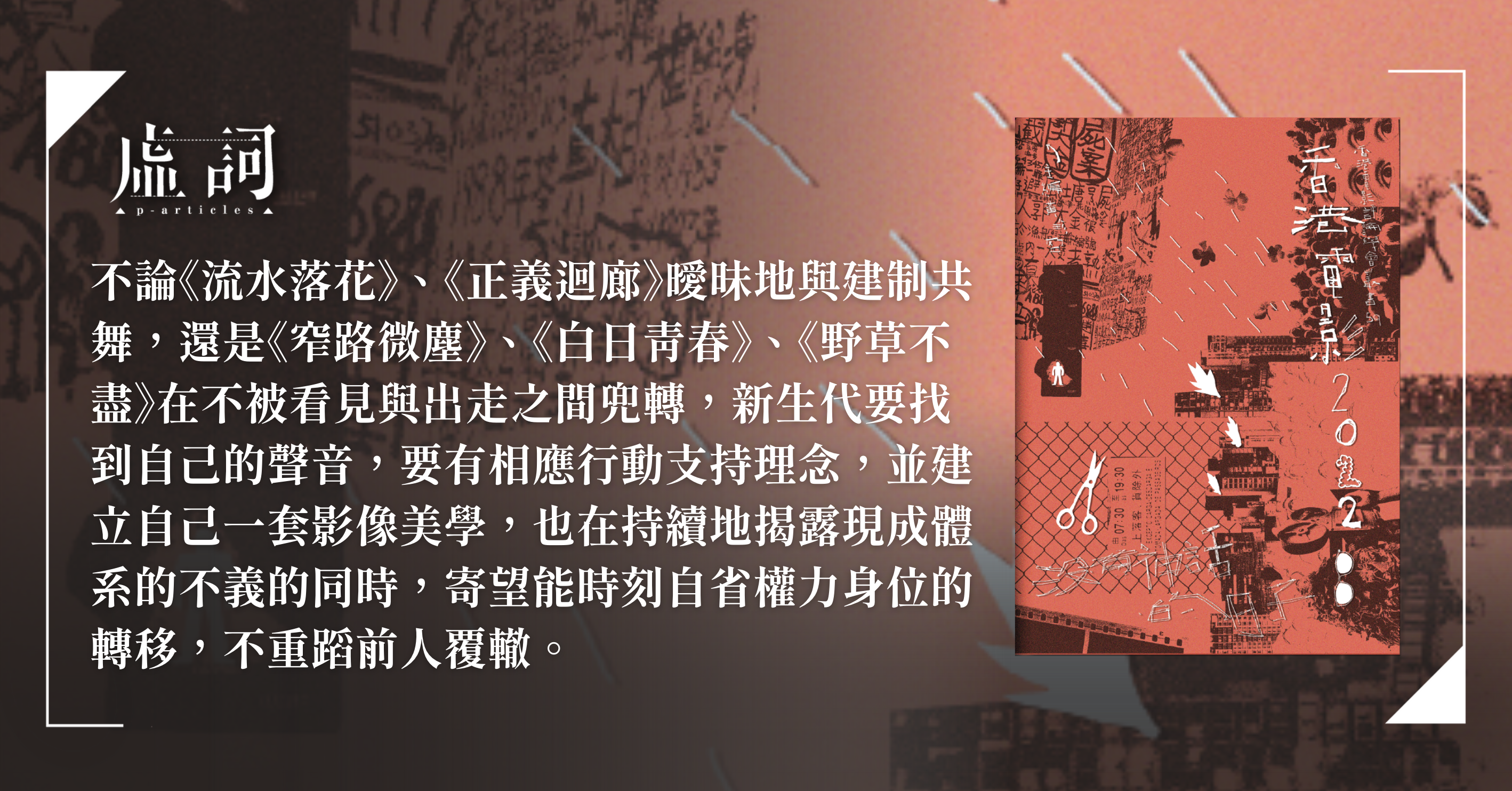
【新書】新生代的出走與反抗: 論2022年香港電影
影評 | by 查柏朗 | 2023-12-22
2023年的《年少日記》與《白日之下》,總讓人想起去年的四字電影熱潮。查柏朗在去年的香港電影脈絡中,處處可見兩代在價值觀、文化傳承或權力上的不對等。不論《流水落花》、《正義迴廊》曖昧地與建制共舞,還是《窄路微塵》、《白日青春》、《野草不盡》在不被看見與出走之間兜轉,新生代要找到自己的聲音,要有相應行動支持理念,並建立自己一套影像美學,也在持續地揭露現成體系的不義的同時,寄望能時刻自省權力身位的轉移,不重蹈前人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