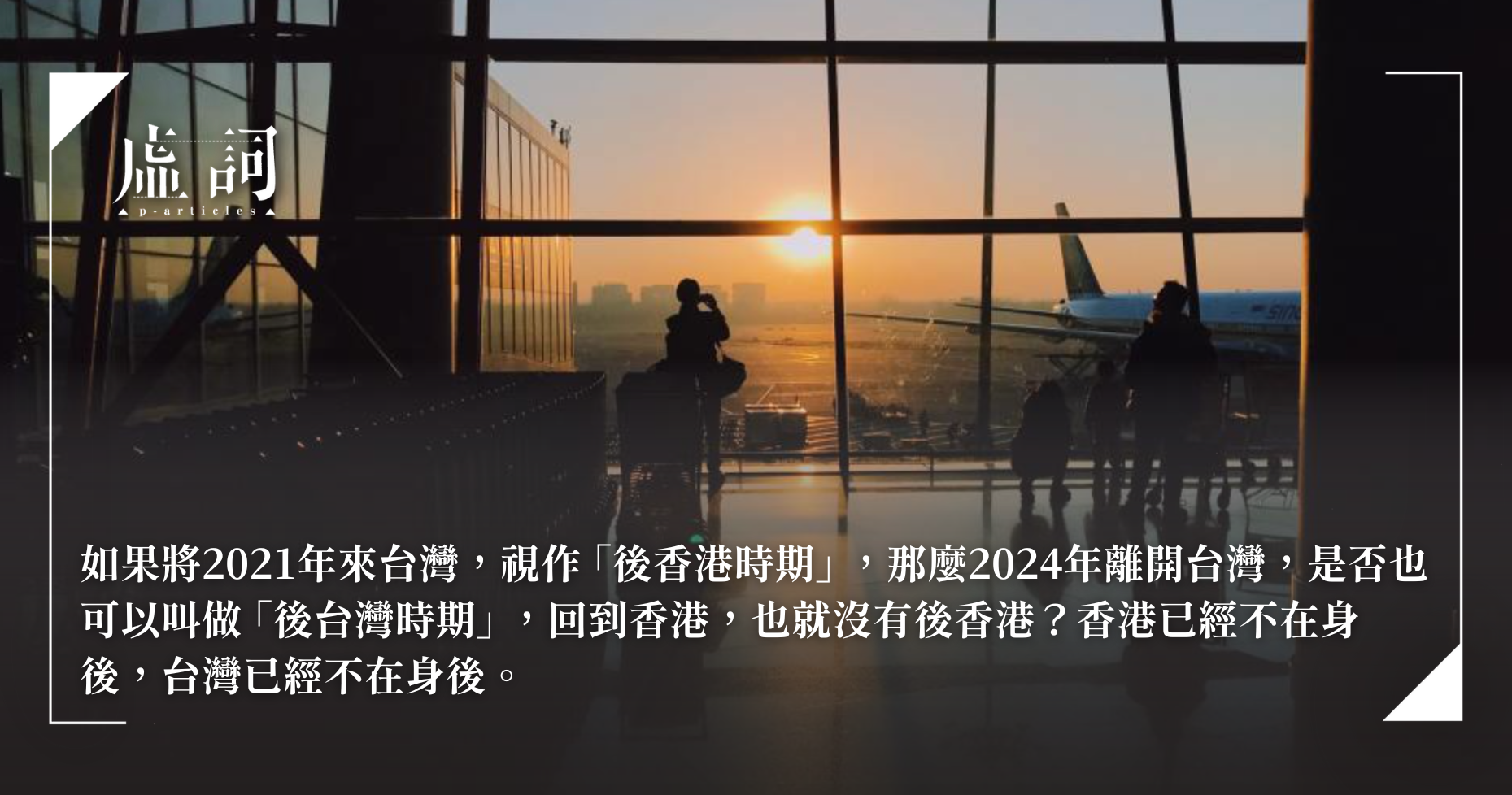黃戈三年前離港到台灣清華大學進修。初到日子正逢颱風,陰沉細雨不免有路盡途窮的錯覺,隔著海峽,煙濤微茫,香港已經不在身後。種種改變,儘管他不習慣,但變了就變了,變了就不想變,反覆循環,許多生活細節提醒已身在異處。一人在台灣,既隔斷香港但也不融入台灣,在獨處中群居,或在群居中獨處,不即不離,不冷清不熱鬧,他反而又自在之感。2023年畢業,清華大學的畢業歌叫〈清華大工地〉,後來便成了記憶的支點,偶爾想起,覺得痛,就好像還活著。三年後,臨近畢業,其中的生活記憶突然讓他有種此處是歸宿的感覺,尷尬的是,幻覺成形,卻住不久了。他想,離開香港的日子怎樣稱呼、回到香港的日子有怎樣稱呼。若未來又有更動,記憶會疊加下去,沒有就沒有。 (閱讀更多)
【悼念瘂弦】 瘂弦:技術細節與解答之書
瘂弦先生過世之際,身處臺灣的鄧小樺排除萬般工作,重讀《瘂弦回憶錄》以及瘂弦與楊牧的書簡,恍如讀了現實的解答之書。瘂弦說臺灣的詩刊文化是以地下文學的方式崛起的,也有些改女性化筆名的趣事,而在鄧小樺看來,瘂弦、洛夫、張默三人胼手胝足捱窮辦詩刊,這些前人自掏腰包養文學的故事,倒像是啟示甚或預敘。除此之外,回憶錄也記載了在意識型態強力監控的當時,瘂弦一代人如何繞過審查、追求自由,令她記得在做到「懶洋洋之必要」之前,先要有必要的溫柔。 (閱讀更多)
【馴化事件】舊香港人
作家韓麗珠昨日(8日)發文回應「馴化」爭議,她認為理解和馴化都是漫長的過程,作為舊香港人,她認為香港人即使不認同他人的言論,也會尊重其表達自由。但爭議帶來的討論碰撞,令她發現這幾年來的創傷其實比想像中的大,我們失去了一種無視他人評價的內在力量,在眾多聲音裡,必定有偏見、誤解、了解不足,或不想了解的,而這些都是理解過程的一部份。今非昔比,她認為身在反抗和馴化的現實之中,只可以在小說裡描繪當中無數複雜的刻度,但她始終會回答「我鍾意香港」,即使她害怕街上氣氛沉重,人們彼此遷怒和壓迫的香港。因為只有在香港,她才能專注做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同時儲存內在的力量。 (閱讀更多)
家訪
孫樂欣寫探訪老人。老人獨居在小小的公屋單位,屋中種種物事與複雜味道形成了停滯的時間。老人身體可見的變差,但因為覺得自己時日無多,不願服藥、也不願看醫生。指認照片的不同人物時,老人不記得,無從答起。作者提醒老人,自己是他的孫女,但因記憶的缺失而顯得疏遠,猶如剛認識的陌生人。中秋節晚飯,等待其他家人過來時,他的眉頭皺起,如記憶在當中亂纏,顯得尤其疼痛。 (閱讀更多)
雨中的香港 見山還是山
散文 | by Sir. 春風燒 | 2024-09-06
Sir.春風燒在見山書店結業倒數時未能抽身來一趟,這次終於有空來港,可惜未有在大館藝術書展遇到Margaret。關於新書《雨中的香港》,他憶述有趣的購買經驗之外,也認為字裡行間充滿堅韌不拔的良善與可愛,Margaret在身體力行、認認真真地用溫柔的日常和童真童趣去抵抗、去消解每個虛無的荒謬,不亢不卑,看得人熱淚盈眶。即使緣慳一面,讀到《見字做功課》仍如臨場被老師點名批評和催交功課。那夜,他再讀到《郁鍵名饌》,想起離開大館後到訪的見山書店就潸然淚下,見山有此命途,有是一場圓滿。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