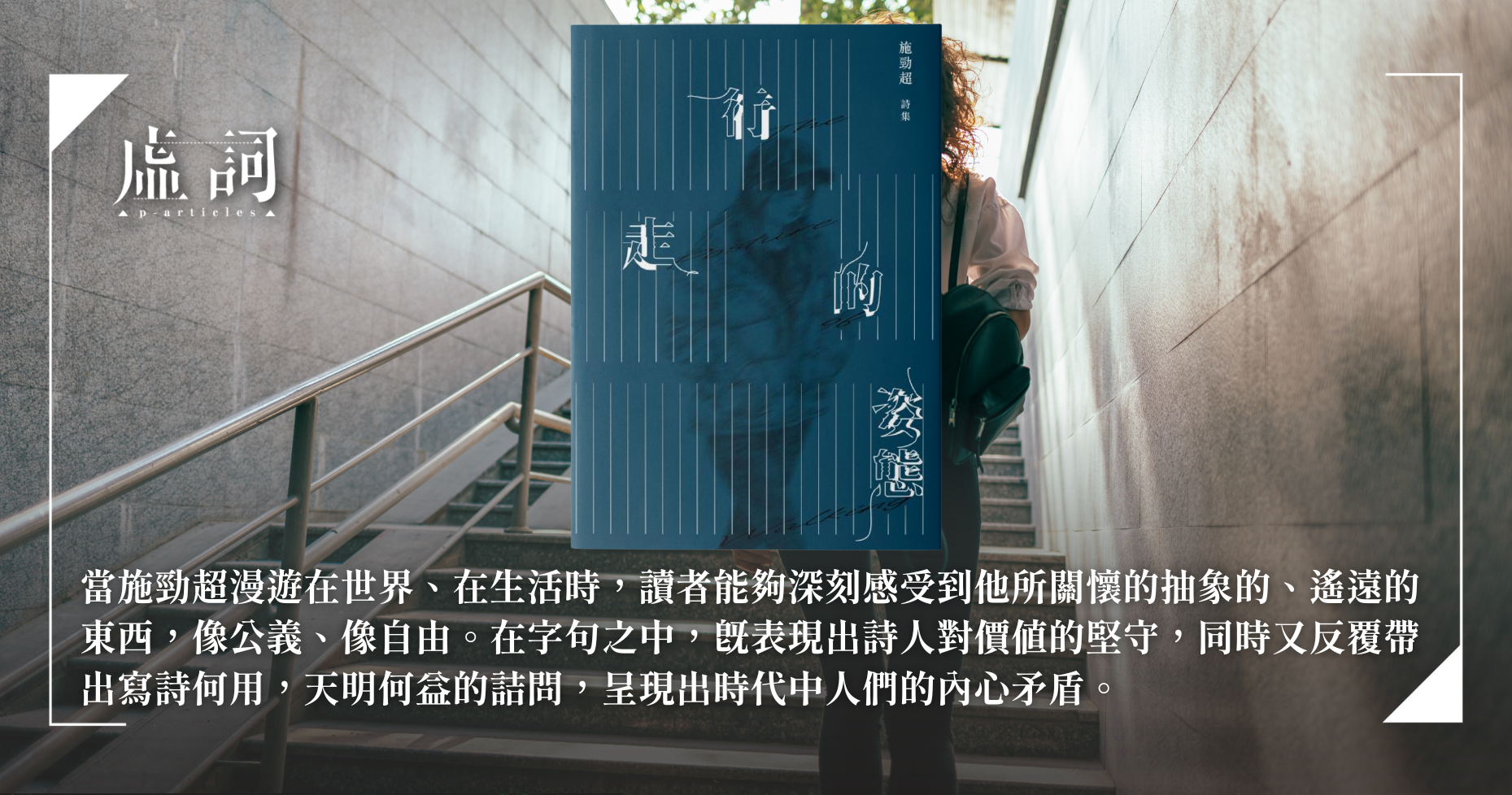肉身的革命——淺論施勁超《行走的姿態》中的城市「漫遊者」
書評 | by 盧麗斯 | 2025-05-09
施勁超是香港新生代的詩人,在2023年出版其首部詩集《行走的姿態》,遊走在生活、在世界、在語言之中,由此去觀察、體會人生之種種。詩人猶如19世紀被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邊走邊觀察邊思考的漫遊者(flâneur)般,在紛擾的世代中重新建構人與社會,乃至世界的關係。當現今人們都傾向躺平、擺爛時,而詩人卻以「行走」體驗生活,把詩集分為五輯,由外至內,在凝視外界時,同時凝視自己,以表達出對資本的反抗以及於生命的思考。
詩集的第一輯,詩人命名為「觀望:風波裡的茶杯」,在標題便表露出「漫遊者」的姿態。本雅明指出漫遊者「喜歡跟著烏龜的速度散步」[1]並以此作為了一種戰術,在現代空間結構內部實現反權力、反政治。在這輯詩中,詩人漫遊在世界的廢墟之中,以一如「烏龜」般的悠閒恣態,寫烏克蘭基輔、緬甸仰光,觀望著這些「風波」同時將之倒進「茶杯」之中(茶杯是人們相聚閑聊時的標配)。詩人指出紛爭成為談資,借人悠閒刻劃出現代人拜物的人性廢墟。
詩人在〈烏克蘭農場大蛋〉中寫:
Y昨天路過街市把偶然遇見的
烏克蘭農場大蛋植入畫框
經過修飾後上傳至社交媒體——
聲稱灰黑的蛋殼讓他想起遠方
戰火的硝煙與灰燼(這是正式錄用的雞蛋嗎?)
然後,Y從褲袋掏出幾枚硬幣買了
兩隻烏克蘭農場大蛋(不用找贖了,也不用膠袋)
兩隻大蛋在他褲袋裡晃蕩——
Y走出了大慈善家的步伐,好像
剛剛幹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好事
詩作寫出了戰爭下的偽善者和無良商人。偽善者以善意包裝意圖擷取流量的目的,他們把買入所謂烏克蘭農場的雞蛋,當是對烏克蘭的支援並引以為傲,轉頭將之放上社交媒體,假意同情指「想起遠方的戰火」,實際卻是在消費戰爭。
另一方面,商人以戰爭作為招徠手段,然而遠方的農場早已「都被踏為戰場,所有/大蛋也被打碎」,揭示出無良商人將不知來源的雞蛋標為烏克蘭農場雞蛋(故詩人問「這是正式錄用的雞蛋嗎?」),以此吸引偽善者們的消費。
最後詩人說:「永遠,不要以為:/買了烏克蘭農場大蛋就能/成為烏克蘭人」指出戰爭的殘酷非他人能夠體會,批判旁觀者的自以為是和偽善。施勁超以戰爭以外身處和平的人們日常之悠閒,襯托出烏克蘭的狼藉戰場,同時體現出現代人充斥偽善和貪財的人性廢墟,以此對荒謬作出反抗。
在批判偽善者的同時,詩人同樣在反問反抗的意義,寫緬甸內戰的詩作〈提槍的人〉:
封鎖線被延長——
新聞在被截取前翻譯成數十種語言
通訊網絡也是 在中斷前盡量廣泛流通
世界性的頭條在同一天賣光
在一片譴責與聲討以後呢?
事件被廣而宣之,作為頭條被賣光反映出世人對事件的關注,可是在「譴責與聲討」後,同〈烏克蘭農場大蛋〉般批判了那些消費傷痛的人之後呢?詩人並沒有給予回答,而是將問題留給了讀者。當讀者在思考能夠如何進一步對不公義、不人道的事作反抗時,反抗的思想便從詩歌中被承接了下來。
詩人漫遊在不同的廢墟之中,或抽離或深陷,由此在其中建構出他與城市的關係,如本雅明在《巴黎,19世紀的首都》一書中所指:「詩人享受著既是他自己又充當他覺得合適的某種人的那種無可比擬的特權。就像遊魂尋找一個可以依附的肉體, 他隨時進入他想進入的另外一個角色」[2]在詩作中詩人既抽離地以旁觀者般批判他人,同時又進入人群之中表達出共同的苦惱,本雅明就這種文人思維指出:
「文人隨著『波希米亞流浪漢』進入了『遊手好閒者』的行列,他們是大城市的產兒。在擁擠不堪的人流中漫步,『張望』決定了他們的整個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文人正是在這種漫步中展開了他同城市和他人的全部的關係。」 [3]
經濟及資訊全球化加劇了資本主義的影響,在現今世界中我們早已被物質包圍,那個曾經最早出現在巴黎的拱廊街亦早已遍佈不同國家,甚或是世界本身也已成為一個巨大的拱廊街,漫遊者能夠觸及的地方亦更廣泛。施勁超基於這種空間以及資訊的便利,漫遊在世界之中,揭露出在現代化資本主義社會給予人與人、人與社會所帶來的失落、疏離、肢解,同時反思人們在社會,乃至世界中的角色。
自第二輯起,詩人從對世界的思索回歸到其生活的香港和曾留學的臺灣,將視角集中放入群體之中,寫被生活壓迫的打工仔、寫平凡無奇生活在城市中的升斗小民。不同於詩輯一對於異國的那種思想上的幻想漫遊,當詩人書寫香港和臺灣地景時,能看出更多有關於漫遊者在「步行」上的敍述。
米歇爾‧德‧賽托(Michel de Certeau) 從解構主義提出步行者的陳述,認為:「走路行為之於城市體系,就如陳述行為(speech act)之於語言或被陳述之物。」走路行為成為了陳述的空間。[4]在移動之間橫穿、改道,或是拋棄原有的空間元素,使其偏離了原來靜止的秩序時,便超越了空間的邊界,人們能透過對道路的再書寫由此顛覆城市的規劃,並重新賦予空間意義。
在〈過香港仔華富邨〉一詩中,詩人藉由乘坐巴士行走於都市之中,由此將香港不同的景色串連,從中書寫並反思個人的都市經驗,在再現和重塑之間建構出都市形象。詩人見到「朝車站揮手的影子都被塗鴉覆蓋,象徵/歡迎或一種道別(意義總是雙向的)」可能是在車上的人看車站送車的人,或是送車的人看車站尚未開出的車上的人,意義是相向的,如「象徵/歡迎或一種道別」,如「老人與青年人相等」。歡迎與道別是相向的,但是「孩子們不甘被納入體制/與土地縫為一體」卻指出了衰亡與新生相向下的不尋常,孩子不甘心進入到體制之中,卻要與土地縫為一體(入土常意味著死亡)。
詩人進一步覺察到「沒有真情需要被冠名贊助。 對的/但現實哪一種關係並沒有與價值掛鉤?」正如馬克思所認為「一切激慾和一切活動都必然湮沒在貪財慾之中」[5],在關係於資本社會中被異化的狀況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往趨向了商品化。
詩人「坐在上層感受巴士隆隆作響……/車身緩緩挪動,司機調整操縱桿/一幕幕褪去短促的人情風景」,在車上遊走於都市間,詩人以「馬路解除封鎖,車輛因改道逆行」將日常規範的交通錯置、移位,表現出城市的失序,如同上文寫青年與老人的相向般,規範中蘊含失序,平常的事物卻內藏荒謬。在移動間詩人觀及:
臨街的窗是一個水族箱/框住途經的建築和行人
彼此隔絕。 是他們自由還是我們更自由?
是我們觀看他們還是他們觀看我們?
詩人以一窗之隔思考自由,其中亦表現出「看與被看」的相向關係。看似自由的同時,我們是否也如同詩中那些「自願付款困進行走的籠牢觀看動物的遊客」般,自願為奴卻不自知?
當時針指向十一或朝向十二
形成少於四十五度的傾角時
拾荒者以分散的水柱射向紙皮堆
鴿子列隊,在織滿銀線的山坡上跳飛機
詩人提到「拾荒者(ragpicker)」令人聯想到本雅明筆下的書寫,本雅明把拾荒者視為漫遊者的鏡像,指出二者或多或少都與社會對立、面對岌岌可危的未來、關注城市使人感到不安的面貌,及具有一種「反社會份子氣息」。[6]末句「織滿銀線的山坡」似乎指向了金錢掛帥的社會環境,象徵和平的鴒子跳飛機,意圖跳出資本的羅網。詩人一方面點出了資本對自由及和平的羈困,一方面又呈現出對和平、自由的渴求。而當時間走向一天的終結(或是開端),詩人仍在以反抗的姿態叩問價值的所在,確切地如「拾荒者」般,在漫遊間拾起時代的荒蕪,抵抗著華麗掩飾下的失序。當施勁超漫遊在世界、在生活時,讀者能夠深刻感受到他所關懷的抽象的、遙遠的東西,像公義、像自由。在字句之中,既表現出詩人對價值的堅守,同時又反覆帶出寫詩何用,天明何益的詰問,呈現出時代中人們的內心矛盾。
[1] [德]瓦爾特·本雅明著,劉北成譯:《巴黎,19世紀的首都》(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頁121。
[2]同上,,頁123。
[3] [德]瓦爾特·本雅明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北京: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頁5。
[4] [法]米歇爾‧德‧塞托著,方琳琳、黃春柳譯:《日常生活實踐:1. 實踐的藝術》(南京:南 京大學出版社,2009), 頁176及180。
[5] [德]卡爾.馬克思著,伊海宇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臺北:時報文化,1990年), 頁98。
[6] 彭小妍《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〇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 譯者》(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