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 RESULTS FOR "歷史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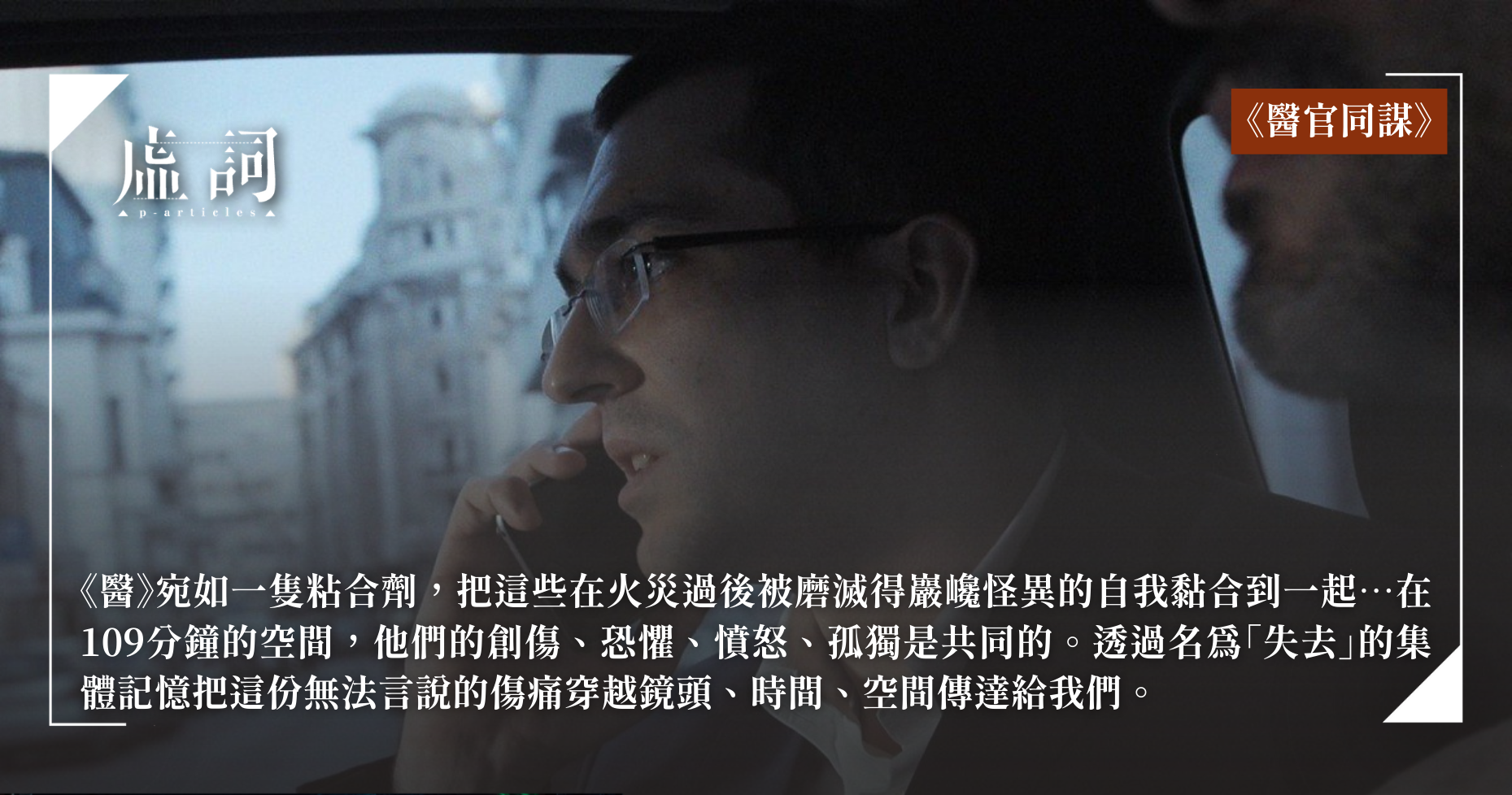
《醫官同謀》:集體創傷與歷史書寫的距離
影評 | by 鄧皓天 | 2026-01-06
大埔火災一事令各界痛心疾首,鄧皓天早前觀畢以大火災難為背景的羅馬尼亞紀錄片《醫官同謀》,指出電影不單止呈現集體創傷,更道出了歷史創傷書寫之不可能及其與創傷論述之間弔詭的辯證。鄧皓天援引王德威的「噬史的檮杌」——現代性與怪獸性,指出戲中既紀錄了官僚體系的平庸之惡,更在改革失敗的絕望中,展現了倖存者無法言說的痛楚。縱使結尾揭示了改革的無力,但片中人物透過共享失去黏合破碎自我,在絕望中以共同的「失去」抵抗遺忘。

葛亮 《靈隱》讀後 ── 疫後和時代變異之際的一封情書
書評 | by 克琹 | 2025-05-08
克琹讀畢葛亮小說《靈隱》,認為葛亮以精湛的文筆,將香港「弒妻案」、SARS與疫情等真實「現象」融入故事當,更以三段鏡像構築小說結構,令整本小說宛如一封寫給疫後倖存者的深情「情書」。小說的故事精彩,甚有許多值得思考玩味再三的句子,一如既往地交織飲食文化、語言變革與人性幽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