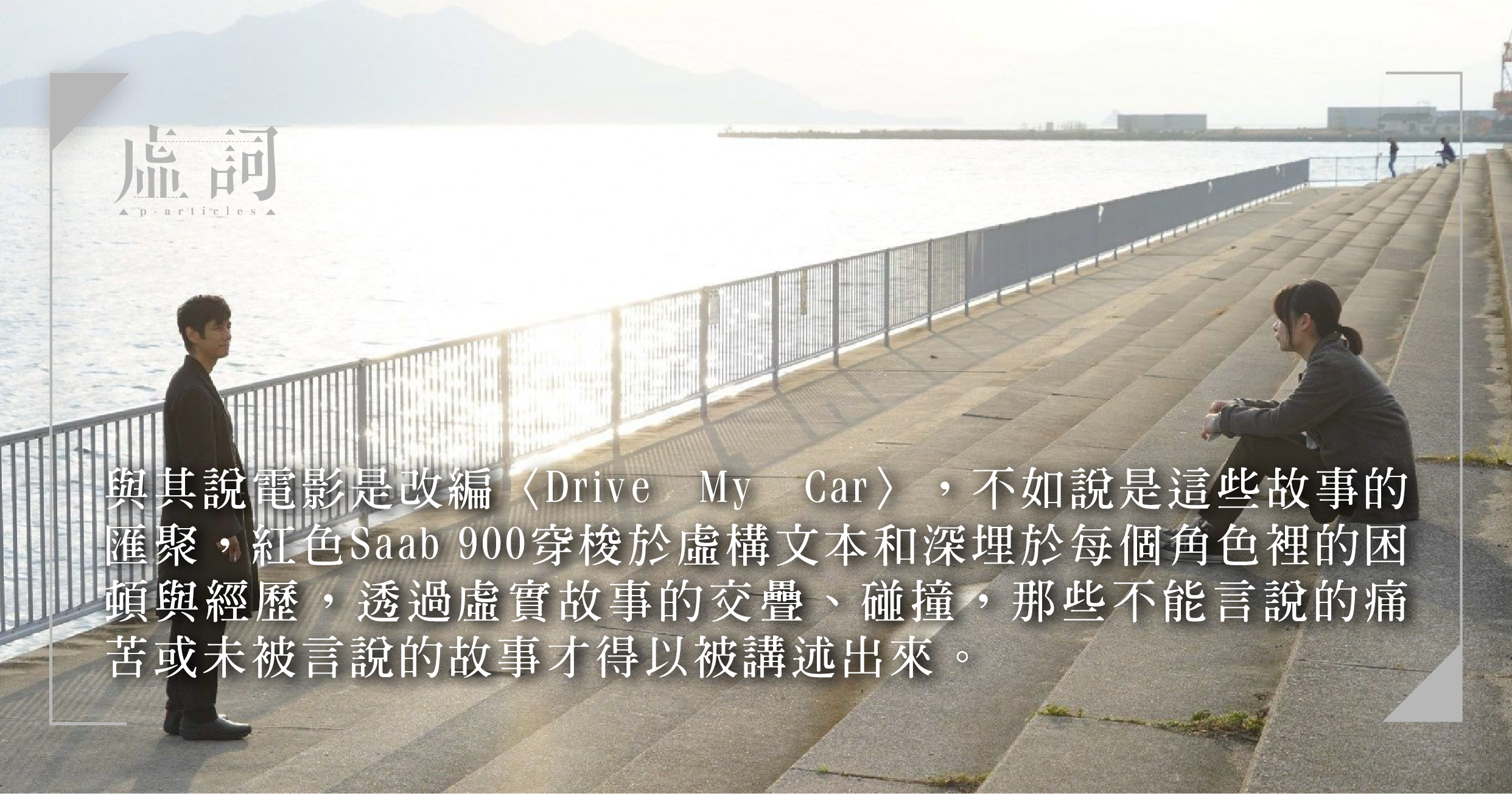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性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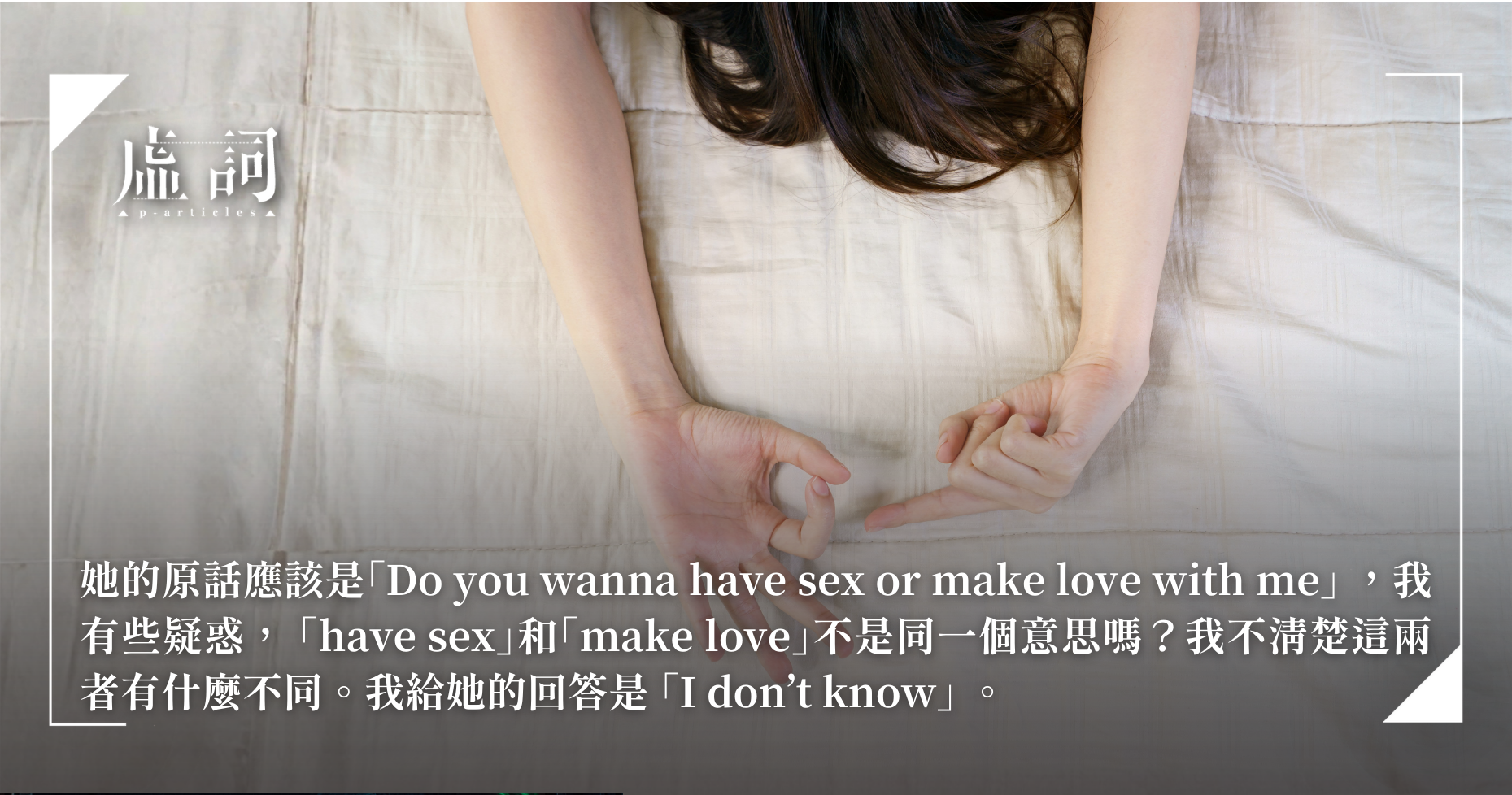
有天一個女孩問我
小說 | by 曾可駿 | 2026-01-30
曾可駿傳來小說,書寫「我」在大學圖書館正在閱讀雷蒙德·卡佛的小說,突然被一名素昧謀面的東南亞女孩詢問是否願意與她做愛。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邀約,「我」感到困惑與驚嚇,僅能回覆「I don’t know」及「I have no idea」,完全無法分辨這是真實邀約、惡作劇還是採訪。當女孩回到另男伴身邊後哭笑不得地向他重複「我」的回答,而神情亦略顯無奈。

比性愛更誘人的「一夜情」《Living for Live》報告指七成人寧看演唱會不做愛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5-11-19
假若今晚有時間,不知各位讀者會選擇去看一場心儀藝人的演唱會,還是與伴侶共度春宵?全球現場娛樂巨頭 Live Nation 近日發布的《Living for Live》趨勢報告,給出了一個令人玩味的答案:在「看演唱會」與「發生性行為」之間,高達 70% 的受訪者選擇了前者,僅有 30% 選擇性愛,其中受訪者選擇看演唱會的比例,甚至超越了電影、體育賽事等娛樂活動,成為全球消費者心目中的娛樂首選。

愛慾分裂的青年戀人群像——小眾日劇《Around 1/4》
劇評 | by 任弘毅 | 2025-06-26
任弘毅傳來《Around 1/4》劇評,指劇中聚焦五位25歲左右青年在人生四分之一階段的情感掙扎。當中他們的人生命題同樣也是關於愛、性、情,共同面對普遍出現在現代論述中的「靈肉分裂」,或「性愛分離」,如早苗深愛男友卻對性感到疲憊,康祐在性中無感卻渴望心靈相通。然而,即使「靈肉分裂」,「性愛分離」也好,愛情的幸福並非全源於肉體滿足,而是心意的契合,正如康祐與早苗兩人以愛的意志超越慾望。

第三屆澳門國際酷兒影展開幕 李安現象級電影《斷背山》重現大銀幕!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5-06-03
第三屆澳門國際酷兒影展正式開幕,影展以「溫柔.革命」為主題,旨在展現酷兒經驗的多面性,共精選了十九部長片和四部短片,題材各異。分別有台灣金馬獎大熱之作《漂亮朋友》為開幕電影,在柏林影展榮獲泰迪熊獎最佳劇情片《太空百合戰鬥姬》、勇奪多個影展獎項的挪威作品《性愛夢之做夢》等。在「酷兒不朽」單元中,更將李安的現象級作品《斷背山》重現幕前,重新回味這部20年前的傳奇電影。

【文藝Follow me】「WOMEN我們:女也彳亍」展覽 潘浩欣談女同志的手與性愛:私密、歡愉及創傷
文藝Follow Me | by 黃桂桂 | 2022-03-19
藝術家潘浩欣(Nicole)以女同志的手作為拍攝對象,展示女同志的性愛,私密、歡愉、創傷,作品名為《In & Out》,在「入」與「出」中間,是否存有第三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