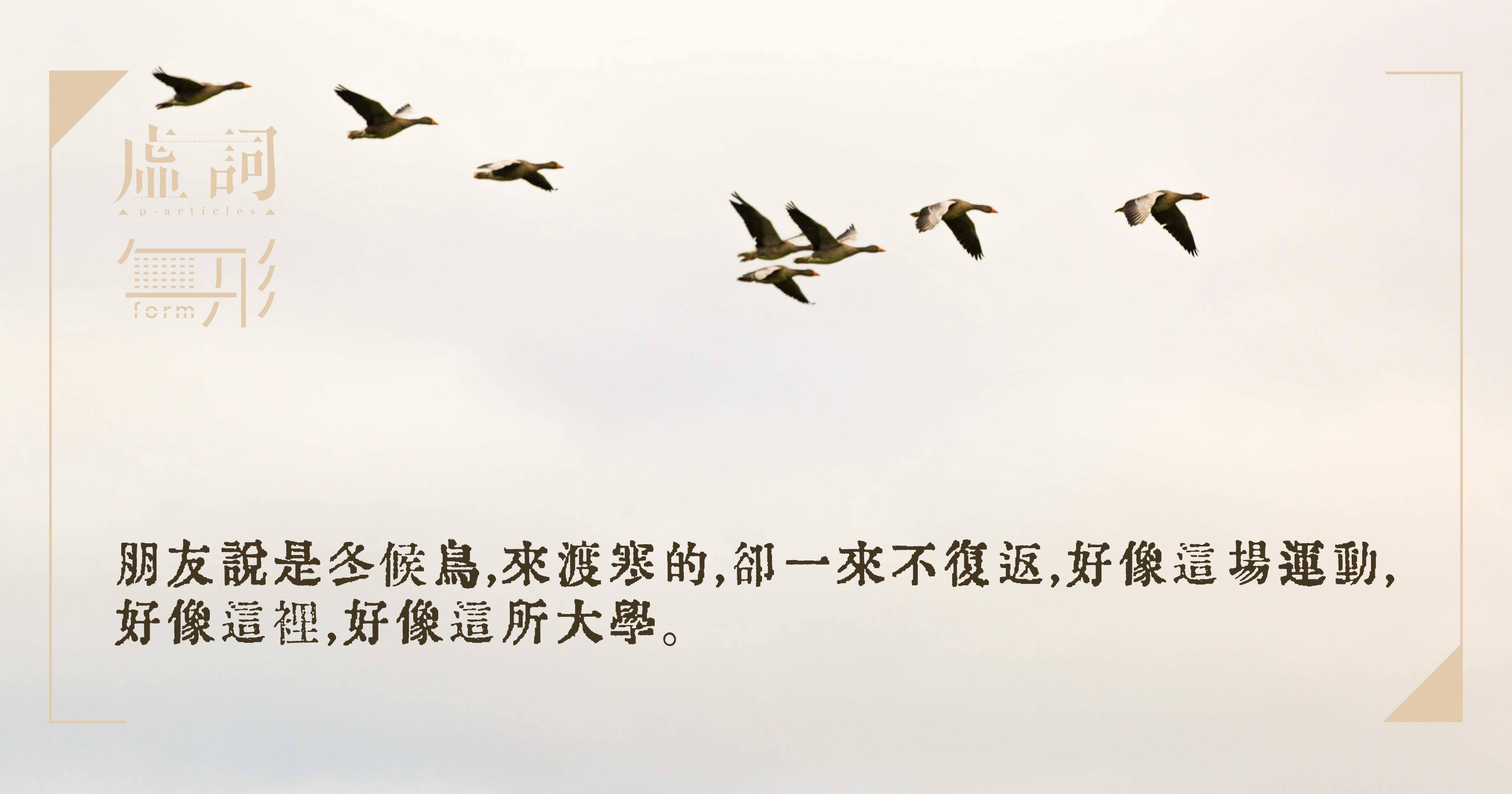【無形.說好的世界末日呢?】候鳥
這個冬天一去不復返。
明微尚未拿畢業證書,已找到工作,留在本科的大學做行政。同學們說她沒大志,先是延畢,又在這裡上班,困在荒蕪偌大的山頭十年八年,怎麼不到外面闖闖。她笑笑,不置可否,沒有解釋這個山裡可供發掘的好玩東西可多了——絮綿飄飛的蒲公英、蜷圈如圓碟子的青蛇、外皮糙軟的蛤蟆、石縫旁的含羞草……明微自認說話笨拙,明明說的是甲,別人卻聽成了乙。軟軟的話被理解成尖尖的刺,還回馬戳得她心裡難過,她才不要困在這溝通之難裡,不如多看沉默可愛的生態。
上班的路上,每天都會經過一道玻璃橋,連接校園山頂和後山,橫恆在山坡的叢林中,偶爾坡上的草枝過長,繞垂至橋上,掉下好些果子和枯葉,便會被理解為潛越空間,由校方召來工友裁枝。要裁枝的工友一臉納悶不耐煩,明微更納悶。
有時會遇見雀仔,在橋上彈跳,輕輕一躍,又上了枝頭。明微不懂分辨鳥的模樣,小時候只知道追著圓渾的麻雀跑啊跑。她阿嬤最喜歡在樓下的棋桌歇腳,撕麵包碎餵雀,麻雀便團團圍在附近一下下啄著,肥碩如巧克力味雪糕球。明微想,若有一次能抓起牠們輕軟的身子,那觸感必定像家裡的毛娃娃一樣溫熟暖和,但一次也沒有成功。阿嬤笑她,鳥是不能抓的啊,除非死了的鳥。
明微的工作幹得不怎麼順心,多是同事間相處。在外打滾多年的中年漢老覺得她不過是幸運蒙中職位的小女孩,一直風調雨順;比她年長幾歲的女孩與她同期入職,卻同薪同酬,說話總像吃了熟成的橙,甜中帶酸;也有自以為是,執著奇怪點上,難以合作的計劃拍檔。特別是,偶爾她會提起從前在這所大學唸書的時光和佚事,譬如唸書、住宿舍、在圖書館通宵寫論文、到廣場上看星星……同事便會一臉嘲弄問她,是否有種過份自以為是的優越感。他們說,好像她這大學畢業的,總抱有種莫名而愚蠢的浪漫主義。
有時覺得無法辯解,價值觀、生命裡的經驗如何影響人的長成,學校曉以她關心這些微小;但人們卻以年齡、工作經驗、出身、畢業於甚麼大學這些龐大的數據庫論斷他人,言之鑿鑿曉以大義。她覺得委屈,因為無法解釋,她無法解釋她自己,也無法解釋為何他人的經驗會賦予對方論斷別人的惡意,而非理解。
也許重點不在於如何理解,或許那些人根本不認為是惡意,不認為這些打擊與善意抵觸,於是長成現在的模樣。好像你小時候按死一隻蟻,燒一條蜈蚣,沒有後果,沒有人喊痛,你便繼續做下去一樣。多麼可怕。
晚上到天台抽了幾根煙,吐露港對岸的燈光閃爍爍的。明微忽然好憂傷,從辦公室回家的路,止不住哭得一塌糊塗。回去前想躲到哪裡再抽一根,卻連打火機也打不著。好沮喪,最沮喪的是,她不知道是否她太沒用才這麼傷心,抑或是她受了這樣的對待,實在是有權利難過的。
她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只想離開這種磨人而無從辯解,夾附在人群中的瑣碎日子。
下班後常去橋上看雀仔,發現一種鳥。不是麻雀,身形稍大,頭頂、翼末至尾端皆有一撮油畫般的藍,翼間倒是啡色的。明微第一次看到藍色的鳥,遠看以為雀仔是否在哪裡中了水炮車,弱弱飛來,畢竟早幾天才有鴿子中了催淚彈,眼腫如橄欖的片段,看得她心有戚戚。友人喜歡觀鳥,看了照片告訴她,這是藍翅希鶥,是候鳥一種,遷徙而來。又補充,你那山頭大學裡,住著許多候鳥,風光如畫,不少鳥都愛來過冬。往後明微開始跟朋友學認鳥,北灰鶲、灰背鶇……原來看鳥,還分有看鳥喙、色澤、身形、毛色,多麼神奇。
六月後日子開始變得不一樣,同事不再像從前一樣關心紅酒、股票、旅行,開始談起社會。她依然沉默,他們討論時事,就像那確實只是時事,像某條國際新聞標題一樣遙遠而不貼身:「反正不會鬧到我們這邊啦,沒事。」明微如常上班,沒有罷工,怕上司責備。但有捐款,周末會去遊行,當然不敢穿黑衣,只帶口罩,走到終點後便離開,完美融入人群。
她想,在能力範圍裡,已經做得夠多了。
那個在大學校園裡發射了二千多枚催淚彈的晚上,她在家裡邊吃飯邊看著直播,她從來沒有想過,這舒妥安好的山頭,竟也有被攻訐的一天。翌日早上,她回到辦公室工作。九時多,得知一個大學學弟被捕了,於是,一封公事電郵,打了三小時,仍未發送,看著每顆字,明微都覺諷刺。工作上,所有人設想「未來」將會多麼安定穩妥;但現實裡,「當下」又是那樣荒謬的事。
午後,明微經過橋間,終於看到了——一隻隻鳥的屍體橫陳在橋上,沒有彈跳,沒有躍動,就這樣,靜靜的,眼目圓渾,像小豆子。她俯下身,很近、很近、很近地,凝視牠們,甚至伸手便能觸摸它們,如同童年時一直渴望能把一個鳥放到掌心裡撫摸的欲望。
但她卻不願了,阿嬤說,鳥是不能抓的啊,除非死了的鳥。
朋友說是冬候鳥,來渡寒的,卻一來不復返,好像這場運動,好像這裡,好像這所大學。
明微想起自己的學弟學妹,幾天來在大學裡的奮戰。她忍不住想像,如果下午時分,突然間警察攻入來,在樓下拉捕同學,她在樓上拍下過程時被發現了,他們發射胡椒球彈或催淚彈,射爆辦公室的玻璃,她能如何呢?她連發射的人是甚麼面容都不會知道,而發射者,根本不會有任何後果。
在鳥以後,她想到,那些在辦公室栽種了一年多的靠窗植物,她所竭力保護的小花園,哪怕放假也要回來澆水,只怕他們會枯死的植物們。仙人掌、空氣鳳梨、玉露、碰碰香,好不容易長得欣欣向榮,一旦被催淚彈攻進來,將會全部枯死,忽然覺得,好難過,好難過。而她甚至沒有任何辦法阻擋任何生命的逝去。
明微邊默默埋著鳥的屍體,邊想,她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只想回到那種磨人而無從辯解,夾附在人群中的瑣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