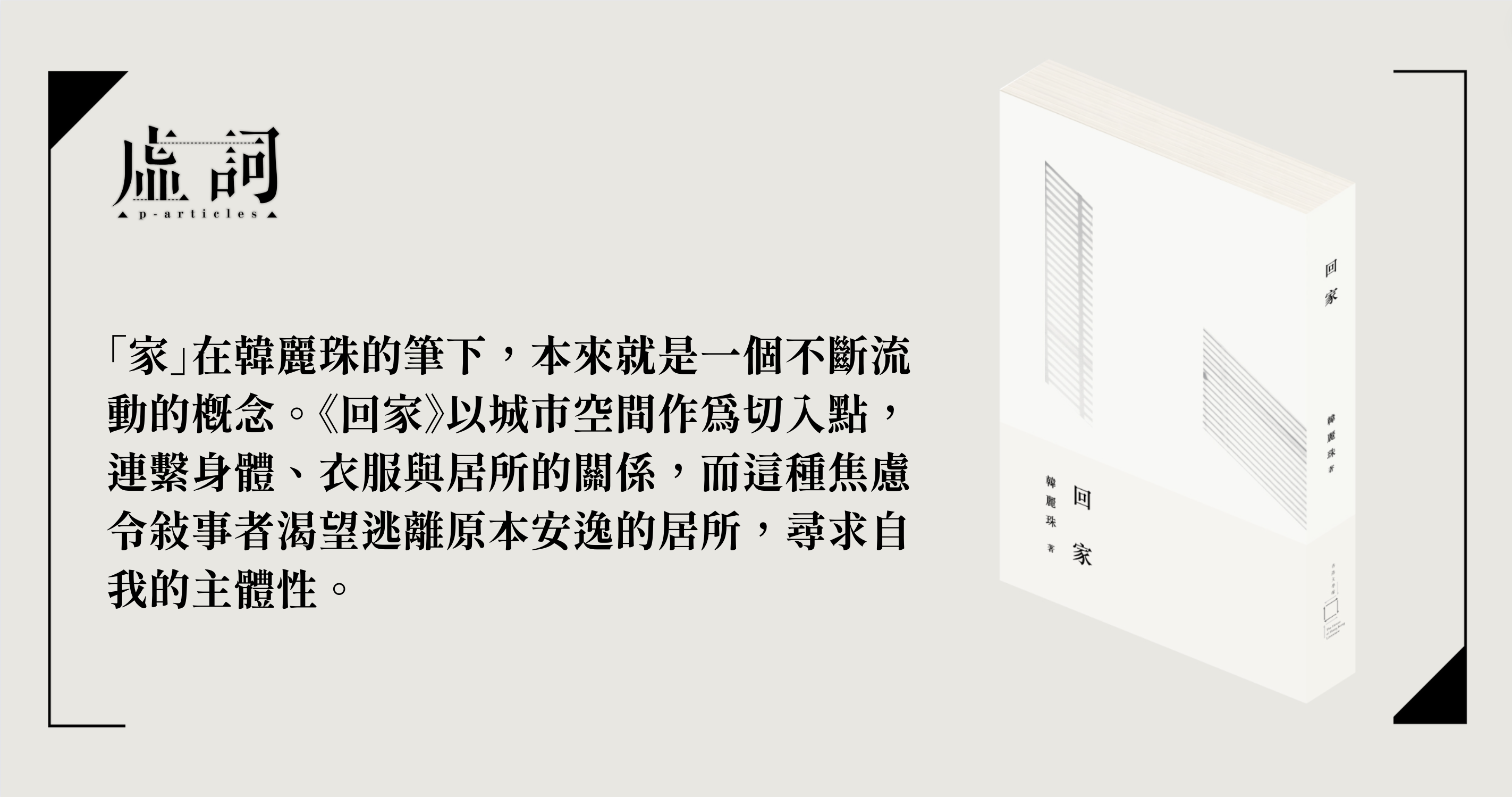木漏れ日日和——《新活日常》的木、日、影
雙雙看完《新活日常》的那晚,想起中學圖書館西北隅存放卡片目錄的小木櫃,就像平山的生活日常——一沓重複的表格,統一,泛黃,手寫,沒有更新,但有一種極簡主義的質感。他亦分析「木漏れ日」的構成,指出並非日日是好日,公廁有很多種,日子也是,平山的睡房「精緻」但樓下的儲物間依然凌亂;而片中的「影子疊加」問題令他想起了房慧真〈聊齋〉與《燒失樂園》裡的海美,她們的影子想必是很輕,很輕。 (閱讀更多)
與史俱進的歷史學家:評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到不自由之路》
書評 | by 翁稷安 | 2024-03-04
翁稷安讀提摩希.史奈德的新作《到不自由之路:普丁的極權邏輯與全球民主的危機》,總是忍不住想起昆德拉的「永劫回歸」。書中討論普丁如何打造俄羅斯的極權統制,進而影響世界的著作裡,史奈德從宏觀的視角提出兩個左右當代政治的虛構幻象:「線性必然政治」和「永恆迴圈政治」,來解釋民主在今日世界的挫敗。他認為前往不自由之路已然展開,需要每個人排除雜訊,謙卑而真誠的面對歷史,重新肯定真相的追尋和價值的建立,才有機會懸崖勒馬,替未來的人們在史冊上寫下美好的轉折。 (閱讀更多)
《墜惡真相》——事實與真相的隔閡、信仰之躍及審判本身的傷害
影評 | by 曾友俞 | 2024-02-28
臺灣律師作家曾友俞評《墮下的對證》,認為臺灣譯名《墜惡真相》使用「真相」一詞多少有些誤導性,因為「真相」從來不是法庭在意的,應以原文翻譯為「一個墜落的解剖」更為恰當。《墜》不但具有懸疑片與法庭片的外觀,實際上更讓觀眾意識到「決斷—判斷」的代價,以及提醒了我們審判程序——國家司法所具有的權力所帶來的傷害。 (閱讀更多)
《新活日常》——公廁圖鑑看當下
電影《新活日常》於國際影展成績斐然。它原是一個獲日本財団及澀谷區的委約作品,以2020年的「The Tokyo Toilet」項目為背景,推廣區內十多個出自著名設計師之手的公共廁所,像是東京公廁圖鑑。石啟峰認為它不帶硬銷意味,又不失影像語言的美感,彷彿是「說好東京故事」的教科書式範例,也順勢輕敲了觀眾的腦勺一下,以他者的樸實日常,以及「文青夢」來提醒人細嚼每個當下的清雅。 (閱讀更多)